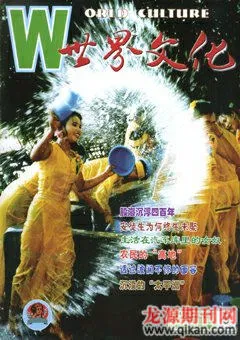憂傷而絕望的青春愛情之歌
巴勃羅·聶魯達(1904—1891),智利當代著名詩人,1971年,由于“詩歌以大自然的偉力復蘇了一個大陸的命運和夢想”,且“與人類和大地和諧”,“謳歌奮斗”,“為維護理想和未來吶喊”,“有益于全人類”,“具有世界意義”,而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再加上他多次訪問前蘇聯和中國,積極參與智利的政治斗爭,因此,在國人的心目中,聶魯達主要是個思考智利、美洲乃至人類命運的詩人,尤其是一個政治詩人。這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遮蔽了其詩歌相當重要而且極有特色的一面——愛情詩。其實,聶魯達早就說過:“首先詩人應該寫愛情詩。如果一個詩人,他不寫男女之間的戀愛的話,這是一個奇怪的詩人,因為人類的男女結合是大地上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如果一個詩人,他不描寫自己祖國的土地、天空和海洋的話,也是一個很奇怪的詩人,因為詩人應該向別人顯示出事物和人們的本質、天性。……對于詩人來說,所有的道路都是開放的,……詩人如果掌握了人民和自然界這樣一個巨大的力量,他就可以走得非常遠。……有了這一切力量,一個詩人就可以成為一個真正的人。”正因為聶魯達認識到愛情對于人類的重要性,而他自己在感情生活方面頗為開放,體驗比較豐富,因而留下了相當多的愛情詩歌,構成了一組組著名的愛情組詩。《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就是其早年愛情詩的代表作,也是其名揚智利的成名作,這部小小的詩集是20歲的青年大學生聶魯達獨特才華的初次展露:“《二十首情詩》一出版就轟動了智利文學界,特別是年輕的聶魯達崇拜者們,更是先睹為快,爭相傳頌,它在一代青年中得到共鳴。聶魯達由此名聲大震,他的詩從邊陲特木科的冷雨中走到首都圣地亞哥,現在又走向整個智利。評論界的反應也很熱烈……”
20歲,正是風華正茂、激情滿懷、浪漫翩翩的年齡,既渴望被人愛,也期盼真誠熱烈地愛人,許許多多動人的愛情故事就產生于這個年齡。才華出眾的聶魯達由于貧窮(當時父親斷絕了生活經費的供給),更由于詩人多情的心靈,加倍渴望愛的慰藉。他與一些女子,演出了一幕幕美麗的愛情悲喜劇,留下了這本使他名震智利的詩集。那么,這本詩集中的女子究竟是誰呢?這是聶魯達生前一個難解的謎,不少研究者費盡心機,也只能徒勞而返。詩人在回憶錄中曾作過解釋,稍稍透露了一點點“消息”,因為他采用的是詩人含蓄的表達方式:“《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是一本令人痛苦的田園詩集,書里寫的是青春期把我折磨得好苦的情欲,還交織著我國南方那使人不知所措的大自然。這是我珍愛的一本書,因為它在刺心的憂傷中展現了生的歡樂。因佩里亞爾河及其河口幫助我寫就這本書。《二十首情詩》是有關圣地亞哥及其有大學生走動的街道、大學校園和分享著愛情的忍冬花香味的浪漫曲。……不斷有人問我,《二十首情詩》中的女子是誰,這是個難回答的問題。在這本既憂傷又熾熱的詩中交替出現的兩三位女子,我們可以說相當于瑪麗索爾和瑪麗松布拉。瑪麗索爾是迷人的外省愛神,有夜里閃現的點點繁星和特木科濕漉漉的天空般陰沉的眼睛,幾乎所有的篇頁里都能見到她的歡樂和明麗的形象,圍繞著她的是港口的水域和露在山巒上的半規明月。瑪麗松布拉是首都的大學生,是灰色貝雷帽,是極度溫柔的眼睛,是用情不專的大學生愛情忍冬花所散發的持久香氣,是在城市隱蔽地點熱情幽會后的肉體的寧靜。”時至今日,隨著一些書信的出版,這個謎已被初步揭開,能比較肯定的是三位姑娘。最迷人的外省女神瑪麗索爾的真實姓名是黛萊莎·萊昂·貝蒂安斯,而瑪麗松布拉的真實姓名則是阿爾維蒂娜·阿索卡爾,第三位是瑪麗婭·帕羅迪。他和她們都有過熱戀,并且不僅為她們寫情詩,而且給她們寫了不少書信。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未能與她們中的任何一人結為夫婦,而其中前兩位女性都是等到三四十歲以后才結婚。正因為這是沒有希望的愛情,因此詩人在這組詩里憂傷而較為絕望地歌唱純樸的愛情,表現男人和女人之間的愛的激情。
50歲時聶魯達曾說過,《二十首情詩》中的第3、4、6、8、9、10、12、16、19、20首和最后那首絕望的歌是寫給瑪麗索爾的,其余10首是寫給瑪麗松布拉的。65歲的時候,他又指出,第19首是寫給黑眼睛的瑪麗婭·帕羅迪的。由于經過了幾十年時間,當年許多的事情不一定都能記得十分清楚,再加上文學尤其是詩歌本身表達的既具獨特性更有普遍性的特征,因此,這21首詩除了一些特別有特征的外,不少詩實際上是交混、共通的,也就是說是獻給當時兩位甚至兩位以上女性的。但總體看來,這21首詩還是可以大體上分為“瑪麗索爾(或黛萊莎)組詩”或“瑪麗松布拉(或阿爾維蒂娜)組詩”。
黛萊莎是聶魯達的同鄉,她的美麗使她1920年在特木科當選為“春光皇后”,聶魯達當時就為她寫了表示祝賀的詩歌,并且在報上發表了。他們相愛了。可是黛萊莎家庭屬于特木科的上流社會,而聶魯達只是一個貧窮的鐵路工人之子,社會地位的懸殊,使得女方父母堅決反對兩人的交往,最終導致她們分手。黛萊莎是一位活潑、開朗的黑姑娘,給詩人帶來南方和大海的神秘。她黝黑、靈敏、快樂,充滿了生命活力:“黝黑、靈敏的姑娘,使果實成長、/小麥灌漿、水草卷曲的太陽,/造就了你快樂的身體、明亮的眼睛/并使水靈靈的笑容掛在嘴角上。//當你伸開雙臂,一個黑色、渴望的太陽/滾動在你黑色的發絲上。/你和太陽玩耍,宛似和小溪一樣/它使兩汪深色的清水在你的眼睛里流淌。//黝黑、靈敏的姑娘,我無法靠近你的身旁。/一切都使我遠離你,像遠離正午一樣。/
你是蜜蜂癡迷的青春,/是波浪的陶醉,是麥穗的力量。//然而,我憂郁的心在將你找尋,/我愛你快樂的身體,輕松而又纖細的聲音。/溫柔而又堅定的黑色的蝴蝶/宛似麥田和太陽,水和虞美人。”(第19首)她讓詩人想起松林、海濤、麥浪,產生愛的欲望:“遼闊的松林啊,破裂的濤聲,/光線緩慢的游戲,孤獨的鐘,/姑娘啊,陸上的海螺,大地/在你身上歌唱,黃昏落入你的眼睛。//河流在你身上歌唱,我的靈魂從河中逃離/如你所想的那樣并向你喜歡的地方逃去。/請在你的希望之弓上為我標明路途/我將在癡迷中將自己的箭射出。//我正在自己的周圍觀賞你云霧的腰身/而你的寂靜在追逐我受折磨的時辰,/正是你和你那透明巖石的雙臂/我的親吻在那里拋錨,我濕潤的欲望在那里筑巢。//啊,你神秘的聲音,在邊回響邊逝去的黃昏/愛為它涂上了色彩并使它成倍增長!/于是在深刻的時辰里,我看見在田野上/麥穗在風的口中起伏蕩漾。”(第3首)他們曾有過暴風雨中的熱戀:“風暴席卷著清晨/在夏季的心中。//白云在漫游,宛似一塊塊告別的白手帕/風用飄擺的雙手將它們晃動。//暴風無限的心靈/跳動在我們相愛的寂靜中。//在林間呼呼作響,神圣而又動聽,/宛似一種語言,充滿了戰斗與歌聲。//暴風飛快地掠走枯枝敗葉/并擾亂了鳥兒跳動之箭的飛行。//風將她推倒,在沒有浪花的波濤、/沒有重復的物質和傾斜的火中。//她的親吻在爆裂并沉沒/在夏日之風的門口拼搏。”(第4首)然而,就在熱戀中也出現了不祥的悲哀:“黃昏時分,你在我的天空宛似一片云朵/而且有著使我稱心如意的形狀和顏色。/唇兒甜蜜的女人,你屬于我,屬于我,/你的生命是我無限的夢想的居所。//我的靈魂之燈給你的雙足染上了玫瑰的顏色,/我痛苦的酒在你的雙唇間變得甜了許多:/啊,我的傍晚之歌的采集者,/我孤獨的夢想覺得你何等的屬于我。//你是我的,你是我的,我在傍晚的風中/呼喊,風兒拖著我失去了配偶的聲音。/我眼睛深處的女獵手,你的掠取/使你有著像水一樣平靜的夜間的眼神。//我的愛情啊,你在我的音樂之網中被俘獲,/我的音樂之網像天空一樣廣闊。/我的靈魂在你悲哀的眼旁誕生。/夢的國度在你悲哀的眼中形成。”(第16首)然而,愛情的裂痕終于出現了,她開始逃離詩人:“你的胸膛對我的心足矣。/我的翅膀對你的自由足矣。/將從我的口升到天上/那在你的靈魂上安睡的東西。//那是你身上每日的憧憬。/你如同露水落在花冠。/你用自己的懷念破壞著地平線。/永遠在逃走,宛若波瀾。//我說你在風中歌唱/宛似松樹,宛似桅桿。/你像它們一樣高大并默默無言。/突然又宛似一次遠行而變得傷感。//你像古道一樣接納他人。/你充滿著回想和懷念的聲音。/我醒來了,但你靈魂上安睡的鳥兒/有時卻遷徙并逃遁。”(第12首)但是,癡情的詩人仍在渴望、祈求,哪怕是沉浸在極度的孤獨中,他依舊充滿著對她的渴求:“白色的蜂,你在我的靈魂中嗡嗡,陶醉于蜜,/你的飛行迂回在煙霧緩慢的螺旋里。//我是絕望的人,是沒有回聲的話,/他失去了一切,也擁有過一切。//最后的維系,在你身上緊繃著我最后的渴望。/在我荒蕪的土地上你是最后的玫瑰。//寂靜啊!//閉上你的眼睛,黑夜在那里振翼。/啊,你的身體,一尊受驚的雕像,一絲不掛。//
你擁有一對黑夜在其中抽打的深眼。/花朵的冷靜雙臂和玫瑰的懷抱。//你的乳房像兩個潔白的海螺。/一只陰影的蝴蝶飛臨你的腹部沉睡。//寂靜啊!//這里是你不在其中的孤獨。/下雨了。海風在獵取流浪的海鷗。//水赤腳走上濕漉漉的街道。/葉子在樹上害病似的埋怨。//白色的蜂,甚至當你離去還在我的靈魂中嗡嗡。/你在時間里復活,苗條而沉沒。//寂靜啊!”(第8首,黃燦然譯)然而,分手的時刻終于來臨,詩人深感:“愛戀多么短暫,而遺忘又多么漫長”,“失去了她,我的靈魂怎能高興”(第20首),并且寫出《絕望的歌》:“對你的記憶從我所在的夜晚浮現。/河流向大海傾訴自己滔滔不絕的怨言。//被拋棄的人,像拂曉的碼頭。/是離開的時候了,啊,被拋棄的人!//寒冷的花冠雨水般落在我的心上。/啊,溺水者殘酷的洞穴,廢料的底艙!//在你身上積累了戰爭與飛翔。/從你身上豎起來歌唱的鳥兒的翅膀。//你吞下了一切,宛似遠方。/就像海洋,就像時光。一切都沉沒在你身上!……”
阿爾維蒂娜比聶魯達大一歲,也是南方外省人,出生在智利的阿勞科。他們同是一個專業的大學同學,平時經常一起聽課,放假回家,還可乘同一趟火車,共一段路。在一起上課的過程中,他們產生了愛情。可惜的是,大學二年級時,她遵父命轉到500公里外的另一所大學學習。距離可以產生美,也可以阻隔愛情。盡管聶魯達絕望地、狂熱地不斷以詩歌、書信表達愛的激情,但最終這次愛情還是以悲劇告終。阿爾維蒂娜最突出的特點是沉默寡言,喜歡沉思,詩人在詩中一再寫到這點,并且對此表示欣賞。他寫到她的沉默甚至憂傷所具有的極強生命力,足以讓一個藍色的民族獲取營養:“夕陽用它微弱的光芒將你包裹。/沉思中的你,面色蒼白,背對著/晚霞那衰老的螺旋/圍繞著你不停地旋轉。//我的女友,默默無語,/孤零零地與這死亡時刻獨處/心里充盈著火一般的生氣,/純粹繼承著已破碎的白日。//一束光芒從太陽落到你黑色的衣裳。/一條條巨大的根莖在夜間/突然從你的心田里生長,/隱藏在你心中的樁樁事回到了外面,/因此一個蒼白的藍色民族/它一降生就從你身上獲取營養。//啊,你這偉大、豐盈、有魅力的女奴/從那黑色與金黃的交替循環里:/挺拔屹立,完成了生命的創造/鮮花為之傾倒,可你充滿了傷悲。”(第2首,趙德明等譯)也熾烈地表達了自己對這份沉默寡言的衷心喜愛:“我喜歡你默默無言,仿佛你不在,/你從遠方聽著我,而我的聲音接觸不到你。仿佛你的眼睛已經飛走,/仿佛有一個吻封住你的嘴巴。//就像所有的事物充滿我的靈魂/你從事物之中浮現,充滿我的靈魂。/你就像我的靈魂,一只夢的蝴蝶,/你就像憂傷這個詞。//我喜歡你默默無言,仿佛你在遠方。/仿佛你在悲嘆,你蝴蝶的低語如鴿子的輕喚。/你從遠方聽著我,而我的聲音接觸不到你:/讓我也默默無言于你的寂靜無聲。//并讓我拿你的明亮如一盞燈,/簡單如一個環的寂靜無聲和你交談。/你就像夜晚,默默無言且布滿星星。/你的寂靜無聲是星星的寂靜無聲,一樣地遙遠和真實。//我喜歡你默默無言,仿佛你不在。/遙遠而充滿悲哀仿佛你已經死去。/那么一句話,一個微笑,就已足夠。/而我感到幸福,幸福于它的不真實。”(第15首,黃燦然譯)她喜歡帶灰色的貝雷帽,有一顆平靜的心,并且像秋天的黃昏一樣充滿魅力:“我記得你宛若秋天的模樣。/灰色的貝雷帽,平靜的心。/黃昏的火焰在你的眼中搏斗。/在你靈魂的水面上落葉紛紛。//你像一條藤蔓將我的雙臂纏緊,/葉片在收集你緩慢、平靜的聲音。/我的渴望燃燒在驚愕的篝火里。/藍色溫柔的風信子倒向我的靈魂。//我感到你的眼睛在漫游,而秋天多么遙遠:/灰色的貝雷帽,鳥兒的啼鳴和家的心靈/我深深的渴望向那里遷移/我像火炭一樣的快樂的親吻也落在那里。//從船上仰望天空。從山岡將田野眺望。/你的記憶是光芒、煙霧與平靜的池塘!晚霞在你眼睛的深處燃燒!/秋天的枯葉旋轉在你的靈魂上。”(第6首)他們曾有過狂熱的性愛:“女人的身體,潔白的山丘,潔白的大腿,/你獻身的姿態宛似這時節。/為了讓嬰兒從大地的底部跳出/我粗野農夫的身軀將你挖掘。//孤獨的我曾像一條隧道,鳥兒從我身上逃離/強大的黑夜侵襲了我的身體。/為了生存,我曾將你煅造成一件武器,/宛似我弓上的箭,投石器上的石子。//但報復的時刻降臨,可我愛你。/肌膚、苔蘚、貪婪而又堅韌的乳汁的身體。/啊,胸部的酒杯!啊,迷茫的眼睛!/陰部的玫瑰啊!你緩慢而又悲哀的叫聲!//我的女人的身體,我將執著于你的魅力。/我的渴望,我無限的情欲,我的路撲朔迷離!/昏暗的渠道,我永恒的渴望、我的疲憊/以及我無限的痛苦都在那里持續。”(第1首)然而,阿爾維蒂娜遠去了,空虛、孤獨的詩人呼喚著她,祈求她愛自己:“為了讓你/聽得見我的話語/它們有時細得/像海鷗在沙灘上的足跡。/項鏈,陶醉的鈴鐺/獻到你像葡萄般柔軟的手上。//我望著自己在遠方的話語。/它們其實更屬于你。/它們像常春藤一樣爬上我痛苦的往昔。//它們這樣攀上潮濕的墻壁。/這淌血的游戲,是由你引起。//它們正在逃離我陰暗的巢穴。/你無所不在,充滿一切。//它們先于你,占據了你的孤獨,/它們比你更習慣于我的愁苦。//此刻我向它們道出對你的訴說/為了讓你聽到它們如同想讓你聽到我。//苦悶的風常常還將它們拖跑。/夢幻的狂飆往往仍將它們橫掃。//
在我痛苦的聲音中你會聽到別的聲音。/古老的口中的哭泣,古老的乞求的血滴。//伴侶啊,愛我吧。跟著我,別將我拋棄。/伴侶啊,跟著我,在這苦惱的波濤里。//我的話語會染上你的愛的色彩。/你占據了一切,你無所不在。//我要用所有的話語做成一條長長的項鏈/獻給你潔白的雙手,她們像葡萄一般柔軟。”(第5首)最后,詩人深深感到,自己“在深深的孤獨中思考并擺弄著影子”,而“你同樣遙遠,啊,比任何人都遙遠”,甚至覺得“你的存在與我無關,對我與同一個奇異的物體”,不由自主地深思:“女人啊,你,你在那里是什么?在那無比巨大的扇子上/你是什么樣的條、什么樣的線?……/你是誰,誰是你?”處在這樣一種迷惘和困境中,詩人感到:“我的靈魂,被所有的根震撼,/被所有的浪沖擊!/無休止地滾動、快樂、悲戚!”(第17首,本文中未標明譯者的,均為趙振江等譯,見趙振江、滕威編著《山巖上的肖像——聶魯達的愛情·詩·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