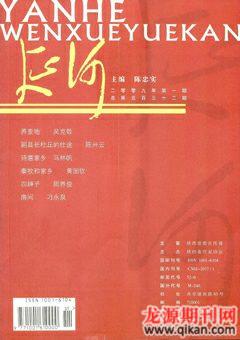嗩吶萬清
周 煒
萬清的嗩吶在方圓是吹出了名的,誰家喪事樂人伙里沒見萬清,吊孝哭喪的都感覺沒有眼淚。萬清就那么給人伙里一站,嗩吶的口口高高在空中一揚“嘟——”一聲,眾人便無不為之動情,那揪心撕肝的嗩吶聲使在場的人比自己爹媽去世還難受。
那天酒足飯飽后,楊大頭把伸在嘴里摳牙縫的手指頭取了出來,在自己的屁股上抹了幾下,然后從身后的那個小皮包里取出一大沓扎得緊繃繃的人民幣,“嗵”的一聲放在了萬清面前,萬清老漢吹了大半輩子嗩吶,從來還沒見過這么多的錢,平日里在哪家過事,吹得頭頂冒汗,兩腿打顫,主家才往桌上撂上個五元,遇上個干部家最多拾元,楊大頭一下子甩了這么多,萬清真想當著楊大頭的面把自己婆娘親上兩口。楊大頭說:“娃不小了!”萬清迷著眼,點頭哈腰:“是不小了,是不小了!”“你那娃娃咱放心著呢?”楊大頭對萬清說:“方圓都知道你那女子是個乖娃,我家軍成就只看上你那娃咧。”
“嘿嘿……萬清不知該說什么好,眼睛看著楊大頭下了炕,只要咱那邊好了,這邊沒啥說的,早把這事辦了,我也就該洗手了。”
楊大頭寒暄幾句之后,滿意地打著飽嗝走了。
“萬清把女子賣了——”村里人知道了都說。“媽!我不想活了,”彩紅在房子里有氣無力地說:“我爸逼著要我死呢?”
“瓜娃先,咋說那話哩!你爹又不是把你往火坑里推,軍成他爸不是好東西,咱又不給他嫁,娃沒啥問題就行了。”萬清的老伴極力安慰著自家女子。
“哼,啥樹上結啥蛋蛋,狗吃屎,狗患能不吃”彩紅沒好氣地說。
“軍成那娃一直不是挺好的么?”
“白天就像是個人,媽,你倒底知道啥嗎?反正我也不活了,不妨給你說了吧!上個月咱村上有電影,那貨就來坐在我旁邊,那晚上,電影機子片子斷了,那貨乘著天黑臟手就過來了。”
萬清老伴瞪著眼問“干啥?”
彩紅說:“你說要千啥?”
“我不知道?”
“要……要……摸你娃奶呢!”
“你讓摸了?”
“你女子沒有那么賤!”彩紅看著他媽古怪而驚異的表情。“他就又把嘴湊了過來。”
“他親了你了?”
“沒有,他對我低聲說:你私下問一下你村子的女娃,誰的大,誰的小,誰的上邊有痣,我都能給你說上來,摸你是看得起你昵?我高興了還要摸下邊昵?”
“虧他先人哩!虧他先人哩!”萬清老伴說:“楊大頭咋弄下那貨呢?……”
“我說你摸你媽去?”
“罵的好,是我非扇他個X嘴。”
“他說:‘小時候把我媽摸夠了,現在就摸你”。
“我說你個流氓,我要喊人了。”結果那個下流坯子還說什么“男人不流氓,發育不正常。”他還說“你不嫌丟人,你就喊,xx摸我奶頭呢?”
“那么你個瓜娃昨不喊昵?”
“我怎么喊呢?”彩紅紅著臉說。
“那你讓他摸了。”
彩紅沒吭聲。
“嗯?”
“嗯!”好半天,彩紅方從嗓子里擠出了一聲。
“瓜娃先,人一輩子圖個啥,還不是過上個舒心日子,”我看:男人就沒有一個好東西,你爸年輕時,娶我進門后,在外過喪事時,有幾個女的找到家要跟你爸,為此媽經常被你爸罵了、打了卻不敢吵鬧。女人一輩子嫁個人容易嗎?再說離開這家到另一個家有會是個啥樣子呢?我媽活的時候經常讓我坐在她懷里,說:“娃呀!女人一輩子鬧著活不如過著活,想想這媽啥都就在乎了。”
彩紅就覺得媽的命好苦好苦,可自己一點也不同情媽,她只是覺得自己實在沒有必
活下去了。連一天都不想了。
萬清老伴還低著頭安慰著女兒好半天,沒聽見彩紅說一句話,抬起頭時,萬清老伴
照在屋檐上的陽光也沒有了,太陽已經偏西了。
當太陽在地平線上完全消失的時候,整個村莊的上空和周圍裊裊的炊煙就升起來了。
彩紅穿著整整齊齊走到她媽的房子里,平靜地說:“媽。”
萬清老伴正把一大把一大把的柴禾往炕筒里塞。天冷的出奇,不睡火炕萬清老倆口
疼的厲害。
“我娃想通了”萬清老伴手不停地問,也沒有注意彩紅的表情。
彩紅的眼淚就像斷了線的珠子一樣往下落,她覺得天底下最可憐,最可憐是她的媽,再
下來就是她。
她蹲下身子,幫著她媽往里邊填柴。
彩紅說:“媽,你甭怪你娃噢!”
萬清老伴轉過身。
“娃吔!你哭啥哩嗎?”萬清老伴幫女子擦眼淚,“好好的媽咋能怪我娃呢?,,
“媽——”彩紅一下子覺得心里有一種巨大的難受侵撓著自己,于是便抱著自己的主
失聲痛哭,萬清老伴禁不住把娃的手拉住站起身陪著掉眼淚。
“媽,我喝了藥了”,彩紅說的很平靜,瞬即又哭。
彩紅媽身子一震:“真的——”
彩紅的淚流了一臉,仔細地望著她媽蒼老的臉點了點頭。
“好我的娘昵?你咋給我弄個這事呢?”萬清老伴就覺得心里空落落的,隨之身子
“撲踏”就坐到了地上,身子發抖,渾身顫栗著喊:“大龍,大龍.你死到那里去咧。”
大龍昕到他媽焦急地喊聲,從房子里跑了出來。
“媽,咋咧,咋咧!”
“咱那媽給咱把亂子闖下了,”彩紅媽說著就狠勁地打了一把彩紅。
彩紅沒有躲,吃了她媽狠狠的一打,哭得更厲害。
“到底昨回事。”
“快,快,快去把你爸叫回來,快,彩紅喝了藥咧!”
“啥?!”大龍的兩個眼睛瞪成了公牛卵子。
大龍的婆娘把娃也擱在炕上,任娃哭爹喊娘自己一古腦跑到婆婆房子里,一邊勸著婆婆
一邊把彩紅抱住連搖帶問。
彩紅的嘴開始變得烏青,彩紅發瘋似的撒扯著肚子上的衣服,揪著自己的頭發,但
喊一聲,就像無形當中有人在用刀在割著彩紅身上的肉。
萬清把車子也沒放穩當,就一腳踩進房門,他沒有罵彩紅,沒有打彩紅,對著婆娘吼:
“聲住了,又沒死人,哭啥呢?”大龍,幫爸把彩紅放到車子上。
大龍沒有動彈,望著萬清忙活,然后他說:“爸!要不要叫幾個人來。”“放你媽的狗臭屁,叫人看熱鬧呀!”萬清一時間真有些后悔。
“大龍,你死了么?”
大龍不吭聲,幫著讓彩紅坐上車子,然后自己扶著車把就要走。
“你干啥去?”萬清問。
“到醫院。”大龍說。
“滾一邊去。”萬清說:“全部給我窩到家。誰的屄嘴放出消息,把誰屄就撒爛。”
萬清推著彩紅往村口走。村里煙霧繚繞,空氣里不知誰家的辣椒當火燒,嗆得萬清連打幾個噴嚏。
村里上地的人三三兩兩收工回家。
“萬清哥,天快黑了和彩紅上那去”眾人問。
“娃病了,給娃娃去鎮上看看”,萬清若無其事。
“喲!這娃病得不輕呢?你看,娃鼻子、嘴里都出血了。”
“可不是呢?彩紅、彩紅。”萬清裝著很親妮的樣子,用手把彩紅嘴角的血全擦了去,推上就走,好在天色越來越暗。
冬季的夜來的快,一時間,田野上模模糊糊。
萬清叫了聲彩紅,彩紅微弱的答了聲。
萬清感到車子頭越來越沉,走上大路的時候,天全部黑了,萬清又叫了一聲女子的名字,彩紅沒應聲。又走了幾十米,萬清實在推著力不從心,停下來連叫數聲彩紅、彩紅、彩紅、田野一片寂靜,只有風把電線吹響的哨聲,萬清把手伸到女子的鼻子底下,手涼涼的,和外邊的空氣一樣冷。他給自己說:不用去了,就勉強著轉了個頭,把彩紅推回了家。
家里正焦急不安。
他讓大龍把彩紅的腿抬著,他架著彩紅的胳膊把彩紅放在支好的床上。
老伴問:“好了沒有,看了沒有?”
大龍就盯著萬清的臉,不動聲色。
只有墻上的那架老掛鐘“柒框,柒框”的走著,空氣也像全凝固了,不知能過多久,萬清就沖著婆娘喊了一句:
“哭——”接下來就是他:啊啥哈、彩紅,你個沒良心的。嚎叫起來,于是哭聲就一下子傳了出來,滿村子的人沒有一個人昕不見的,院子里塞得實實的,都說彩紅,太狠心了,他爸他媽養她這么大,一場病就走了。
有人就勸萬清和老伴,說女子本就像個荒花,不會結果,走了也就走了,難過啥呢?
萬清不哭了,就趕緊找人商量后事,村長把鈴一打,臨時派人連夜打墳挖墓,全村人知道因為彩紅還未嫁人,尸體不能放一天一夜的,村上有專門負責喪事的連夜把風水先生也叫了來。
村里的大人全分班輪流打墓,村中央掛起了大燈,村里的氣氛一下子緊張起來。
第二天下午,墓打好了,萬清眼看著把滿嘴烏青的彩紅放到了訂好的木箱里,萬清老伴哭得死去活來,哭著哭著便罵一聲萬清,村子里的人都納悶:這老婆,女子出事,罵老漢干啥?
大龍的婆娘也跟著哭,但卻沒有罵,雖說沒有哭得昏天黑地,但圍觀的沒有一個不陪著掉眼淚,都說彩紅生前多么乖、多么昕話。
送喪的人很多,但卻沒有一個穿白戴孝的,大龍夾在送喪的隊伍里邊卻沒哭,他就過一會兒看看哭著的老爸萬清。
村里人說男人的心硬!
大龍最后一眼看了一下親生生的妹子,眼睛一翻,就轟然一聲平撲在地。
眾人又是插人中,又是撫胸口。好半天才見大龍睜開了眼睛。
一大鏟一大鏟的土被埋在了裝彩紅的箱子上,墳墓的土越來越多,終于從地面凸起了一個小土堆時,一陣風帶著啥地方一個清脆的嗩吶聲,聲音斷斷續續,像是有人在學嗩吶,可在場的人都感覺那嗩吶聲比萬清老漢的嗩吶還要好聽,還要痛斷肝腸,萬清就不自在地去看兒子大龍,正好大龍也地看他,萬清平時的兇狠全然沒有了,就像一只斗敗的公雞一樣耷拉著腦袋。
嘿嘿就知道你的心里虛著呢?大龍給自己說,一時間,他覺得說不出來的難受,在她的思維里,他完全想著彩紅,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情血直涌上心頭,他想著彩紅的名字“爸吔”抱著彩紅墳堆上的新土,鼻涕拉了好長好長,別人拉勸都不頂事。
大龍是被眾人拉回家的。
萬清老漢眼睛也腫了。
村子死個年輕人,村子里的人躺在自己家,也不再出去,煞氣重重的,小孩也不敢大聲哭,偶爾有二只貓凄厲的叫上二聲。
萬清回家后,打了個轉身,便走出家門,直奔女兒彩紅的墳墓。
風像刀子一樣硬,吹在臉上生冷,像鬼在抽打著臉,萬清在彩紅的墳前找了個避風的地方就坐了下去,他的腦子里木木的。半夜了,風出奇的冷,萬清覺得骨頭的里邊都沒有一點溫度了,遠處有一個高大的黑影像一個鬼魅東搖西晃,萬清畢竟活了大半輩子,是個年輕人不被嚇死也活不旺,況且,萬清知道,遠處的黑影只不過是一棵樹而已。
一只貓頭鷹突然在夜半叫了起來,把個本來就陰森森的夜叫得更加凄慘,驚恐。責任編輯 寇揮周煒 男,生于七十年代,陜西扶風人,做過雜志編輯,已發表中短篇小說若干,系陜西作家協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