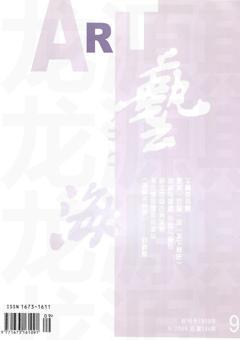古典詩之音樂描寫
林升樂
我國是一個詩的國度,且歷史悠久。古詩詞為我們留下了許多感情真摯、動人心弦的篇章,尤其是古詩中對音樂中器樂、聲樂的描寫,常常以豐富多彩的風格美出現。
一、“方軌儒門”的典雅之美
1.“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則勤而不怨矣。……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也,其周之東乎?……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樂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低,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吳公子季札欣賞周、王、豳、魏、頌等國之樂.極為贊嘆。他認為諸國之樂皆為“方軌儒門”之樂,具有典雅之美。劉勰《文心雕龍》云:“典雅者,熔式經誥”,方軌儒門也。今天,誦讀上面這段引文,依舊會被那詩韻的氣氛所籠罩,一種典雅的美溶注全身。
2.“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詩經·小雅·鹿鳴》第三章)
鹿鳴呦呦,喚伴食野芩。滿座嘉賓,彈瑟奏琴,和聲久鳴,酒酣耳熱座生春,一杯美酒,借此娛樂諸貴賓。這是貴族宴會賓客之絕唱。這段文筆中,“眼琴綠陰”,“坐中佳士”,優雅嫻情,實有典雅之美。唐末司空圖在《詩品·二十四則》中對典雅風格的形象和意境表述為:“玉壺買春,賞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鳥相逐,眼琴綠陰,上有飛瀑。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書之歲華,其曰可讀。”真有道理。
二、“孤云一鶴”的飄逸之美
1.“浮云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風揚。”(韓愈《聽穎師彈琴歌》)
韓愈極善刻畫穎師琴音。古琴那輕柔、飄浮、如絲如縷的音樂,遠揚而持久,把音樂這個不易捉摸的聽覺形象,通過巧妙描繪,訴諸于“浮云柳絮”這等優美的視覺形象,仿佛高空“孤云一鶴”,給人以飄逸之美。陶明濬曰:“何謂飄逸?秋天閑靜,孤云一鶴者是也。”
2.“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東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于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漿,擊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蘇軾《前赤壁賦》).
詩客扣舷而歌,胸懷渺渺,遙盼“美人”,思緒飄逸,正與其行止所符:任小船于“萬頃茫然”的水上浮游,似憑空馭風,有“羽化”、“登仙”的“飄飄乎”之感。這種泛舟暢歌中落落欲往,嬌嬌不群,御風羽化,泛彼無垠的境界,給讀者以飄逸之美優勝的感覺。司空圖《詩品·二十四則》中對飄逸風格的闡述是:“落落欲往,嬌嬌不群,猴山之鶴、華頂之云。高人畫中,令色絪缊,御風蓬葉,泛彼無垠。如不可執,如將有聞,識者已領,期之愈分。”所言正是。
三、春花秋月的纏綿之美
1.“回樂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李益《夜上受降城聞笛》)
李益這首絕句,似一組電影鏡頭,給人以直觀感;征人遠居邊地,夜登受降城忽聞笛音,頓時觸動他的邊庭離情,于是踮腳望鄉,悲哀地歌唱,音調哀怨纏綿。這給讀者情感上以“纏綿不已,不能解脫”的纏綿美感。
2.“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心。”(李白《春夜洛城聞笛》)
春夜洛城,玉笛幽怨,令李白情思興起,宛若見親人路邊惜別,流兩行清淚,折楊柳一枝,依依惜別深情寄于楊柳之中,那曲調飽含離愁別緒,激起纏綿的故園之情。
四、“笳拍鐃歌”的悲壯之美
1.“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于是項王及悲歌概慷,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闕,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司馬遷《史記.項羽本紀》)
極力描寫項羽最后失敗的“英雄末路”,悲歌一曲,音韻悲壯、凄美,頗富人情味。細節典型,筆調沉重,讀時宛若悲壯凄愴古琴之韻猶在耳畔,具有催人一掬同情之淚的藝術力量。
2.“蔡女昔造胡笳聲,一彈一十有八拍。胡人落淚沾邊草,漢使斷腸對歸客。古城蒼蒼峰火寒,大荒沉沉飛雪白。先拂商弦后角羽,四郊秋葉驚槭槭。董夫子,通神明,深山竊聽來妖精。言遲重速皆應手,將往復旋如有情。空山百鳥散還合,萬里浮云陰且晴。嘶酸雛雁失群夜,斷絕胡兒戀母聲。川為凈其波,鳥亦罷其鳴,烏孫部落家鄉遠,邏娑沙塵哀怨生。幽意變調忽飄酒,長風吹林雨墮瓦。迸泉颯颯飛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長安城連東掖垣,鳳凰池對青瑣門。高才脫略名與利,日夕望君抱琴至。”(李頎《聽董大彈胡笳弄兼寄語房給事》)
李頎為當時著名胡笳手董庭蘭精湛琴藝折服,揮筆寫詩,好一派胡笳的悲壯之音:大漠沉沉,白雪似鵝毛紛紛飄落,烽火寒煙籠罩四荒八野,蔡文姬歸漢啟程,行走前彈奏一曲悲切的《胡笳十八拍》,商弦羽音,更添寒意。漢朝使節對樂愁腸寸斷,十二年春夏秋冬,如今辭別一朝,胡人也不禁潸然淚下。這雖為蔡文姬彈奏《胡笳十八拍》時的境況,但時隔數百年,李頎聽董庭蘭彈奏此曲,驚動深山妖精前來竊聽。董指下多情,如泣如訴的妙音流出,四散鳥雀為之集合山巔,陰沉的浮云為之放顏開晴,哀且悲壯,恰如雛雁失群,胡兒戀母,痛裂肝腸,江河為之息波,鳥雀為之罷鳴,琴音嘶啞,一曲難盡。變調彈奏,深沉的樂曲忽如飛蝶狂蜂飄散萬般,長風吹林,石泉過澗,野鹿呦呦鳴聲回響堂前。這就在前面“悲”的基礎上,抹濃了“壯”的色彩。陶明濬曰:“何謂悲壯?笳拍鐃歌,猛起者也。”確也近理。
五、“絲哀竹濫”的凄婉之美
1.“昔季流子向風而鼓琴,聽之者泣下沾襟。弟子曰:‘善哉鼓琴!亦已妙矣!”(阮籍《樂論》)
聽之者“泣下沾襟”,是季流子向風鼓琴聲悲音哀、絲凄弦慘之故。今日吟讀,透過字里行間,也能享受到那種凄婉風格的美感。
2.“傳書言:‘瓠芭鼓瑟,淵魚出聽;師曠鼓琴,六馬仰秣。或言:‘師曠鼓《清角》,一奏之,有玄鶴二八自南方來,集于廊門之危;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吁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尚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雖奇怪,然尚可信。何則?鳥獸好悲聲,耳與人耳同也。禽獸見人欲食,亦欲食之;聞人之樂,何為不樂?然而淵魚出聽,六馬仰秣,玄鶴延頸,百獸率舞,蓋且其實。”(王充《感虛篇》)
其所以淵魚出聽、六馬仰秣、玄鶴延頸而鳴、百獸率舞,是因為琴瑟彈撥之曲和擊石拊石之節奏悲涼低沉,凄切哀婉,六馬、玄鶴、百獸為其感傷而心動,故不但聽之,且鳴之舞之。這種以鳥獸動情于音樂的描寫,實不多見,今人讀之,多覺文筆的凄婉風格美甚。
六、清越宛轉的回環之美
1.“唱了十數句之后,漸漸地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個尖兒,像一線鋼絲拋入天際,不禁暗暗叫絕。那知他于那極高的地方,尚能回環轉折;幾轉之后,又高一層,接近有三四疊,節節高起。恍如由傲來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情景;初看傲來峰峭壁千仞,以為上與天通;及至翻得傲來峰山頂,才見了扇子崖更在傲來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見南天門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險,愈險愈奇。那王小玉唱到三四疊后,陡然一步,又極力騁其千回百折的精神,如一條飛蛇在黃山三十六峰半中腰里盤旋穿插,頃刻之間,周匝數遍。從此以后,愈唱愈低,愈唱愈細,那聲音漸漸的就聽不見了。”(劉鶚《老殘游記》第二回《歷山山下古帝遺蹤,明湖湖邊美人絕調》)
這是對王小玉說書中宛轉歌喉的描寫。那清越的妙音的上行和下行,“回環轉折”、“盤旋穿插”的回環之美,似乎一個蓋世的花腔女高音在耳邊繚繞、引人入勝。
2.“花繁柳暗九門深,對飲悲歌淚滿襟。數日鶯花皆落羽,一回春至一傷心。”(錢起《長安落第》)
這首悲歌并不停留在愁者落第、悲淚滿襟的聲樂現象描寫上,而著重于“一回春至一傷心”的點睛之筆上,年年傷心,時光與悲愁共回環,濃化了讀者情思,強化了聽覺想象力,使悲歌的傷感情調更趨深沉。
古人在古詩中對音樂的描寫,本文純屬舉隅,僅把名著中極少精彩的段句列舉出來,雖“一斑片爪,莫窺全豹”,但古人對音樂中聲樂和器樂方面的寫技,特別是豐富多彩的風格美,皆源于描寫對象器樂或聲樂本身的風格美,這未嘗不可賞心悅目,陶冶性情,啟迪靈感,開拓神思,助人審美。
(作者單位:四川建筑職業技術學院)
責任編輯: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