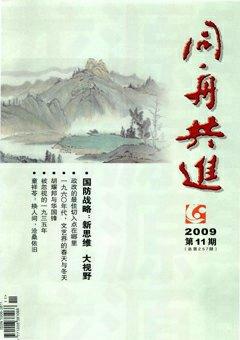駱思典:一個外國學者眼中的中國60年
曾東萍
駱思典(Stanley Rosen),美國中國問題專家,研究中國三十余年。美國南加州大學政治系教授、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美國政治學會、亞洲研究協會成員。編著有《21世紀中國國家與社會》(英文)、《中國電影藝術、政治與商業間的交互作用》(英文)等。
中國青年:從紅衛兵到汶川地震志愿者
《同舟共進》:您第一次來中國是什么時候?
駱思典:我1971~1976年在香港寫博士論文,關于紅衛兵的思想研究,也是我研究中國的開端。第一次到中國內地是在1980年,去了北京和廣州。以后每年都會來中國,去不同的地方。
《同舟共進》:那您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見證人了。在您的記憶中,30年前的中國是什么樣的?
駱思典:中國變化太大了。記得1980年我帶團(學術研究團)到北京,是國際旅行社安排的——當時以個人身份是很難進入中國的。那時北京的酒店非常少,房間不夠,只能住天津的招待所。每天凌晨5點起床趕到北京參觀游覽,第二天凌晨1點才能回到天津,那時天津到北京坐車要4個小時;1980年也帶過團經澳門去廣州,那時還沒有高速公路,有些地方只能坐船渡江,當時廣州很多人不會講普通話。1980年代的中國還有很多落后的地方,我們的團友很喜歡拍那些地方,當地人就阻止說:“你為什么拍最落后的地方?你想干嘛?”然后就把我們帶到新一點的地方去。其實我們都知道現代化是怎么回事,所以對中國的文化傳統感興趣,這正是矛盾之處。現在中國城市里,落后的地方已很難找到了。
《同舟共進》:您覺得30年中,中國最大的變化是什么?
駱思典:人的思想和價值觀,尤其是青年。我為了完成博士論文,在香港呆了5年多,采訪了200多個從廣東偷渡到香港的紅衛兵。他們大多是還沒畢業的中學生和共青團員。很多人認為紅衛兵是意識形態化的,但并不那么簡單,有些紅衛兵的思想很“紅”,非常革命;有些是“我看透了一切”;還有些認為自己是犧牲品,上山下鄉就留在農村一輩子……每個人都不一樣,不過都是愛國者。紅衛兵也有很功利的(這一點跟現代中國青年的物質主義有點像),比如很多紅衛兵競相加入共青團、共產黨,并不單純因為愛國,還因為這與個人的工作、前途密切相連。中國現代的青年,思想上當然有了很大轉變,特別是1992年以后,中國開放得很快,互聯網開始普及,海歸派回國,青年對國際的變化了解得更多,思想也更多元。在我看來,當代中國青年的思想有三個特點:國際化、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物質主義。中國青年在平時物質主義表現得比較強,但有特殊情況發生,比如在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等事件中,就表現出一種理想主義、愛國主義。汶川大地震后,很多“80后”去到四川當志愿者,這與紅衛兵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似的。所以,常態和特殊時期要分開來看。
前段時間《中國不高興》引起很多爭議,我也看了。我覺得他們(作者)就是民族主義者。比如,他們認為美國已經不那么強大了,中國為什么不出擊?還有,他們批評親美派,批評改革派,當然也批評自己的政府。
《同舟共進》:那些紅衛兵現在的生活怎樣?
駱思典:他們有些人聯系我。有一個紅衛兵,以前是廣州科技學校的,當年沒什么文化。幾年前他給我打電話,說兒子要上大學,不知喬治敦大學好還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好。我告訴他兩所大學都是美國頂尖的院校,但喬治敦大學是私立學校,學費比較貴。他說,錢不是問題!他在硅谷已經有了自己的電腦公司,還給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捐款。很多紅衛兵到了美國都挺成功的,因為他們很努力,這一點我很欽佩。他們本身的文化不高,甚至有些現在英語都說不好,但他們的孩子都很成功,這種現象非常普遍。當然,“文革”那段經歷對他們影響很大。不久前有個人打電話給我,和我談論一部電影《高考》,電影內容是關于1977年恢復高考的,他看了覺得很感動。他們覺得自己是比較幸運的,還有很多人就留在了農村一輩子。
透明度:中國下一步最需要解決的問題
《同舟共進》:您前面談到中國社會的發展和進步,那么,在您看來,社會發展有沒有帶來一些負面的東西?表現在哪些地方?
駱思典:當然有,比如物質主義、腐敗、“包二奶”等等。拿物質主義來說,有人做過調查,結果顯示現在的小學生知道麥當勞叔叔的比知道孫悟空的要多。這是一種很奇怪的現象。中國有五千年的文化傳統,強調儒家思想,強調教育,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還有,我認為中國的腐敗問題很難解決。因為有兩個矛盾,一是社會穩定與反腐敗的矛盾。政府強調穩定,地方官員為了維持穩定,不讓老百姓上訪,壓制群體事件,對上級政府包括中央政府,隱瞞了太多東西。老百姓對中央政府有信心,反而對地方官員不信任;二是經濟發展與反腐敗的矛盾,商人與官員的關系太密切,如果在短時間內過于強力反腐,有人擔心會影響經濟發展。
《同舟共進》:美國媒體經常說中國是一個崛起的大國,這代表了大多數美國人的想法嗎?您個人的看法呢?
駱思典:說實話,很多美國人不怎么關心外國的事情。比如在香港,可以看到美國的新聞,但在美國,很少有外國的新聞,即使有,也多是有關伊拉克、阿富汗的。當然,中國非常成功,這是無可置疑的。我記得看過《中國青年報》的一個調查報告,在美國、歐洲,有90%的人承認中國是下一個超級大國。但很奇怪,中國人自己反而不一定承認。在我看來,中國在經濟實力和對世界的影響方面,越來越成為一個大國,但在政治影響力和軍事實力方面,還稱不上大國。
《同舟共進》:您認為中國要繼續健康快速地發展,下一步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
駱思典:透明度,我認為這是中國繼續發展面對的最大問題。“大躍進”時期,毛主席去到地方考察,有些地方領導把糧食都收集起來,堆在他經過的路上,做出豐收的假象。經過改革開放,現在的情況比以前好一點,但問題還是存在,比如很多大學給出的就業率有很多水分,這樣,中央就很難知道真實的情況,這將最終影響政府的決策。透明度會影響很多方面。
再比如在西藏和新疆事件上,為什么那么多西方媒體誤讀?除了它們本身的因素外,跟中國的透明度也有很大關系,一是對外的透明度,二是對內的透明度。
不過中國人尤其是年輕人,對媒體的態度有一個很有趣的轉變。上世紀80年代初,我跑了中國很多地方,經常跟大學生交流,當時很多大學生不相信中國媒體,而幾乎百分之百相信BBC和“美國之音”;現在不同了,更多大學生知道歐美的媒體不一定正確。這也跟互聯網的普及有很大關系,現在的中國青年懷疑一切(包括西方媒體),這對中國政府是有很大好處的。
《同舟共進》:對中國的未來,有人把您歸為“樂觀派”,您“看好”中國的原因是什么?
駱思典:未來的趨勢很難預料,從總體趨向看,我比較樂觀,但在全球經濟危機的背景下,也很難說。因為中美的利益已緊密地連接在一起,是“同舟共進”的。不僅僅中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如此,不可能一個國家情況很壞,但與它密切聯系的國家還能很好,這是全球化的趨勢。當然,中國本身存在很多問題,其中一個問題不可忽略,就是一旦有危機發生,群眾相不相信政府?中國的政治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從前毛澤東是權威,他帶領中國革命取得成功;接著是鄧小平,他帶領中國改革開放取得成功。但現在的中國,領導人已沒有像毛澤東和鄧小平那樣的權威。政府應該考慮到這個變化。
從電影看中國社會60年變遷
《同舟共進》:我知道您很關注中國電影,尤其是有關政治和社會變遷的。您能從電影角度談談中國60年的變遷嗎?
駱思典:我在美國加州大學講授電影課,也談中國電影,我做了一個反映中國60年變化的片子給學生看。這里就談談我挑出來的電影和片段吧。
《烏鴉與麻雀》,開拍于1948年,講述解放前夕的上海,一群麻雀般辛苦謀生的平民房客和一個烏鴉般貪婪兇狠的官僚房東斗智斗勇,最后房客取得“勝利”的故事。影片折射出國民黨與老百姓的矛盾,也宣揚了個人力量有限、集體才有力量的思想。那是解放前夕,是最樂觀的時候。在電影的最后,描述國民黨的官員偷偷到香港去了,房客們都很興奮,說國民黨走了,共產黨就快來解放我們了,我們要迎接新社會了。
《決裂》,1975年上映,主演之一是葛存壯,是歌頌“文革”的電影。其中有一個很有名的鏡頭——“馬尾巴的功能”,在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老師在講臺上講“同學們,今天我給大家講一講馬尾巴的功能”,下面有一個學生就站起來發難了:我們為什么不講一講牛尾巴的功能呢?因為在學生看來,南方沒有馬,只有牛,所以教授是“理論脫離實際”,后來貼了大字報批判這個教授。于是得出結論:教授不如老農,課堂不如田野……
《霸王別姬》,故事的時間跨度從1920年代到1977年,表現了中國社會的歷史過程。我特別喜歡“文革”時期那段:誰都不信任誰,誰都背叛誰……表現得非常好。
《頑主》,1988年首映,是根據王朔的小說改編的電影,描述三位無業青年在北京開了一家“三T公司”,專門替人解難、解悶、受過。我后來把這個劇本翻譯成英文,與王朔在北京一起吃過飯,他看我翻譯的英文劇本,但他英文不好,只認識一個“China”。電影有一個非常有意思的鏡頭,就是在迪斯科有一個時裝表演,出現了各種各樣的人物,有清朝的官員、國民黨的官員、共產黨的官員,有地主、貧下中農,還有當年的潮流青年朋克一族……各種各樣的人,甚至敵對的,音樂一開始,都一同跳起了舞,好像一家人。我想它要表達的意思是:中國的歷史太復雜了,都算了吧,我們重頭再來吧。1988年是中國的過渡時期,很開放。
《盲井》、《盲山》。《盲井》于2004年上映,講述了一個發生在礦區的故事:兩個生活在礦區的閑人靠將打工者誘騙到礦區并害死在礦井下,再向礦主索要賠償來賺錢。金錢讓兩人喪盡了天良……但在一個小男孩成為他們的目標之后,其中一個謀殺者的感情發生了變化,為了保護那個16歲的小男孩,這個謀殺者與他的同伴發生沖突,最后死在深深的礦井下。《盲山》于2007年上映,與《盲井》一脈相承,以紀錄片的形式講述一個女大學生被拐賣至某法盲山區,多年后被解救的故事(在國際流傳的李揚的最初版本中,女大學生并未被解救)。這個系列片的導演李揚正在創作第三部作品《盲流》,是關于農村小孩到城市來的。我認為這一系列電影展示了中國發展帶來的一些壞現象,表現了社會和人性“盲”的一面,也是在一個特定的年代國家影響普通人生活的反映。
《非誠勿擾》(導演:馮小剛)和《南京!南京!》(導演:陸川)是我近期給學生看的兩部電影,學生很喜歡《非誠勿擾》,我也曾邀請馮小剛到我的課堂展示他的電影。
《同舟共進》:您有喜歡的中國導演嗎?
駱思典:我喜歡謝晉,喜歡他導演的《天云山傳奇》多于《鴉片戰爭》。我曾請他到我的公寓,討論他的一部還沒完成(也不會完成了)的電影。但他告訴我,我1980年代以前的電影你不要看,那時我不是很自由。他那個時期的代表作是《海港》。但他1960年拍的《紅色娘子軍》我還是挺喜歡的。
我也很喜歡賈樟柯,他和李揚都是中國第六代導演,他們用電影鏡頭記錄了平民百姓的生活。
《同舟共進》:對于中國電影在海外的發展,您有什么看法?
駱思典:這里我談一部電影《功夫熊貓》,我認為這部電影給了中國一個教訓——功夫和熊貓都是中國的東西,為什么是好萊塢拍這個片?我想,如果由中國來拍,熊貓不可能那么胖那么懶,因為熊貓是中國的象征。陸川在看完《功夫熊貓》后也曾呼吁“把熊貓還給孩子們”。中國電影審查制度太嚴厲,太強調“政治正確”,是不利于電影發展的。中國拍電影有三個原因:一是商業,二是藝術,三是政治,即所謂的主旋律。而好萊塢最看重的只有一點,就是商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