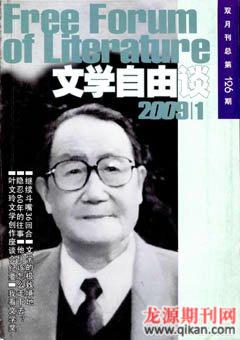究竟是誰中了毒?
趙月斌
前陣子,有位詩人,猛然宣稱:“文學死了”,并在文章每個段落的開頭都如是大叫一聲,以此召布天下:“文學,這只舊時代的恐龍,這個曾經傲視其他文字的龐然大物,它已經死了。”
據粗略統計,算上該文的標題,在不足三千字的篇幅里,該聲大叫共計重復13次。
但是,詩人仍嫌不夠過癮,緊接著,又開出一份死亡報告,羅列了中國當代文學的十幾種死狀,昭昭佐證出熱氣騰騰的中國當代文學,僅是一具“軀體正在腐爛”的華麗的僵尸——“文學,不再有現在,也不再有將來。”
正當我等驚魂甫定,不知所措之際,詩人突然又將話鋒一轉:他所說的“文學死了”,是指“源于西方的那個文學觀念與文學系統,在中國公眾生活中的徹底死亡”。
鬧了半天他只是在為假洋鬼子發布訃告。
盡管他宣稱“文學死了”是“一種思想”,是一個“真問題”,盡管他已親自把“文學這具尸體”運進了停尸房,并且號召大家一起默哀,但是詩人似乎察覺到他先前的診斷結果失之輕率,有草菅“文”命之嫌,所以才鄭重發布這么個補丁,告訴大家:中國當代文學最多只是心跳驟停而已,還沒發展到腦死亡的地步。
原來,詩人只是說話也喜歡另起一行而已!
原來,詩人對于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學,其實深懷感情,哪能讓它隨隨便便就去“死了”呢?
而且,這一次,為了“向死而生”,為了拯救奄奄一息的中國文學,他慨然開出一劑大處方:讓“西方文學觀念”去死吧,讓“中國傳統文學觀”在“當代文化語境中”重新復活,將“中國的傳統文學觀”發揚光大,以此拯救“死去的中國文學”。
本以為這位“詩性學者”真能掏出幾粒起死還魂丹呢,卻原來只是在兜售他的排毒膠囊,似乎只要肅清了西方觀念的“流毒”,中國文學的煌煌大統馬上就可重建。
認為中國文學過于西化,缺少中國特色,這一論調其實并不新鮮。諸如此類的觀點在評論界幾近“共識”, 甚至,在一些人看來,中國文學自新文化運動以來便籠罩在從西方舶來的思想觀念中,缺乏“中國式的人文精神”以及“對民族文化精神的大信”;中國的精英文化習慣于使用關于“靈魂”的想象,中國作家亦喜歡拿“希伯來靈魂”說事,少有以傳統的審美方式表達出來的中國式體驗。所以,才有論者指出:相對具有宗教背景的西方文學,中國文學明擺著先天不足,只是一味地東施效顰、邯鄲學步,既丟棄了大好特好的傳統,又無法跟上西方的步伐,結果就產生了一批又一批半吊子,有畫虎不成反類犬之嫌,好像中國作家飽受西方文學的毒害,好像他們大都在用漢字寫作一種不倫不類的“外國文學”。
果真如此么?所謂西方文學觀念真的是把中國文學殘害得半死不活的罪魁禍首?是不是像那位“詩性學者”和一些評論家所認定的,中國文學已經背離了傳統,其主流一直是“靈魂”意義上的文學?而只有重新用所謂的“中國之心”、“中國情懷”去繪制、發掘現代生活,才是令當代文學絕處逢生的必然出路?
讓我疑惑的是,在一百來年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中,像施蟄存寫作《石秀》那樣講究弗洛伊德式的深度剖析、追求所謂希伯來式靈魂的作家、作品占多大比例?是否只是鳳毛麟角?上世紀30年代初倒是出現過“新感覺派”,但是他們的衣缽似乎乏人繼承。至于80年代被視為于傳統最為離經叛道、于西方最為慨然拿來的先鋒小說,又庶幾近乎語言、文體實驗。即便在形式上“西化”了、“現代”了,我們的文學還是一只老狐貍,無論它把皮毛染成什么色,身上流的還是中國血,對所謂“靈魂”的訴求好像并無多大可觀,更遑論成為“中國文學主流”了。
當然也不能否認,也有若干中國作家鐵了心要與國際接軌,鐵了心要“現代化”、“后現代”,但是這樣的作家才真正少而又少,如果尋找證人,似乎只有殘雪差可勝任。她曾坦言其思想感情像從西方文化傳統里長出的植物,并聲稱要在手法上、寫作的深層結構上、理念上都要全盤西化,才能使中國文學前進。再結合她的作品,更可見其“中毒”之深。她認定我們的傳統文化里沒有精神內核,中國文學要站立起來,就必須向西方學習。她所說的精神內核就是“靈魂”——當然又與所謂希伯來靈魂有所區別,她毫不諱言寫作就是對靈魂世界的探尋,因此,她譏諷那些“回歸傳統”的作家“自卑”,她堅信自己“走在時代的前面……通過在創作中批判我們的文化,將消極面奇跡般地轉化成了積極面,創造性地挽救了垂死的傳統”。但是這種自覺的“靈魂寫作”,并未進入評論家的視野,他們所稱的“主流”,好像也難將殘雪統計在內。殘雪不是說國內只有三個和她類似的作家嗎?三四個這樣的數量,作品又難以出版,其影響力可想而知。
再來看我們的主流文學,自“五四”以降,究竟有多少人擺脫了“傳統”?
魯迅以寫作深挖國民劣根性,老舍到美國走了一遭還是歸于“京味”,即便沈從文、張愛玲這樣的非主流作家,一個心系邊城,一個神浸沉香,還是與傳統的中國情懷與中國之心一脈相承。及至當前被眾多作家尊行的“弘揚主旋律”、“為老百姓寫作”、“描寫下層人民的生活”(“底層敘事”、“打工文學”)、“三貼近”等原則、觀點,也都是傳統的“文以載道論”的進一步發展。僅以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歷屆的獲獎作品為例,從《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到《歷史的天空》,從《趙一曼女士》到《一個人張燈結彩》,即不難看出,我們的作家不但沒有遠離傳統,而且很傳統,很中國。以其中極負盛名的《白鹿原》來說,雖然作者陳忠實也自陳從《百年孤獨》中得到過啟示,但是除了那個“引以為豪壯”的開頭,又能找到多少馬爾克斯的影子?它所呈現的只能是所謂的“中國情懷與中國精神”。再如未曾獲獎的《檀香刑》,不也是以“傳統”見長?莫言不僅在結構形式和語言風格上刻意本土化,而且注重小說的社會功能,使其成為書寫傳統文化的大制作。還有張煒的《古船》,盡管其中的隋抱樸常年研究《共產黨宣言》,但是小說所體現的傳統精神、社會意義、歷史價值,卻是地地道道的中國氣派。
面對聽眾的提問,嘗有論者感喟:像莫言那樣具備“中國之心”“中國情懷”的作家實在是太少了。可是,果然太少嗎?在我看來,魯迅、老舍寫出的“國民性”、京味小說,或正是“中國之心”;沈從文、蕭紅、張愛玲筆下的邊城、呼蘭河、上海往事,或也有“中國情懷”;即如韓少功乃至殘雪的作品,竟或也含藏“中國之心” 、“中國情懷”。為什么諸多評論家都叫嚷中國文學缺少民族性呢?為什么他們憂心忡忡地認為中國作家的總體趨勢是向西方投降呢?為什么他們看不到那或多或少或美或丑的“中國情懷”、“中國之心”呢?舉凡當代中國作家,絕然不只莫言能夠胸涌“中國情懷”回到鄉野,回到民間,表達出對世界渾樸、自然、直接的感受,絕然不只他能觸摸到“中國之心”。這樣的作品閉上眼便能摸出一大堆,只是有的尚可一覷,有的不忍卒讀而已。像賈平凹和他的新作《高興》(也可包括以前的舊作),難道還不夠“傳統”嗎?簡直太傳統了,寫農民進城,塑造“新農民形象”,對所謂小人物、底層給予溫情的關注,老賈義不容辭地充當了“宏道”之人,不正可充當評論家們所呼喚的中國文學之“大家”嗎?
那么,為什么眾多評論家都要宣稱所謂“靈魂意義上的文學”已然成為中國文學的主流呢?若是引用幾句《圣經》,叫幾聲上帝,安幾個靈魂,就算作西式的“靈魂”建構,未免太抬舉了那樣的作品。檢點一下曾經過眼的小說及作家言論,除了有人在小說里引過幾句《圣經》,有人說過幾次關于耶穌、天國、窄門、寬門的話,似乎只有北村的《和上帝有個約》以“源自希伯來傳統的神學框架”為依托,找到了“用來發問的立足點”,并以此獲得了某些評家的肯定。也就是說,在當今中國,真正像模像樣地操持希伯來語法的作家,實在少得可憐,像北村這樣克服了語境的困難,寫得像那么一回事的,更是極度稀缺。要我說,這年頭,還有幾個人顧得上“和上帝有個約”?充斥耳目的多是廣告文學、欲望文學、微笑文學、變態文學……少見的偏偏是與“靈魂”有約的文學。當然也不排除還有一部分作家,他們也在急三忙四地翻《圣經》,也在挖空心思地畫靈魂、寫救贖,他們目的無非是拔高度、裝深沉,也蒙那幫舉著探照燈找“靈魂”的評論家。
“中國文化中精神的缺失導致當今的文學不能生長、發育,就像一些長著娃娃臉的小老頭,永遠是那么老于世故,永遠能夠自圓其說,具有世界上最出色的匠人的精明,卻惟獨沒有內省,沒有對于自身的批判。”這是殘雪對傳統文化提出的批評,太老,太傳統或許正是當代文學的癥結所在,雖然我并不完全贊同她說的“全盤向西方經典學習”,但是我相信中國作家根本欠缺的,絕對不是惟用、惟道、惟命等等這些傳統中老于世故的“大統”,而是對這些“大統”清醒的自覺與審查。一味地回歸“傳統”,執拗地張揚“大信”,好像一經“自我的體認與修養”便“人人皆可為舜堯”,這種中國式的“人文精神”果真這般好用,為何還有那么多沒有“人格”的人和沒有“人格”的文學?這種把自我供成圣人的“大信”,除了助長自私和虛妄,真能造就“大家”么?傳統中有實用,也有夢想,有形下,也有形上,有自足,也有缺欠,我倒是希望中國文學能夠沖破這些“大統”,重新發現那個被擠壓、被掠取、被掩蓋、被塵封了的真正的“中國情懷”與“中國之心”。
重建“大統”,是不是太過自戀(反過來也是一種自卑)?為什么老有人說中國作家在整體上跑偏了,偏到所謂西方建制上去了?莫非中國作家只要斷絕了不清不白的海外關系,就會在偉大祖國的懷抱里茁壯成長,結出光輝燦爛的果實?
問題絕非這樣簡單。
在我看來,評論家們之所以得出他們的西化主流論,要么是故意危言聳聽,要么就是因為,他們故意只看到那么幾個“代表作家”,借以高屋建瓴,發表他們的宏論。當評論家只關注那么幾個合口的作家,作家只盯著那么幾個評論家的臉色時,中國主流文學除了在作家和評論家之間曖昧地媾合,或者隔著十萬八千里自說自話,還能指望它做出什么好事?
而且,如果非要說西方的思想觀念有毒,那么,搶先中毒的,直接中毒的,中毒最深的,恰是某些搞理論搞批評的。是他們操著混亂的語種拿著混亂的標尺,把中國文學嚇傻了攪渾了。并不是中國作家寫出了夾生的“外國文學”,而是中國的文學評論家慣常借用西方的腦筋審思中國文學,慣常寫作一種隨時可能夾雜著簡裝英語的洋涇浜文論。
所以,中國的評論家談論中國文學,最拿手的本領就是套用西方的文學理論、思想觀念。他們給中國文學或掛上十字架,或披上燕尾服,再將其一股腦趕進他們蓄意編織的籠子中,就如同施展了障眼法,兼且言之鑿鑿,再經歷久日深,故而乍眼看去,中國文學好像真的已經大面積、大規模地“洋化”。不僅場外的觀眾,連同裝在籠子里的模特兒,都毫不含糊地相信:西方文學的毒素不僅已經疾在中國文學的肌膚腠理,而且滲入腸胃骨髓,庶幾“無奈何也”。于是,造籠子的評論家又反過來指責中國文學不夠中國,所以必須打碎籠子,把披掛在中國文學身上的洋玩意兒盡皆毀掉。這才是中國當下文學創作與文學評論的現實,事實上正是評論家過于沉迷于來自西方的理論建構、學術標準,喜歡拿捏著洋腔洋調說話,才為我們涂抹出一幅玄虛不實的文學圖景,而終至“文學死了”。
就如那位喜歡判死刑的詩性學者,他借已立論的依據卻正來自西方。當他試圖穿上“傳統”的長袍時,還沒來得及把西來的“毒藥”洗掉,所以我們看到和聞到的只能是半生不熟的“古典大統”和揮之不去的貼牌香水味。在那篇呼喚重建“大統”的文章中,僅四千余字,“文本”一詞先后出現了27次。在八百字的段落中,他就能左一個德里達,右一個福柯,僅直接引語就有二百多字,用所謂解構主義、結構主義、后現代來談中國文學的大統,用“文本”、“話語”、“三位一體”來講中國古典文學,果是饒有趣味,確然耐人尋味。
再如被評論家目為舶來品的“希伯來靈魂”,不正是常掛在他們嘴邊的一道可口菜嗎?有強調“靈魂寫作”,強調民族靈魂的發現和重鑄的;也有提倡“靈魂敘事”,提倡靈魂救贖的……一些堪稱“寵然大物”的評論家,難道不正是靈魂理論的積極“建構”者,怎么沒人指責他們跑偏了呢?更為吊詭的是,有的評論家在反思抨擊過西方建構之后,似乎很快就忘卻了他要提倡的中國氣派,反又不厭其煩地“拿來”和運作“靈魂”。他們在發表言論時,還是常常懷著極高的期待,到中國的文學作品中捕捉“靈魂”。他們慣用的、喜用的還是希伯來的靈魂話語——不排除這些“靈魂”都有其特定語境,但是無論他的字面意義是什么,我們都有理由說,評論家的確在為非國產的靈魂“構建”添磚加瓦,他們才是鼓吹中國文學追趕靈魂的領喊者。當評論家的興趣僅限于制造種種“說法”、制造種種新術語、新名詞,不僅不尊重文本,而且不尊重自己制造的“成果”,今天這么說,明天又那么說,剛提倡過精神敘事,又去批判靈魂敘事,剛提倡過“中國之心”,轉過來又批評人家不夠“靈魂”,這種只有立論沒有立場的評論能有多少力度和信度?評論家們看到了中國作家的“分裂”,怎么就沒看到文學評論的“分裂”?
許多文學評論家正是這樣,一邊罵中國作家分裂,罵西方觀念該死,一邊卻拔下人家的卷發,做成假發戴到頭上,充當起義正辭嚴的大法官來。他們擺出“中國文學之假”作為假想的受審者,好像真的握有絕對真理,占據了絕對的道德優勢和理論優勢。可是我要問的是,應該出庭的究竟是誰?在審問別人之前,作為公訴人的法官大人是不是應該先審審自己?
那些高深莫測的藝術理論,那些又是建構又是重構又是解構又是語義學符號學敘事學又是人性靈魂終極價值……等等說法,哪一個不是我們的理論家、評論家從外邊倒騰回來的?中國作家的一大特色就是大多師出無門,不少人沒受過正統的學院式文學規訓,很少有人系統或深入地研究過西方理論,有的也只是吸點虛無縹緲的“二手煙”,間接地受點“毒害”。他們之所以被抱怨太過西化,盲目崇拜“西方文學觀”,大部分功勞要歸于理論家、評論家。正是我們的一些專家學者,無私地傳播了他們的西方觀念、西方標準,才使中國文學陷入一種白馬非馬的尷尬境地。評論家本人對傳統就說不出多少所以然來,他們自身就缺乏解讀“傳統——中國之心”的功力,卻單單指責中國文學被西方文學觀念侵略了、殖民了,這是不是有點養虎為患的味道?我無意指責那些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的開路者,只是想說明:一方面,評論家在用西方話語模式、西方評價體系來解讀、評判、校正中國文學,將其誘引到他們設計的迷津中;另一方面,他們又反過來說中國文學偏離了跑道,掉到了希伯來式的陷阱中……究竟是誰中了西方的“毒”?
在我看來,當今中國文學并不缺乏“中國式體驗”,缺乏的或許只是作家對這種體驗的把握力和表現力,以及批評家對作家作品的感知力和理解力。在這里,我無意評價“靈魂敘事”、“中國之心”孰優孰劣,只想表明:按下中國文學是否過分希伯來靈魂不說,只說評論家是不是具備了評價中國文學的“中國之心”?我們的評價系統、審美尺度乃至價值標準是不是立足于本土,夠不夠“中國特色”?如果你本人戴上了進口墨鏡,便看什么都是洋的、不順眼的,便把自有的和“拿來”的一并斥為外來貨,反罵人家沒有中國情懷、中國精神,豈不是一種無理的話語霸權?
由此可見,文學理論家的任務不應只是制造“宏大聲音”,不應只用某種論調去調戲、奚落中國文學,為中國文學去偽存真、探索和發現它的可能性才是理論家之正途。作家、理論家都不該偷偷摸摸地勾勾搭搭又明目張膽地同床異夢,只有雙方相互敞開了心靈,放寬了眼界,才有可能發現中國文學的拐點與隱秘,從而上揚真正的中國傳統,煉出真正的“中國之心”。
現在,有人喊過“西方文學觀念死了”之后,究竟什么還活著,什么已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