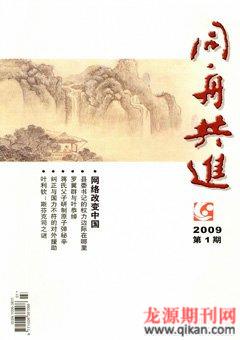改變中國:靠制度?靠道德?
秋 風
19世紀末以來,中國人一直被一個焦慮折磨著:怎樣實現現代化?不同人對現代化有不同的理解,于是,形成了社會變革的形形色色的理念,其中尤其重要的一個爭執是:究竟是文化、道德決定制度,還是制度決定文化、道德?這一爭論持續了百年,過去半個世紀,處于劇烈變革時期的中國,仍在苦苦尋找這一問題的答案。
“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曾經的烏托邦
官方哲學主張物質決定論,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只要生產力發展了,人們的意識、觀念及社會政治結構就會發生變化。此外,意識反過來也可以影響物質。極少數人作為先知先覺者,可以用先進思想改造群眾,精神一旦完成革命,就可以煥發出無窮力量,所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
這是現代中國革命傳統的主要哲學依據。它強調在每個人靈魂深處爆發革命,認為通過改造人的思想,可以建成新社會。
上世紀70年代末,這種烏托邦理想破滅了。上世紀80年代是一個反思的年代,部分人把“文革”之禍歸咎于中國有幾千年的專制文化傳統。他們認為,西方文化從希臘時代開始就是民主的、科學的,這樣的傳統注定了西方會建立起現代憲政制度,而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就必須徹底拋棄自己的文化。
其實,這種文化決定論并不是新東西。陳獨秀、胡適等人都曾對中國文化傳統痛加批判,認為中國的落后是因為文化落后。新文化運動時有人主張把中國書扔到茅廁,為1980年代劃上休止符的《河殤》則要中國全面轉向西方的藍色文明。
進入上世紀90年代后,人們又放棄了文化決定論,進入了制度決定論時代。隨著市場經濟獲得承認,比較強調制度的決定性作用的經濟學和法學成為顯學。制度決定論認為:治理國家的關鍵是設計合理的制度。好制度能使壞人變好,壞制度則可能使好人變壞。
因此,只要碰到社會問題,輿論馬上就呼吁改進制度。正是在這種思考方式的引導下,過去十幾年來,中國在建設現代國家制度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包括承認私人產權、市場制度、民主與法治制度等。
不過,在法治國家運轉良好的制度,在中國有時卻產生了令人失望的后果。制度決定論者相信,橘變為枳的原因是,優良的制度如果缺乏相應的制度配套,效果會大打折扣,甚至適得其反。因此,唯有進一步完善已有制度,并引入配套制度。
這種認識是正確的。然而,如果扭曲的制度使人的行為也趨向扭曲,那么,生活于不合理制度之下的人有沒有可能進行變革,變革的動力何在?面對這樣的問題,制度決定論陷入某種困境。
于是,過去十幾年來,誰來進行變革這樣一個重大問題被省略了。假如非說不可,一位年輕學者給出的答案非常有代表性:“我們就有理由期待,當人群中哪怕是個別道德感較強的人恰好出現在某個關鍵決策部門時,他也許會給我們的制度改革帶來關鍵性的第一推動力,正如鄧小平對于當初的改革開放所起到的關鍵性推動作用一樣。”
這真是奇妙的邏輯跳躍:制度決定論突然變成了英雄創世論。當然,誰也不能排除出現這種“第一推動者”的可能,但把國家的前途交給偶然的命運、運氣,顯然是很不靠譜的事。
難能可貴的“立法企業家”
制度決定論的一個嚴重缺失就是假定制度自己會變革。其實,制度不可能自天而降,也不可能自行變化。相反,制度是人創造的,也是由人推動著變化的。
人的變革意識從哪里來?它源于人們的道德感:人們是因為覺得現實不“好”才形成變革意識的,而好、壞是由人們的道德和價值觀決定的。現有制度不合理,所以人們希望變革。但是,不合理的制度必然造就一些依附它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反對損害自己利益的變革。有些時候,變革者甚至可能面臨巨大風險,包括殺身之禍。這時,能否堅定地變革,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們的道德勇氣,亦即求善的意志。只有當這種意志壓倒了人們的擔心、恐懼,變革才會付諸行動。
舉例說,假設政府不合理地禁止企業進入某個領域。面對這樣的規則,企業家大體可在四個策略之中進行選擇:第一,放棄進入企圖;第二,賄買管制的官員,購買進入的特權;第三,不理睬該規則而自行交易,形成黑市;第四,要求改變規則,放開市場進入。
選擇第一種策略的企業家既無強烈的是非感,也缺乏道德勇氣。選擇第二種策略會使舊體制更堅固,官員從不合理的管制中獲得利益,傾向于維護與擴大管制。第三種選擇倒是形成了市場,但這個市場沒有穩定的規則,人們的行為必然短期化,隨時可能毀滅。
唯一可取的是第四種選擇。但這需要雙重勇氣,首先是放棄從不合理制度中尋租的勇氣,其次是改變不合理制度的勇氣。他們之所以放棄,是因為他們具有較為強烈的是非對錯觀念:賄買官員在道德上是不正確的,黑市也不是正派人應當進入的。他們之所以選擇變革,是因為他們希望正當地進入市場,更因為他們認為,政府不應實施不合理的管制,而應當做正確的事。
他們就是所謂的“立法企業家”。這些企業家獻身于理想,就像科學家獻身于科學事業。他們不僅僅是進行利益的計算或“算計”,他們還有長遠的視野,追求金錢之外的東西。一個社會在任何時候,都不能缺少這種有道德情操的人,他們有力地推動著社會的變革。
避免跌入“道德理想國”深淵
制度決定論者對此可能不以為然。只要有人談起道德,他們馬上聯想到人類歷史上道德理想主義所導致的可怕災難。這種擔心有一定道理。不過,在人類歷史上,同樣可以找到道德推動社會變革,但又保持克制,沒有墮入道德理想國深淵的例證。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說,美國幾乎人人信仰宗教,人們具有強烈的道德感,但美國并沒有成為人們所擔心的道德理想國。托克維爾指出了其中的秘密:在美國,道德世界與政治世界是分立的,宗教不去干預政治,權力也不去支配宗教。由此形成一種奇妙的格局:一方面,在政治世界,“政治的原則和一切人定的法律與制度都可以依自己之好惡制定或改變”;但另一方面,人們克制自己不進入道德世界,相反,不加思索地接受宗教的信念。美國立憲過程鮮明地體現了這一點:立憲者對權力進行分解、搭配,設計了全新的政府形式,但他們從來沒有討論過美國的文化、宗教、價值,而是把這些當成既定的東西予以接受。
恰恰是這些既定的“民風”,即宗教、道德、倫理規范,使美國人具有基本的道德感,克服其個人主義傾向,面向自己的靈魂,面向自己的同胞,關心他人,與他人合作,結成各種各樣的社會組織,進而參與公共事務,改進制度。
托克維爾認為,制度同樣是重要的,但沒有道德激勵,社會的良性變遷是不可想象的。不過,道德雖然重要,但并不需要人人成為圣人,因而不需要進行思想改造和靈魂革命;相反,只要具備基本的道德感、是非感,比一般人好一點點,對不道德的行動、規則有那么一些敏感的“一般的好人”就足夠了。這樣的好人是理性而務實的,他們不想改造別人,只是想讓社會真正能夠優勝劣汰,讓壞人受到懲罰,讓好人得到好報。這自然會反過來強化人們的道德和倫理,誘導人們遵守規則,采取正當行為。
今天,中國社會要維持良性運轉、推進制度變革,所缺乏的不是圣人,而是一般意義上的“好人”。人們可以設想,如果企業家有一點點人性,就不大可能發生毒奶粉事件,如果企業家還知道一點點社會禁忌,就不會發生百度霸王搜索事件。人們總是呼吁制度變革,但可能恰恰忘記了:自己就是制度變革的動力所在。
也許,推動社會變革,制度與道德誰更重要的爭論仍將繼續下去,而且可以預料,這一問題不會有唯一正確的解答。然而,在道德問題屢屢為人詬病的當下,確實需要那么一批有道德勇氣、懷著美好愿望而又具有理性精神的人,去推動整個社會制度的良性轉變——所幸,在當代中國,不乏這樣的人。
(作者系憲政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