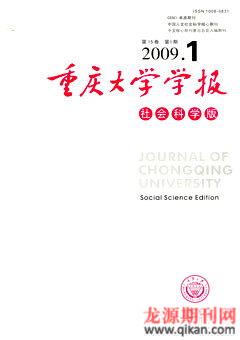論亞洲文學區域的形成及其特征
王向遠
摘要:亞洲有三大文學圈:東亞地區的漢文學圈、南亞東南亞地區的印度文學圈、西亞中東地區的伊斯蘭文學圈。這三大文學圈既具有相對獨立性,也具有相互關聯性與相互重疊性。三個文學圈以宗教傳播為驅動力,各自不斷地從中心向外延伸擴散,最終在各自的邊緣處互相疊合,最終“三塊連成一片”。由此。亞洲文學區域得以形成。如果說歐洲文學區域具有“兩點(希臘、希伯來)連成一線”的“同源、單線演進”的特征,呈現“y”狀結構,那么可以說,亞洲文學區域則呈現出“三點擴散、漸次重疊,連成一片”的特點,在結構上猶如三個邊緣相接的圓環。
關鍵詞:文學區域性;亞洲文學區域;文學圈;比較文學
中圖分類號:I3-1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8-5831(2009)01-0116-05
一、漢語文是東亞各國傳統文學的血脈
漢文化在東亞文化中的核心輻射作用經歷了兩個步驟。首先是大陸地區對周邊少數民族的逐漸影響與同化。性情溫良的南方少數民族在與漢人的長期交往與接觸中,自然而然接受了漢文化的影響,并逐漸地、不同程度地融入了漢文化乃至中華文化之中。性情暴烈的北方地區以游牧為生的各少數民族不斷入侵中原,漢人在被動防御與積極抵抗的過程中,使漢文化在北方塞外地區得以擴散。由于軍事取勝而入主中原的蒙古人、滿族人,則在文化上被漢文化所征服。自動地全盤接受了漢文化。于是,在亞洲的東部大陸,逐漸形成了幅員遼闊的先進的漢文化本土地帶。它像一個巨大的磁石,對周邊民族的海島、半島地區的東亞民族國家,包括朝鮮半島、日本列島和中南半島東部的越南等,都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也為這些東亞國家學習中國提供了巨大的推動力。儒家思想及中國的社會政治倫理學說,可以為東亞各國建立中央集權國家、建立和諧的社會秩序與人倫關系提供思想理論基礎;印度傳來經中國翻譯改造后的佛教經典,又可以為東亞國家提供完備的宗教信仰體系。而學習和接受這一切,首先就需要學習漢語,學習漢語,必然就會接觸到漢文學。對漢字漢文的引進、改造與使用,為“東亞漢字文化圈”及“漢文學圈”的形成提供了先決條件。
漢字和漢文的東傳,對于當時沒有民族文字的韓國、日本、越南的文化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起初三國都沒有自己的民族文字,都直接使用漢字,并利用漢文進行文學創作,于是漢語文就成了東亞各國的共同語文。后來,三國先后參照漢字創造了各自的民族文字,并產生了民族文字的文學作品。但即便如此,漢詩漢文的創作卻沒有因為其民族文字的創立而停止。越南的漢文創作一直持續到18世紀,日本與韓國漢詩漢文的創作一直延伸到20世紀上半期。這些創作成為他們民族文學傳統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進入近現代以后,由于中國的落后與文化吸引力的喪失,漢字和漢文也受到冷遇,韓國與日本都曾試圖廢棄漢字。但由于漢字文化尤其是漢字詞匯已經深深地滲入到三國的語言文化中。完全廢棄非常困難。日本方面經過調查研究,認為漢字詞匯太多,如果不使用漢字標記則可能不知所云,因而無法廢除,只是采取了限制使用漢字的政策。在朝鮮文字中也同樣保留了大量的漢字詞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北朝鮮完全廢棄了漢字,南部韓國也幾度廢棄又幾度啟用漢字。但即使廢棄了漢字,其中大量的漢語詞匯卻無法廢棄,且發音上與漢字發音有明顯的對應性。越南的文字拼音化后,也保留了大量的漢語詞匯與漢文化典故意象。如今朝鮮、韓國乃至越南,仍屬漢字文化圈無疑。關于漢字在東亞文明進程中的作用,胡適在《白話文學史》中曾做過很好的概括,他寫道:
我們的民族自從秦、漢以來,土地漸漸擴大。吸收了無數的民族……這個開化的事業,不但遍于中國本部,還推廣到高麗、日本、安南等國。這個極偉大的開化事業足足費了兩千年。在這兩千年之中,中國民族拿來開化這些民族的材料,只是中國的古文明。而傳播這個古文明的工具,在當日不能不靠古文。故我們可以說,古文不但做了兩千年中國民族教育自己子孫的工具,還做了兩千年中國民族教育無數亞洲民族的工具。
在一兩千年的歷史時期內,漢語不僅是朝鮮、日本、越南文學創作的共通用語,并且出現了“東亞漢文學”這樣一種東亞共同的文學形態。據王曉平教授在《亞洲漢文學》一書中的研究概括,在一千多年的歷史發展中,東亞漢文學大致出現過四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現于8至10世紀日本的奈良與平安兩朝的貴族漢文學,以宮廷為核心,以漢唐文學為模仿對象,用漢文修史(如《日本書紀》),用漢文作文(如《經國集》、《本朝文粹》、《本朝續文粹》等),用漢語賦詩(有《懷風藻》、《文華秀麗集》等)。同時期朝鮮半島駢儷文風正盛,古體近體詩多有佳構。而越南使用漢語文體也大局初定。第二次高潮,以12至17世紀的高麗為代表,作者的基本構成是以科舉制度為依托形成的文人官僚集團。模仿陶詩韓文,推舉蘇黃,稱揚梅歐,詩話初興,文集大備。越南的李、陳兩朝,尊佛友道,詩文取士,詩多禪語,文尚麗辭。日本在平安貴族漢文學陷于停滯并歷經多年戰亂的情況下,以遠離政壇的佛教五座名山的寺院為中心,形成了著名的“五山文學”。第三次高潮為15至17世紀,是程朱理學文藝思想的光大期,各國漢文學發展水平逐漸接近。日本的漢文學則處于中古與近世的過渡期,漢詩創作不絕如縷。朝鮮李朝崇儒抑佛。載道宗經,學奉朱子,詩尊李杜,文人散文筆記大量涌現,在中國的《剪燈新話》影響下,出現了《金螯新話》等一批文言傳奇。越南也出現了《傳奇漫錄》、《傳奇新譜》等漢文志怪小說。第四次高潮在18至20世紀初,是明清文學的呼應期,也是各國漢文學的全盛期。明代擬古文學與唐宋派、性靈派先后在日韓引起連鎖反響,漢文學進一步由宮廷寺院走向尋常街巷。日本江戶時代獨尊儒學,漢詩文創作出現繁榮。朝鮮李朝后期唐宋派古文與主張社會改革的“實學派”漢文學各擅其長,漢文小說與文人筆記十分繁盛。在正統的詩文之外,隨著中國白話小說的流傳,在日本、朝鮮與越南,都出現了一些中國白話小說仿作與翻改作品。19至20世紀初,東亞各國漢文學由蛻變走向衰微,日本明治時期的漢文學卻攀上最后的高峰而后跌入低谷。幕府末年志士以詩明志,明治初年,新聞出版繁榮,報刊雜志競載漢詩文,也有試圖以漢詩文表現西方新觀念新思想者。直到1920年,漢文學才黯然退出近代文壇。越南、韓國隨著科舉的廢止、新學的建立以及文字的變革,漢文學衰微,創作和欣賞漢文學成為少數學者與文人雅士的專利。
漢語及漢文學對東亞各國文學的影響,不僅體現在語言與文體的層面,也體現在作品題材的層面。對漢文作品的閱讀,使東亞各國文學運用中國題材進行創作提供了可能,使以中國為背景、以中國人為主人公的中國題材文學,構成了一種源遠流長的創作傳統。在朝鮮,17世紀以反映朝鮮與中國明朝聯手抗擊日本侵略的壬辰戰爭為題材的歷史小說《壬辰錄》,也描寫中國軍隊及其將領,甚至《三國演義》
中的關云長也出現在戰場中吶喊助戰。18世紀著名的文人長篇小說《謝氏南征記》、《九云夢》(有朝文和漢文兩種版本)和《玉樓夢》、《淑香傳》等皆以中國為題材,背景與人物都是中國和中國人。越南古典文學的翹楚《金云翹傳》,在題材上采用的就是中國的同名長篇小說。中國題材在日本文學中更為重要。筆者在《中國題材文學文學史》一書中曾指出:中國題材的日本文學已經有了長達一千多年的歷史傳統,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沒有中斷,至今仍繁盛不衰。中國題材既是日本文學不可或缺的營養與資源,也是汲取中國文化的重要途徑和環節。中國題材對于日本漢詩漢文這樣的“外來”文體是重要的,對于“說話”、“物語”這樣的日本文體也同樣重要。例如,在12世紀短篇故事總集《今昔物語集》的天竺(印度)、震旦(中國)、本朝(日本)三部分中,不僅“震旦”部分十卷共一百八十多個故事全部取材于中國,就連“天竺”部分的五卷也是間接從中國漢譯佛經、中國佛教類書中取材。“本朝”(日本)部分的佛教故事有許多也受到中國的影響。不久之后。則出現了《唐物語》那樣專門的中國題材的短篇物語集。14世紀成熟的日本古典戲曲“能樂”所流傳下來的現存240種能樂劇本(謠曲),從中國取材的就有二十幾個,占總數的十分之一。日本近代文學盡管不再以中國為師。而是追慕和學習西方文學,照理說在這種大語境下中國題材應該從日本文學中淡出,但事實恰恰相反,近現代日本文學對中國題材的攝取,反而比傳統文學更廣泛、更全面,從事中國題材創作的作家更多,中國題材的作品更加豐富多彩,中國題材日本文學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中國題材日本近現代文學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打破了古代文學缺乏中國現實題材的局面,中國現實題材開始大規模進入日本作家的視野,現實題材與歷史題材的齊頭并進、雙管齊下,使得中國題材的創作在日本文學的總體格局中更為引人注目。
漢語文學是東亞各國傳統文學的血脈,漢字漢文的學習與引進催促了日、朝、越各國書面文學的發生,中國歷史與文學又為東亞各國文學提供了共同的題材,使中國、朝鮮、日本、越南的傳統文學連為一體,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東亞文學區域。
二、印度語文是南亞東南亞文學的母體
正如漢語是東亞各國傳統文學創作的共同語一樣,印度(傳統上印度包括了現在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1947年巴基斯坦從印度獨立出去,1971年孟加拉又從巴基斯坦獨立出去。)語言文學是南亞和東南亞半島地區各國文學的共同母體。不少學者認為,這一地區各國各民族的文學實際上都是印度文學的分支。
斯里蘭卡(原稱錫蘭),它不在印度次大陸之上,是印度洋上一個島國。該島上的兩個主要民族——僧伽羅族與泰米爾族——最早都是從印度本土遷徙過去的。從印度傳去的佛教和印度教文化也占據著統治地位。在古代斯里蘭卡文學作品中,除有用其民族語言僧伽羅語寫成的以外,還有用印度的巴利語和梵語寫成的作品。如公元6世紀由印度史詩《羅摩衍那》改寫而成的《悉多落難記》。進入中古后期,斯里蘭卡文壇以僧伽羅語創作為主,但從內容上說仍以佛教文學為中心。其中聲譽最高、影響最大的是散文巨著《五百五十本生故事》。這一時期的世俗文學也明顯地體現出受到印度文學的影響。例如當時斯里蘭卡風行的有關鴻雁傳書的詩篇顯然是對迦梨陀娑的《云使》的模仿,15世紀中葉至18世紀末葉斯里蘭卡文學史上流行的格言詩,也是由梵語格言詩改寫而成的。
東、南、西三面與印度接壤的一個內陸國家尼泊爾,自古就屬于古代印度文化版圖的一部分。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就是尼泊爾人。尼泊爾人中大部分是印度教徒,少部分是佛教徒。公元4至5世紀起步的尼泊爾古代文學長期使用梵語寫作。1769年尼泊爾境內建立了統一的政權,廓爾喀語(即現尼泊爾語)被確定為國語,出現了尼泊爾語的文學作品。但在題材、主題與風格上,都與印度梵語文學有著深刻的聯系。特別是普遍采用印度教、佛教的題材寫作,反映出受印度文化的深刻影響。
印度語言文學對東南亞的影響也相當巨大。當東南亞開始出現國家時,印度文化早已流傳至此。印度教、佛教等在這一地區得到廣泛的傳播,使東南亞特別是中南半島地區的泰國、緬甸、老撾、柬埔寨等成為佛教國家,乃至一些西方學者把東南亞這些地區統稱為“東印度”、“外印度”或“印度支那”,以強調這一地區與印度深刻的淵源關系。東南亞各國早在民族文字出現之前,其神話傳說、民歌民謠等口頭文學就受到了印度文學的直接影響。東南亞各國民族文字創制之前主要是借助印度的梵語。后來創制的民族文字字母主要是借印度字母創造出來的。例如老撾的寮文字母、柬埔寨的高棉字母、泰國的泰文字母、緬甸的孟文字母和驃文字母及緬文字母、越南南方的占城字母、印度尼西亞的爪哇字母等,都屬于印度字母系統。東南亞國家在文字上與印度的關聯,使他們的書面文學從一開始就受到印度文學,特別是兩大史詩的影響。東南亞最早使用本民族文字書寫的書面文學是古爪哇語文學,它從內容到形式皆受到印度兩大史詩《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等梵語文學的影響。《羅摩衍那》在泰國被稱作《拉馬堅》,其中的人物故事可謂家喻戶曉,很多作品都對《羅摩衍那》史詩中的人物與情節反復引用與改編,衍生出各類體裁的作品。泰國的歷代國王就很喜歡借用《摩訶婆羅多》中的人名為自己或愛臣命名,普通百姓也多有效法。在老撾,《羅摩衍那》被改寫成老撾古典名著《帕拉帕拉姆》,老撾古典戲劇中也不乏移植和借用《羅摩衍那》故事情節的例子。同樣《羅摩衍那》也被柬埔寨吳哥王朝時期的文人譯為高棉文,后來又經過民間藝人結合柬埔寨本土的神話傳說予以加工改寫,形成了柬埔寨著名長篇神話詩篇《林給的故事》。
另一方面,由于佛教在東南亞地區的傳播,尤其當南傳佛教在東南亞半島廣大地區確立了它的主導地位以后,佛教文化對東南亞半島地區的影響更加強大。比如柬埔寨、緬甸等國書面文學的源頭都是刻碑記事的“碑銘文學”。在形式和內容上無不直接受到印度佛教文化的影響。佛教經典中故事性較強的《本生經》(即《佛本生故事》)和散見于其他佛教經典中的佛陀故事成了人們傳道布法的得力工具,也成了作家創作的源泉。東南亞半島各國的佛教文學,大多是以《佛本生故事》為題材的。在泰國、緬甸、柬埔寨等佛教國家中,佛教僧侶作家們長期占據了文壇的主導地位,僧侶作家除了直接借用印度的佛教文學外,還采取間接借鑒的辦法造出仿制品,其中最為典型、影響也最大的作品有兩部:一是源自泰國、老撾的《清邁五十本生故事》,一是爪哇的班基故事。《清邁五十本生故事》是完全按照《佛本生故事》的創作方法寫成,形式上讓人真偽難辨,但故事原型卻來自泰國老撾北部一帶。“班基故事”是印度尼西亞爪哇古典文學中以班基王子的愛情故事為題材的非常著名的歷史傳奇。這個故事早在13至14
世紀就在東爪哇形成,班基故事是繼印度兩大史詩之后在東南亞范圍內流傳最廣,影響最深遠的一部民間文學作品,也是在印度兩大史詩的影響下獨創的東南亞第一部具有民族特色的史詩性作品。
印度語言文學是南亞、東南亞各國語言文學的母體。至少在8世紀伊斯蘭文化進入印度西北部和東南亞群島地區之前,整個南亞、東南亞地區是一個以印度為中心的、相對獨立的文學區域。
三、伊斯蘭教是中東文學一體化的紐帶
西亞中東地區,由于其東西南北交匯處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之可耕地與水源及其他資源的缺乏,歷史上為爭奪地盤與資源,戰爭頻發,歷來都是世界上最不安定的地區。這里有著以巴比倫文明為代表的悠久的兩河流域文明,但各個文明都在互相征戰中中斷、滅亡。在那里,古老悠久的埃及文明中斷了,輝煌一時的巴比倫文明中斷了,窮兵黷武的亞述文明中斷了,以猶太教為中心的希伯來一猶太文明也數次被打散而流落世界各地,以拜火教為中心的源遠流長的波斯文明則被崛起的阿拉伯伊斯蘭文明所征服。整和西亞中東地區長期處于爭戰與混亂狀態,加上該地區以“泥沙”為基本的地表特征,一般建筑物乃至書寫材料都以泥土或泥版為原料,日久易損,因而,流傳下來的文字材料及文學作品極少。直到公元7世紀后伊斯蘭教興起及阿拉伯帝國的創立,才把這一廣大地區統合起來,有了統一的文化,有了較為繁榮的文學創作,并且形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統一的文學區域。可以說,伊斯蘭教與建立在伊斯蘭教基礎上的阿拉伯帝國,既是西亞中東文學的基礎,也是該地區各國文學一體化的紐帶。對此,埃及現代學者艾哈邁德·愛敏在《阿拉伯一伊斯蘭文化史》中寫道:
伊斯蘭教在融合各種文化的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各民族中皈依了伊斯蘭教的人——上層社會的人——認為只有念誦和研究《古蘭經》才能加深其信仰,完成其宗教。為此必須學習阿拉伯語,接受阿拉伯文化的教育。這樣,他們就掌握了兩種文化:本民族的文化和阿拉伯文化,亦必然會把兩種文化融合在一起。將兩種思維方式聚集在一起。很多波斯人阿拉伯化了,很多羅馬人和印度人阿拉伯化了,很多奈伯特人也阿拉伯化了。阿拉伯化的含義就是為接受阿拉伯文化敞開了思想和語言的大門,使阿拉伯文化與他們從小就使用的語言和思維方式結合成一體。阿拉伯化還意味著為使伊斯蘭教代替他們原來信奉的宗教敞開大門。思想、語言和宗教的融合是阿拉伯人與其他民族通婚的一個原因。
的確如此。在公元8至12世紀那統一而廣袤的阿拉伯帝國中,阿拉伯人在文化上兼收并蓄,大量吸收東西方文化的營養,包括希臘、印度、波斯的文化,并對帝國境內較為先進的文化加以吸收、同化與改造。從而將早先散沙一盤的中東凝聚在阿拉伯帝國的統治之下,并在西亞中東地區形成了統一的阿拉伯-伊斯蘭文學區域。
在阿拉伯-伊斯蘭文學區域的形成過程中,最典型地體現在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對波斯文化與文學的改造與同化方面。此前的波斯有著自己獨立而悠久的文化傳統,7世紀中期被阿拉伯征服,從此成為阿拉伯-伊斯蘭帝國的一個行省,納入了伊斯蘭教文化的范疇。雖然阿拉伯帝國對波斯實際有效的統治不過一百來年,但阿拉伯-伊斯蘭教文化對波斯的改造則是深刻而徹底的。在宗教信仰上,波斯人改變了自己古老的瑣羅亞斯德教信仰而改信伊斯蘭教,瑣羅亞斯德教思想基本上從波斯文學中消退。在語言方面,波斯人所使用的中古波斯語受到了強烈沖擊,而蛻變為現代波斯語。現代波斯語大量采用阿拉伯字母(32個字母中只保留了4個是波斯字母),同時大量吸收阿拉伯語詞匯,約有將近一半的詞匯來自阿拉伯語。因而可以說現代波斯語是阿拉伯語化了的波斯語。另一方面,在阿拉伯帝國全盛時期,許多波斯人直接用阿拉伯語寫詩作文,成為阿拉伯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
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對西亞中東地區文學的改造與聚合,還突出表現在土耳其文學中。土耳其是一個文化上后起的、操突厥語的民族。當阿拉伯帝國興盛時他們還生活在中亞地區,并開始向西遷移,能武善戰的土耳其人在阿拉伯阿拔斯王朝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12世紀末,當入侵的蒙古人的勢力衰落時,土耳其人繼之崛起,一部落首領奧斯曼在小亞細亞宣布成立獨立的公國,稱為奧斯曼國。以后又不斷擴張,到16世紀中葉,形成一個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龐大的軍事封建帝國,覆蓋了當年阿拉伯帝國的幾乎所有地盤。土耳其人在西遷過程中皈依了伊斯蘭教,其文化也納入了伊斯蘭文明的范疇。13至14世紀時伊斯蘭教蘇菲派神秘主義流行時,土耳其人中出現了各式各樣的蘇菲派教團。這些教團主要通過詩歌創作活動來宣揚自己的信條,產生了所謂“教團文學”,隨著伊斯蘭教日益深入人心,阿拉伯和波斯文化、文學對土耳其文學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在奧斯曼王朝的宮廷里以及一些城市中的知識分子眼中,土耳其語是簡單粗俗的語言,不能用來進行深刻而優美的宗教、科學與文學創作,因此出現了大量借用阿拉伯語、波斯語詞匯和語法的現象,以至于形成了一種只有精通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的知識分子才能掌握的完全脫離口語的書面語言——奧斯曼語。用這種由土耳其語、阿拉伯語和波斯語混合成的華麗典雅,但又難免雕琢藻飾的語言寫成的文學作品被稱為“迪萬文學”。當時的作品大多以古蘭經、圣訓、先知及其門徒的故事為題材。這些都使土耳其文學成為整個西亞地區伊斯蘭文學的一個重要環節和有機組成部分。
阿拉伯帝國依靠武力征服、文化懷柔和伊斯蘭教的巨大吸引力,陸續將西亞地區各民族文學納入了統一的伊斯蘭文化體系。公元8至12世紀阿拉伯帝國進取、享樂的時代風氣促進了文學創作的繁榮,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土耳其人作家大量涌現。寫出了汗牛充棟的詩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散文作品,出現了《一千零一夜》及《一千零一日》等篇幅龐大的故事集,從而與中國唐宋帝國的文學繁榮交相輝映,并使同時期的歐洲文學顯得黯然失色。12世紀后,阿拉伯帝國分崩離析,分裂為幾十個獨立國家,各個阿拉伯國家之間、各教派之間紛爭不斷,常起戰火,直至今日。但在政治上分裂與混亂的同時,阿拉伯各國卻一直保持了伊斯蘭文化的一致性。由于伊斯蘭教強大的紐帶作用,西亞中東文學圈的整體統一性與區域性充分顯示并一直保留下來。
四、“三塊連成一片”形成亞洲文學區域
以上大體勾勒了亞洲的三大文學圈——東亞地區的漢文學圈、南亞東南亞地區的印度文學圈、西亞中東地區的伊斯蘭文學圈——的形成與構造。在整個亞洲文學中,這三大文學圈既具有相對獨立性,也具有相互關聯性與相互重疊性。古老的亞洲好比是一個遼闊平靜的湖面,湖面上有三塊地方浪花涌動,激起了環環擴散的漣漪,打破了湖面的平靜。這三塊地方就是亞洲的三個核心文化區,即東亞的中國,南亞次大陸的印度,和西亞的阿拉伯伊斯蘭。這三塊地方在空間上大體呈等邊三角形分布,他們激起
的浪花漣漪逐漸向四周擴展,分別形成了東亞文學圈、南亞一東南亞文學圈、阿拉伯—伊斯蘭文學圈。三個圈不斷向外擴散,最終互相重疊,邊界變得模糊,遂使得整個亞洲連成一片,形成了亞洲文學區域,我們可以把這種現象概括為“三塊連成一片”。
將這三個文學圈聯系在一起、重疊在一起的,除了絲綢之路上的東西方貿易的帶動之外,主要得力于佛教與伊斯蘭教的傳播。
在中國西漢末年,來自印度的佛教,向北傳向中亞(即中國古代所謂西域地區),到了東漢末年,再由中亞拐向東方,傳入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特別是唐代,中國將大量佛經譯成漢文,并將佛教一定程度地中國化之后,再向朝鮮、日本與越南北方地區做二次傳遞,從而在東亞文學圈內形成了源遠流長的佛教文學傳統。世俗文學在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上也受到佛教思想的滲透與影響。這樣一來,佛教及佛教文學就把印度文學圈與漢文學圈兩者聯系起來。換言之,佛教使東亞、南亞兩大文學圈得以重合,而重合點就在西域或中亞地區。
在公元12至19世紀,即中國的元明清時代,伊斯蘭教從阿拉伯半島向東傳播,傳至西域即中亞地區,原來信仰佛教或沒有宗教的西域各民族開始信仰伊斯蘭教,于是伊斯蘭教就成為中國西部邊疆各民族的共同宗教,在文學上也深受阿拉伯、波斯的伊斯蘭教文學體系的影響,加上由漢人與阿拉伯人、波斯人混血而成的回族也信奉伊斯蘭教。回族除主要居住在中國西北地區外,還散居在全國各地,并將伊斯蘭教文化帶到漢土。如此,伊斯蘭教就把漢文學圈與西部的伊斯蘭教文學圈聯系起來、重合起來,而重合點,仍然在西域或中亞地區。
同樣的,伊斯蘭教在印度文學圈與阿拉伯伊斯蘭文學圈之間,也起到重要的連結作用。13世紀初葉至16世紀上半葉的三百多年間,在以德里為中心的印度西北部地區,出現了一些小國王朝,總稱為德里諸王朝。德里諸王朝統治者一般是從南亞次大陸西北邊境入侵的突厥人和阿富汗人。他們都信仰伊斯蘭教,首次將西亞中東地區的伊斯蘭教文化帶到印度。到了16世紀下半葉至19世紀的三百年間,雜有蒙古族血統的突厥族的一支莫臥兒人,在印度中北部廣大地區建立了統一的莫臥兒王朝。莫臥兒王朝在德里諸王朝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伊斯蘭教信仰,與該地區原有的印度教發生了長期沖突,許多原先信仰印度教的人被迫改信伊斯蘭教。在這一大背景下,梵語文學也開始衰微,受波斯語、阿拉伯語影響的印度各地方語言及其文學開始興起,但它們又都繼承了此前的梵語文學傳統。于是,印度的西北部地區(主要相當于今日的巴基斯坦),在伊斯蘭教與印度教文化的沖突與融合中,伊斯蘭文學與印度文學也發生了融合,使這一帶成為印度文學圈與伊斯蘭文學圈的重合地區。此外,印度文學圈與伊斯蘭文學圈的重合地區,還有東南亞南部的海島地區,即現在的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這些地方原來屬于印度文學圈,13世紀后逐漸地伊斯蘭教化了。
綜上所述,亞洲文學區域的形成有著不同于歐洲文學區域的鮮明的特點。如果說,歐洲文學區域具有“兩點連成一線”的“同源、單線演進”的特征,那么可以說亞洲文學區域則呈現出“三點擴散、漸次重疊,連成一片”的特點,如果用一個圖形來表示,恰似現代奧林匹克的五環旗的結構,不同的是三個環的邊緣部分相交疊而已。
(責任編輯胡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