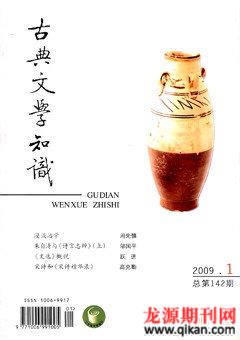從突破到高峰
景凱旋 陶穎越
蜀地自古多詩人,當這些詩人在家鄉接受了最初的教育后,往往會乘船穿三峽,渡荊門,走向一個更加廣闊的世界,去實現其建功立業的人生理想,歷史上關于荊門之詩很多,唐代兩位大詩人陳子昂與李白都曾在此地留下了自己的詩篇,詩歌的體式與情感也都有相近之處。這里,本文擬對陳子昂的《度荊門望楚》和李白的《渡荊門送別》兩詩作一分析比較,希望借以透視初唐至盛唐詩歌嬗變的轉捩。
陳子昂生于高宗顯慶四年(659),梓州射洪人。青年時曾兩度赴京應試,后官至右拾遺。其友人盧藏用《陳氏別傳》載:“子昂始以豪家子,馳俠使氣,至年十七八未知書。嘗從博徒入鄉學,慨然立志,因謝絕門客,專精墳典。數年之間,經史百家,罔不該覽”,“年二十一始東入咸京,游太學,”《度荊門望楚》或即作于調露元年(679)陳子昂初次出蜀之時。詩云:
遙遙去巫峽,望望下章臺。
巴國山川盡,荊門煙霧開。
城分蒼野外,樹斷白云隈。
今日狂歌客,誰知入楚來。
青年陳子昂胸懷濟世之志,對自己的才能充滿了自負。《陳氏別傳》稱其初赴京,“歷詆群公,都邑靡然屬目矣,由是為遠近所稱,籍甚”。《唐詩紀事》亦載其“以其文軸,遍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此詩可以說即是他面世的宣言,充滿一種壯偉之氣。首聯“遙遙去巫峽,望望下章臺”以全景入詩,巫峽是三峽之一,在今四川巫山縣東。章臺是章華臺的省稱,為春秋時楚國所建,故址在今湖北監利西北。這里的“巫峽”和“章臺”分別用來指代蜀地和楚地。“遙遙”對應“望望”,疊聲的運用顯得用詞古樸,同時也表達了蜀地之遙和出蜀之艱,顯示出高古的氣象。
“巴國山川盡,荊門煙霧開”兩句承上,巴國與荊門相對應,山川同煙霧相映襯。一個“盡”字,一個“開”字,讓人聯想到“山窮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境,頓生豁然之感。在地理上。荊門自古是巴蜀通往荊楚的必經之地,《水經注》卷三二江水云:“江水東歷荊門、虎牙之間。荊門在南,上合下開,暗徹山南,有門像虎牙在北,石壁色紅,間有白文,類牙形,并以物像受名。此二山,楚之西塞也。”舟船經過這里,江面變得寬闊,仿佛是一個新的啟程,自然也就常常成為詩人離蜀遠游的象征。
在敘寫完全景圖之后,作者轉入具體描寫。“城分蒼野外,樹斷白云隈”,兩句都是寫遠望,前句是描寫蒼野之外的城市,后句則是寫高聳入云的樹。美國漢學家斯蒂芬。歐文曾指出,陳子昂喜歡用“斷”和“分”一類動詞描寫空間關系,以“表現視覺的延續性被打斷”和“視覺在延續中斷后又重新開始”的意境(《初唐詩》),如“野樹蒼煙斷”、“野戍荒煙斷”、“城邑遙分楚”等。這種在對句中講究動態詞語的技法,正是以宮廷為主的新體詩的著力處,表明在崇尚漢魏詩歌的高古勁健外,陳子昂其實也受到了新體詩的部分影響。
尾聯“今日狂歌客,誰知入楚來”以賦作結,“狂歌客”為作者自況,用的是“楚狂接輿”之典。《論語·微子》:“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詩人借“狂歌”二字點出船行的目的地“楚”地。同時流露出睥睨自雄的豪情壯志,令人想到李白的“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使得詩歌具有詩人所倡導的勁健風骨。
在陳子昂初次離蜀半個世紀之后,年輕的李白也于開元十三年有人說這是寫詩人俯視月亮在水中的倒影(《唐詩鑒賞集》),恐未為當。《詩境淺說》曰:“五六句寫江中所見,以天鏡喻月之光明,以海樓喻云之奇特,唯江天高曠,故所見如此。若在院宇中觀云月,無此狀也。”此論能從詩歌虛實結合的想象特點出發。是為的評。
尾聯“仍憐故鄉水,萬里送行舟”筆鋒一轉,不寫詩人自己留戀故鄉,卻以擬人的手法寫“故鄉水”的深厚情誼,一路相隨,從而表現出詩人對故鄉的依依惜別之情,富有詩味和情趣。《詩境淺說》云:“收句見送別本意。”這是對的,但其稱乃送行者心隨之,則恐失詩人本旨。詩題中的“送別”,當是指故鄉水萬里相送的意思。與陳子昂詩相較,李白詩同樣具有開闊的氣象和勁健的風骨,但修辭更為多樣,技巧也更為豐富,尤其末尾以江水比喻故鄉情誼,更顯出盛唐詩的寄托遙深。
所謂盛唐詩風,可以說就是唐殷墦《河岳英靈集,所說的“既多興象,復備風骨”。從盛唐的代表性詩歌來看,“風骨”當指高遠的志向,以及詩歌中勁健有力的情辭。對其的標舉則是由陳子昂發其端,李白集其成。這與他們的生長環境有關。陳子昂與李白都是蜀地詩人,深受唐初蜀地多元文化的影響,皆崇奉道教,任俠使氣,學百家縱橫之術,向往燕昭王禮賢下士的事跡,并常以楚狂人自況。如陳子昂自稱“少學縱橫術”(《贈嚴倉曹乞推命錄》),“少好三皇五帝霸王之經,歷觀丘墳,旁覽代史”(《諫政理書》)。李白年輕時也曾從趙蕤學縱橫術,自稱“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上安州裴長史書》),“十五好劍術,遍干諸侯”《與韓荊州書》)。這種獨特的地域文化、偏重復古的教育與他們性格和詩歌中的豪俠剛健之氣是頗有關系的,
唐代是一個由貴族制向官僚制發展的朝代,制度安排按照儒家宗旨已經愈加趨于嚴整,陳子昂、李白這種復古理念自然是不合時宜,因而他們在政治上都是失敗的詩人,《陳氏別傳》稱陳子昂“言多切直,書奏輒罷之”,此后他辭官歸隱,終為當地縣令段簡誣陷入獄,憂憤而死。李白則一心希冀不由科舉正途而驟登顯位,一生蔑視權貴。安史之亂后,李白錯將永王李璘視為當今的諸侯而依附之,結果身負“從逆”之名,晚年落魄以終,
然而,政治上的失敗因素卻成了文學上的成功因素。作為武后朝嶄露頭角的詩人,陳子昂與當時京城館閣詩人群應制詠物、講究詩律的時尚不同,他在復古的名義下,反對彩麗競繁的宮廷齊梁詩風,提倡風雅興寄、漢魏風骨,從而預示了詩歌創作的一個新突破。韓愈稱“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薦士》)。《新唐書》本傳亦稱“唐興,文章承徐、庾余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所謂“高蹈”、“雅正”,都是以復古求新變,講求詩歌的現實內容和高尚情懷。這對追名逐利的京城詩人群來說,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唐代詩歌革新由遠離京城的蜀地詩人發起,并最終由邊緣走向中心,不是沒有道理的。
作為盛唐先聲,陳子昂標舉“興寄”、“風骨”,令時人耳目一新。但他最后仍落第西歸,說明在宮廷詩尚占據主流的武周朝,他的時代還沒有到來。更重要的是,詩人忽略了宮廷詩歌的形式追求本身也蘊涵著對“興象”中“象”的把握。一般來說,所謂“興象”,“興”指興發寄托,“象”指物象,它既不是實景,也不是直接抒情,而是將情語與景語很好地結合起來,達到言近旨遠的效果。如果說,宮廷詩往往只有“象”(物象)而乏“興”(興寄),那么,陳子昂詩則是只有“興”而乏“象”,只是簡單地以抽象思辨附著于形象之上,清人王夫之評其《感遇》詩“似誦似說,似獄詞,似講義,乃不復似詩”(《唐詩評選》),
雖不免過苛,但也是看到了其詩理勝于情,有風骨而乏興象的缺陷,
盛唐詩歌的成熟是在李白等人的筆下完成的。一方面,李白與陳子昂一樣,認為“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對六朝柔靡詩風深表不滿,要在詩中抒發個人的真實情感。另一方面,李白并不排斥前代詩歌中的形式因素,而是轉益多師,注重詩歌的藝術表現力。他所贊美的“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便是對建安詩歌中的“風骨”與六朝詩歌中的“清”的雙重推許,并以學習謝靈運、謝跳等六朝詩歌來實踐自己“圣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的詩歌主張(《古風》之一)。如其將大、小謝詩句直接入詩的就有“夢得‘池塘生春草,使我長價登樓詩”(《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金陵城西樓月下吟》),“襟前‘林壑斂暝色,袖上‘煙霞收夕霏一(《酬殷佐明見贈五云裘》),可見他對大小謝詩歌的贊賞。
這些詩句都是大、小謝的寫景名句,其“清”的特點實際上就是不事雕飾、以景見情,也就是具有“興象”。如“池塘生春草”一句,葉夢得稱“正在其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石林詩話》),王夫之則稱是“心中目中與相融浹,一出語時,即得珠圓玉潤;要亦各視其所懷來。則與景相迎者也”(《薑齋詩話》卷上)。可見“興象”就是皎然所說的“情緣景發”、“情在言外”的詩境。李白喜歡大、小謝的詩歌,蓋緣于他對詩境的追求。而他自己的詩歌也是如此,在學習和繼承前人詩歌的基礎上,創造出更加高遠的詩境,除了那些氣魄宏大的古體詩外,其絕句和律詩都是富有清新曠遠的興象和情韻的。
《渡荊門送別》屬于李白的早期之作,但已經具備了盛唐律詩的聲律情韻。陳子昂詩尚不合律,偏重抽象全景描寫和直陳豪情,故多思致而少情韻;李白詩則是聲律和諧,既自由放達,又虛實結合,尤其是講究具體的意象和情思,使得此詩兼具盛唐詩歌的風骨和興象,通過對江水、平野、明月、云霞之間關系的出色描寫,表現出詩人對外面世界的向往與對故鄉的思念相交織的復雜情感。
在唐詩史上,陳子昂是開啟盛唐詩歌的詩人,李白則是盛唐詩歌的最杰出代表。前者標舉的“風骨”固是扭轉了初唐詩的輕艷柔靡,而后者體現的“興象”更是盛唐詩的一大特色,體現了盛唐詩歌所特有的渾融深遠的意境。可以說,陳、李這兩首詩的區別即為初唐與盛唐之別,從中可以見出唐代詩歌的嬗變。正是在對傳統的不斷繼承與發展之中,詩歌才由初唐走入了盛唐,由突破走向了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