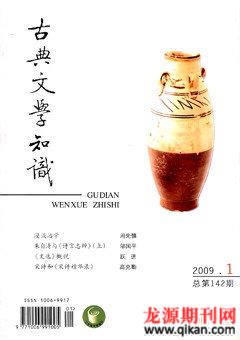因物生情,感慨無端
陳 平
飄拂微風(fēng),芊眠楊柳,上河時候清明。扇底嬉春,誰人一角重臨?鑾輿猶記曾來駐,更趙家、圖畫重尋。久消沉,《夢華》舊錄,且說東京。才人何事搜求苦,數(shù)奔州遺恨,直到而今。倦客相看,此時別自傷心。金戈鐵馬經(jīng)過眼,看廿年、河外霓旌。剩閑情,渡頭艇子,打槳來迎。
莊械(1830~1879),又名忠械,字希祖,號中白,祖籍江蘇丹徒,有《中白詞》傳世,為清代咸、同年間的詞壇巨子,當(dāng)時與其好友大詞人譚獻(xiàn)齊名,詞史上有“莊譚”之稱。
莊械出身富家,先人本淮揚(yáng)鹽商,家于揚(yáng)州,少年時即捐得部主事官職。后因時勢混亂。經(jīng)商不利,家道中落。咸豐五年(1855),莊械在京師與譚獻(xiàn)訂交于顧亭林祠下,此后兩人交誼曰深,并相與切磋詞學(xué),成為以張惠言為首的常州派詞旨的重要推闡者與實(shí)踐者,據(jù)譚獻(xiàn)《莊械傳》云,咸豐八年(1858),清廷于天津簽署喪權(quán)辱國的《天津條約》,有一部分官吏與知識分子上書朝廷表示反對與不滿,莊械也在其中。因投書權(quán)臣,言辭激切,受到阻諫,于是遂將滿腹的哀憤,統(tǒng)付之于詞,所謂“后有哀憤則托于樂府、古詩,回曲其辭以寓意,至倚聲為長短句,皆是物也”。可見莊氏詞學(xué)創(chuàng)作的發(fā)韌,乃與家道、時勢及其心態(tài)有關(guān),莊氏后來無意于仕進(jìn),進(jìn)入了曾國藩創(chuàng)辦的書局,與戴望、劉壽曾等一起編校書籍,更肆力于詞學(xué)與經(jīng)學(xué)。清人陳廷焯《白雨齋詞話》卷五云:“吾鄉(xiāng)莊械……余觀其詞,匪獨(dú)一代之冠,實(shí)能超越三唐兩宋,與《風(fēng)》、《騷》、《漢樂府》相表里,自有詞人以來,罕見其匹。”雖不無夸獎過當(dāng)之處,然莊氏詞作之功力,亦可見一斑。只因享年不永,未能盡才。
此《高陽臺》詞題下有小序云:“丙子清明,題郭湘渠所持臨宋人《上河圖》一角畫扇,感今懷古,念亂憂生,觸緒成吟,不自覺其言之拉雜也。”從小序可知此作本因郭湘渠所臨宋人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之一角扇面,因物起情,沘筆題詞。本來一首題畫之作,一般不會寄托深遠(yuǎn)的思想寓意,更何況歷史名畫《清明上河圖》提供給詞人的創(chuàng)作靈感,也很難與“念亂憂生”之情思相綰結(jié)。然詞人胸中自有塊壘,不惜“拉雜”而感發(fā)之、聯(lián)想之,在足見其“念亂憂生”情思之濃烈的同時,也展示了詞人不尋常的騰挪跳躍、開闔自如的筆法手段。
詞之開句,從扇面所畫景物寫起,亦屬通例。《清明上河圖》本是展示北,宋京師開封汴河兩岸,于清明時候的商務(wù)、風(fēng)情等內(nèi)容的歷史畫卷。從扇面一角看來,但見春風(fēng)輕拂,楊柳依依。河面上,舟船往來,一片繁忙;街市中,生意興隆,人聲鼎沸。所以開頭詞人用“芊眠楊柳”、“扇底嬉春”兩句輕輕帶過。“鑾輿”句至結(jié)拍,乃將《清明上河圖》所畫當(dāng)年京城之繁華,很快因“靖康之變”使北宋王朝草草終結(jié)的命運(yùn),與清王朝曾經(jīng)有過的盛世與時下的衰敗暗作對比,詞句中的“曾來駐”、“久消沉”,正是暗寓了歷史的滄桑興衰之感。南宋人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曾經(jīng)回憶描述北宋京師開封(東京)當(dāng)年市場繁榮,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物阜民安,風(fēng)情萬種的城市風(fēng)貌。而這種曾經(jīng)有過的美好圖景,在詞人宋、清兩朝相同的盛衰比照中,反而加重了觸物起情、“憂生念亂”的傷感。蓄積至此,郁勃之情直逼出下片換頭“才人何事搜求苦”一句的再轉(zhuǎn)。此處“才人”指清人李宗翰。李宗翰(1770~1832),字公博,臨川人,乾隆五十八年進(jìn)士,官至工部左侍郎。李氏藏有唐代著名書法家褚遂良所書《京師至德觀主孟法師碑》,當(dāng)時頗負(fù)盛名。此碑帖后邊有明代文壇大家王世貞(字弁州)所寫的《跋》。王弁州評此碑帖云:“波拂轉(zhuǎn)折處,無毫發(fā)遺恨,真墨池中至寶也。”這里詞人不僅由眼前之名畫自然聯(lián)想到李宗翰所持之名帖,而且反用弁州評帖“無遺恨”之典故,既暗扣書畫藝術(shù),又似深藏“潛臺詞”:既使弁州在世,見此情景亦當(dāng)有“眷懷君國”之遺恨了,此筆法頗類姜白石《揚(yáng)州慢》之換頭句:“杜郎俊賞,算而今、重到須驚。”既然唐代的杜牧可以復(fù)臨趙宋之都城,那么明代的王世貞重臨清代的名城,又有何不可!莊械曾于《復(fù)堂詞敘》中云:“自古詞章,皆關(guān)比興,斯義不明,體制遂舛。……夫義可相附,義即不深;喻可專指,喻即不廣。托志帷房,眷懷君國,溫、韋以下,有跡可尋。”莊械認(rèn)為,在中國詞史上頗被人輕視的曲子詞,并非都是“剪紅刻翠”、“搓粉滴酥”的側(cè)艷之作,相反從溫庭筠、韋莊以來就不乏“托志帷房,眷懷君國”的比興寄托之作。這正是繼承了以張惠言為首的常州詞派的一個重要觀點(diǎn)。如果說詞人由眼前之《上河圖》而聯(lián)想至宋人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猶不妨可稱為自然之聯(lián)想,那么從名畫聯(lián)系到名帖,再反用王世貞評帖之典,則是在騰挪跳躍的“拉雜”之中,通過“遺恨”兩字的牽合,將不同的書畫藝術(shù)、不同的朝代境遇與詞人的家國之恨作了無痕的綰結(jié)。其結(jié)構(gòu)之“離”,運(yùn)思之“奇”,實(shí)非等閑手筆可辦。換頭之后的“倦客相看”句,直寫當(dāng)時局勢。咸豐以后,清廷內(nèi)憂外患,危機(jī)四起。此前已有鴉片戰(zhàn)爭的失敗,割地賠款,一敗涂地。而繼之以太平天國的大規(guī)模戰(zhàn)爭,幾使清廷一籌莫展,岌岌可危。此詞所作于“丙子”年,即光緒二年(1876),詞中所謂“金戈鐵馬經(jīng)過眼,看廿年、河外霓旌”,往前推算二十年,又正是太平天國風(fēng)起云涌、戰(zhàn)亂方酣之時。至此詞人的“優(yōu)生念亂”之情已經(jīng)和盤托出,情懷的抒發(fā)也達(dá)到一個高潮,歇拍“剩閑情,渡頭艇子,打槳來迎”,詞筆再轉(zhuǎn),回歸題畫本旨,情思似又轉(zhuǎn)為平靜與舒緩,這種運(yùn)思結(jié)構(gòu)不但使全篇開闔完整,靈動有致,而且也使情思的寄托與鋪陳更顯起伏變化,張弛有度,充分顯示了詞人感情的深沉與筆法的老辣。
莊械秉承常州詞派論詞宗旨,不僅強(qiáng)調(diào)創(chuàng)作的情思寄托,而且規(guī)慕兩宋詞家,尤其至莊械所處時代,周邦彥、吳文英、王沂孫等宋代詞人的地位空前提高,于是詞作的藝術(shù)筆法亦越發(fā)顯示出與近體詩的差異。詞被稱為“詩余”,表明詩詞本來同源,而且出于唐代盛、中期的詞,最初還受到近體詩的直接影響。唐五代至北宋初、中期,詞的寫作與詩的句法乃至音律均較為接近,至北宋后期周邦彥出,才在詩筆中輔之以賦筆,利用長調(diào)慢詞特有的結(jié)構(gòu),于鋪陳中結(jié)合大量的比興句法,將唐人詩句與典故情事隨心進(jìn)行牽合勾連,從而逐漸形成與近體詩截然不同的表達(dá)方式。譬如同為“詠春”,杜甫《春曰五首》之一云:“農(nóng)務(wù)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茅屋還堪賦,桃源自可尋。艱難昧生理,飄泊到如今。”詩歌的章法往往是扣住本題,關(guān)合情思,雖然詩句也講究騰挪跳躍,但其思緒軌跡大都?xì)v歷可尋,主題也相對較為顯豁。而周邦彥之《瑞龍吟》(章臺路)一首,《花庵詞選》原題作《春詞》,卻連用唐人“章臺柳”、“人面桃花”、“劉郎”、“秋娘”、“燕臺”等故事,將看似不相關(guān)的情事,一一串連,從而營造出一種恍惚迷離、感慨無端的情境,所以繆鉞先生《論宋詞》中,在比較詞與詩的不同表現(xiàn)手法時,有“其境隱”的概括。這種表現(xiàn)手法對南宋婉約派詞人及清代常州派詞人的創(chuàng)作均有深刻影響。莊械此作,也從一個方面體現(xiàn)了這樣的特點(diǎn)。
《高陽臺》全詞因物起情,聯(lián)想縱橫,開闔自如,哀而不傷。莊械作為一個下層士子,在其無力左右局勢的情況下,仍能夠感慨盛衰,系念家國,觸目所及,不忘現(xiàn)實(shí),足見當(dāng)時的國家危機(jī)已經(jīng)遍布士林,無可逃避了。譚獻(xiàn)《篋中詞》中評莊械此作云:“止庵所謂能出者也。”周濟(jì)(號止庵)是常州詞派的重要詞論家,其《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曰:“夫詞非寄托不入,專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觸類多通。”意思是說好的作品,不但要有嚴(yán)肅的情思寄托,更要能激發(fā)起讀者的想象與聯(lián)想,讓讀者因之產(chǎn)生出新的創(chuàng)作靈感。由于古代的讀者大多是從事創(chuàng)作的詞人,他們欣賞作品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豐富和有益于自己的創(chuàng)作,所以詞人的作品能夠使他人產(chǎn)生創(chuàng)作的動力與激情,為他人的創(chuàng)作提供詩材詞料或靈感的源泉,莊械從扇面中的《上河圖》一角,感發(fā)情思創(chuàng)作新詞,同理,他的詞作也將為他人的感發(fā)情思產(chǎn)生作用,如此循環(huán)往復(fù),以至無窮。譚獻(xiàn)小莊械兩歲,其詞與論詞宗旨均與“憂生念亂”相關(guān),作為莊械的好友,當(dāng)不是沒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