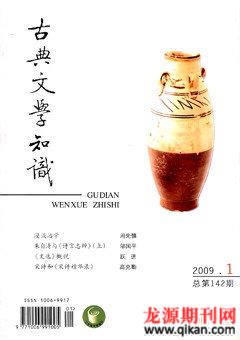宋代寓言《東方智士說》和宋人的人生觀
王曉驪
所謂寓言,是指寄托某種事理,具有勸諭、諷刺意義的簡短故事。中國是世界寓言文學的發祥地之一。早在先秦時期,寓言就被當時文人用作說理的載體,借此喻彼、借小喻大,形成了情趣盎然、深入淺出的散文風格。發展到唐代,寓言擺脫了從屬于某一理論體系的附庸地位,成為一種完整獨立的文學體式。宋代寓言的創作雖然受到唐代寓言的直接影響,但是也形成了鮮明的文學個性,有些作品的題材完全超出了唐代寓言的范圍,顯示出獨特的時代風貌。其中南宋初年朱敦儒的《東方智士說》以人生為主題,集中體現了宋代文人關注自我、關注個體人生的文化取向,尤其值得重視。
這則寓言收錄于宋末文人趙與時的筆記《賓退錄》卷六,故事講述一位“智士”借居于富家豪第,為期一年。但是在短短的一年中,智士并未享受“西園花竹之勝,后房歌舞之妙”,而是傾盡心力,營建東圊(廁所),以至于“躬執茆帚,與役夫雜作。手足瘡繭,頭蓬面垢”。轉眼一年已到,美圊未成而主人已歸。智士恍然自失,抑郁而終,
作者對這則寓言寓意的解釋非常簡單含蓄:“子奚笑哉?世之治圊者多矣,子奚笑哉?”這給接受者留下了很大的發揮余地,趙與時從中得到的教益是:“世之人不能窮理盡性,以至于圣賢之樂地,而區區馳逐末務以終其身者,皆東方智士之流也。余亦懼夫流而于此也,讀之悚然,為之汗下。”趙與時是楊簡的門人,作為南宋心學的嫡派傳人,他念念不忘的就是所謂“窮理盡性”。所謂“窮理盡性”,出自《周易·說卦傳》“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是宋儒申發各自哲學理論的出發點,各家解釋不盡相同,但都強調對世界本質和人的自我本性的純理性把握。這種把握需要抑制耳目的干擾,因為“德性所知,不萌于見聞”(張載《正蒙·大心篇》)。因此在理學家的眼中,所有感性的、審美的行為追求都是“末務”,包括詩文創作、游山玩水、飲酒品茶等等一切人生快意之事。然而對于并非理學家的朱敦儒來說,其本意卻未必如此。只要想象一下“西園花竹之勝,后房歌舞之妙”,就能感受到作者對人生本質的把握并非理學家式無欲無求的哲學把握。那么在這則寓言中,作者到底寄予了什么樣的人生寓意呢?這要從朱敦儒的生平說起。
朱敦儒,字希真,號巖壑。北宋滅亡之前,他就是洛陽城著名的隱逸詩人,無心功名,過著登山臨水、嘲風弄月的生活。宋欽宗曾經征召他,他卻辭以“麋鹿之性,自樂閑曠,爵祿非所愿也”。他曾有一首《鷓鴣天》可以視作這段生活的夫子自道: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懶慢帶疏狂。曾批給雨支風敕,累上留云借月章。詩萬首,酒千觴,幾曾著眼看侯王?玉樓金闕慵歸去,且插梅花醉洛陽。
可見從那時起,他就有視富貴如浮云、視王侯如糞土的狂傲之氣。北宋滅亡之后,朱敦儒的生活經歷了一波三折的變化。一開始他仍然隱居山中,不愿做官。由于國難當頭,在朝廷的一再征召和朋友的勸說下,他曾一度出山。然而官場險惡,朱敦儒最終因支持李光而被彈劾,在飄零了一陣子以后又重新隱居。秦檜當國,迫于權奸的淫威,他再度出山。秦檜死后,他受到牽連,再次落職,但這一次為官,徹底丟失了他保持了大半生的靖譽,留下了晚節不保的悔恨(朱敦儒生平材料參見脫脫《宋史》,中華書局1985年版;楊海明《唐宋詞與人生》,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起起落落之中,破滅的是理想——包括兼濟天下和獨善其身,備受打擊的是人格和自尊,攪亂的是原本超脫平靜的生活,他越發領會到外在功業只是春夢一場,最終帶給他的只有痛苦和悔恨:
新來省悟一生癡,尋覓上天梯。拋失眼前活計,踏翻暗里危機。莫言就錯,真須悔過,休更遲疑。要識天蘇陀味,原來只是黃薹。(《朝中措》)
了解了這一生平,我們再來看《東方智士說》,就能發現這是一則關于人生意義的寓言,其中充滿了蒼涼虛無的人生之嘆。東方智士的悲劇性正在于他所苦心窮力營建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廁所而已,而且并非為自己所有,到頭來不過是為他人作嫁衣裳,作者通過巧妙設喻,以骯臟而微不足道的廁所來象征功業,以寄居豪宅來象征人生,從而徹底解構了傳統的人生價值觀。世人孜孜以求的外在功業,實際并非人生的真正意義之所在,它對個體而言毫無價值。對外在功業和名利的追求最終使人們錯過了人生真正值得珍惜和享用的東西。更何況人生本來就是寄居,如同白駒過隙,匆匆流逝,因此試圖在虛無人生中建立對自己毫無意義的“事功”,以此來體認自我的存在意義,這正是佛家所謂“陽焰求魚”、“夢中說夢”,
然而,這則寓言的意義遠不止此。從客觀上說,它也集中體現了整個兩宋文人對人生本質和人生價值的重新思考和重新定位。宋代是一個積弱積貧的時代。面對內憂外患,不少宋代文人都曾有過通變救弊、投身國是的熱情。但這又是一個皇權統治高度完備的時代,這種熱情是不被鼓勵的,不僅如此,實際上任何以自我肯定為基石的人格目標都是沒有發展空間的,南宋張拭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秦漢以來,士賤君肆,正以在下者急于爵祿,而上之人持以為真足以驕天下之士故也。”(張拭《張子房平生出處》,《南軒集》卷十六)宋代士大夫主體意識的覺醒和君權專制體制之間的強烈沖突使傳統人生價值觀遭受到嚴峻的挑戰。可以說,宋人對人生本質的不倦探求,是建立在對傳統人生價值體認的質疑和部分否定之上的。
在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人生價值體系中,個體的生命價值必須附麗于社會,也就是說,只有當個人的行為對社會有所裨益時,其人生才是有價值的;只有建立了某種社會性的“事功”(包括德、功、言三個方面),個人的存在才是有意義的。然而當榮華富貴如同春夢一場煙消云散的時候,當少年壯志在世事磨礪中只剩下蒼白兩鬢、飄零一生的時候,宋人開始將眼光從外界轉向內心,在自我省視中尋--求生存的意義和人生的真諦。“我是誰”、“人活著到底為什么”、“我所做的一切有意義嗎”,這些看似簡單卻困擾了古今中外一切哲學家的問題也讓宋人陷入了沉思,他們朦朧地感受到“我”之所以為“我”,除了社會的屬性之外,還有一個非社會的“自我”的存在。社會的“我”直接影響甚至決定非社會的“我”,但越是這樣,非社會的“自我”的離心力就越大,人就越發渴望一個自主自由和自悅的個人世界。正因如此,才會有蘇軾“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臨江仙》)的悲哀無奈和王安石“乞得膠膠擾擾身,五湖煙水替風塵。只將鳧雁同為侶,不與龜魚作主人”(《初到金陵二首》之二)的輕松喜悅。宋人人生發展的需要和自我理性思維的高度成熟都促使他們超越紛紜復雜、變幻無常的人生表象,從更深層次去把握世界,也把握人生本質。
如果說人生如夢的虛幻感是宋代文人揮之不去的夢魘,那么否定事功、關注自我就是他們擺脫外在得失榮辱,追求自由自主自悅人生境界的解脫之路。只要看下面兩則軼事:
雷宣徽有終,頗涉道書。因讀史費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釣餌。橫戈開邊,枝劍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
(蘇東坡)后過金山,坡題自己照容偈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儋州惠州。”(《宋稗類鈔》)
“橫戈開邊,枝劍討叛”本是封建時代男性崇尚的最高事業,只要讀一讀李賀《南園》詩中“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請君暫上凌霄閣,偌個書生萬戶侯”的慷慨詩句,就能想見唐代文人對軍旅生活的向往和建立軍功以名垂青史的渴望。而宋代文人卻將之一并視為貪婪者的釣餌。宋代另有一位文人林防在其寓言《赴火蟲》中曾用撲火的飛蟲來比喻那些追逐聲色利欲而蹈死不疑的世人,很明顯,這“聲色利欲”之中同樣也包括了功名。蘇東坡遠貶惠州時,佛印曾在給他的信中這樣勸他:“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空;想要從這膠膠擾擾的紅塵中得到解脫,唯一的途徑就是“把一二十年富貴功名,賤如泥土”(錢世昭《錢氏私志》)。然而實際上,蘇軾的入仕并不為富貴功名,而是“一心為國”。早年力倡革新,是為通變救弊;為官一方,是為了造福百姓;反對新政,也是為了國家社稷,然而在佛印的眼中,這一切都是“富貴功名”,均非“自家本來面目”。這雖是一個佛教徒的看法,但對蘇軾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所以他才會把他一生的功業歸之于政治上毫無建樹的貶謫時期,因為只有在困頓中,只有在遠離了充滿是非得失的政壇,只有在擺脫了功名榮辱的攪擾之后,他才領悟了人生的真諦,至少宋人是這樣認為的。
不能否認,《東方智士說》蘊涵的人生哲學是悲觀消極的,它對外在功業的否定消解了人生的現實意義。試想,沒有了外在事功,個體人生價值何從體現?沒有了現實人生,自我又皈依何處?對此宋人實際上也充滿困惑,并且陷入了由此帶來的無限悲哀之中。然而這則寓言深刻而廣漠的人生悲哀在整個封建時代都具有很強的典型性。它的強烈的否定性植根于對當時社會合理性的質疑,因此對“當時社會秩序具有潛在的破壞性”(李澤厚《美的歷程》)。從這一點而言,其深刻性不言而喻。此外,《東方智士說》也教人珍惜生命,看淡功名利祿,學會享受人生,因此即使在今天的社會中,仍然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