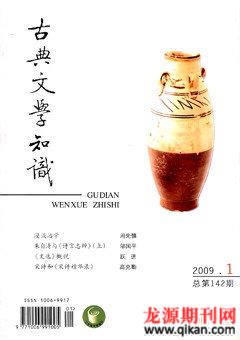新時期《綠野仙蹤》研究綜述
趙維平
一、關于作者和成書
《綠野仙蹤》作者為李百川,因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百回手抄本前有“李百川自序”,并且所有版本都有的“陶家鶴序”中有“予于甲申歲二月,得見吾友李百川《綠野仙蹤》一百回”之語,而向無異議。侯忠義《論抄本(綠野仙蹤)及其作者》一文,推斷作者生卒年道:“乾隆十八年寫作此書時,他自言已‘年過三十,假定作者此時為三十四五歲,那么作家當生于康熙五十八年(公元一七一九年)左右,而卒于寫作時間最晚的侯定超序完成之時,當在乾隆辛卯(即三十六年,公元一七七一年)之后。”上世紀90年代在美國發現新的百回手抄本后,翟建波《(綠野仙蹤)作者、版本新證》指出俄亥俄大學館藏百回本上李百川的作者權,除一見陶序外,尚二見于陶序補記,三見于第六回夾批,李百川的作者權成為鐵證,
李百川籍貫,自吳晗1931年根據為小說作序的陶家鶴是紹興人,侯定超是洞庭人,認為百川自序“宜刪”的周竹蹊是南京人,李百川自序中“癸酉攜家存舊物遠貨揚州”一語,提出李百川“江南人”說,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一直作為學術界主流看法。上世紀80年代末陳新《(綠野仙蹤)作者、版本及其它》指出吳晗的“江南說”證據不充分,提出“李百川為北方人,小說開始即寫山西事,似為山西人”的新見解。繼而蘇興、蘇鐵戈《(綠野仙蹤)叢談》標榜鄭振鐸提出的“山東人”說,除了從作品語言特色例證,還從敘述語氣和人物語氣、溫如玉活動在山東省太安州、作品對蘇杭的描寫及感嘆帶有北方人的氣味三個角度分析作品的山東人創作印跡,得出“作者是北方人,可能更合適一些。……是山東人(當然到過北京)也是可能的”的結論。翟建波進而力證李百川是山東人,實證色彩比較濃厚。首先,作者自序中說曾被時任直隸太原府遼州牧的堂弟迎請到遼州,而“羞歸故里”,山西顯然不是作者故鄉;其次,作者自序中有“遠貨揚州”,夾批中有“余在江南”、“余在江南揚州居停七載”的話,可知作者也不是南方人;再次,作者對北方方言尤其是對河南、山東一帶方言非常熟悉,他很可能是河南或山東人。但自序中有“壬午抵豫”一語,非返鄉口吻,所以他只能是山東人。作者還列舉內證,根據“全書約三分之一的故事發生在山東境內”,作品中山東籍人物(溫如玉、金鐘兒、苗禿子、蕭麻子)性格刻畫最鮮明,有關故事情節最精彩,以及溫如玉鎮江被騙帶有作者揚州被騙的“影子和教訓”,得出“作者為山東人較為實際”的結論。
《綠野仙蹤》的成書研究,人們主要根據作者自序。侯忠義論述成書過程道:“據自序稱,清乾隆癸酉(即十八年),他草創《綠野仙蹤》三十回于揚州旅邸,至乾隆壬午(即二十七年),在河南完稿,歷時九年,共計一百回,”可謂清楚明白。李百川創作思想,經歷了一心寫鬼、兼重人情、偏重民生三個階段。李百川“家居時有‘最愛談鬼的嗜好,繼之更有‘廣覓稗官野史的興趣,但創作《綠野仙蹤》的最根本原因,還是根源于他窮愁潦倒、浪跡他鄉陌路的艱辛生活經歷”。林虹《論(綠野仙蹤)在文學史上的價值》指出:“在他醞釀創作及創作之初,他‘最愛談鬼而想創作‘百鬼記,因此,此時他心目中的‘奇無疑是‘牛鬼蛇神之奇,可當他歷盡滄桑,四海漂蕩,經歷了形形色色的人情物性之后,腦海里更活躍的必然是那些現實生活中活生生的‘若男若婦。這使得小說真正出‘奇的恰恰是在寫‘日常起居的人情部分。”可謂的論。
二、關于版本研究
《綠野仙蹤》傳世的版本分百回抄本與八十回印本兩個系統。抄本系統主要三家,北京大學圖書館百回抄本先后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據之影印出版和整理校點出版,美國俄亥俄大學圖書館藏百回抄本由中華書局“古本小說叢刊”第四十一集收錄,印地安那圖書館藏百回抄本為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說集成”所影印。八十回印本則分三類:刻印本有乾隆刊巾箱本、道光十年刻中型本、道光十五年乙未集誼堂校刊本、道光二十年武昌聚英堂刊小本、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刊本:石印本有光緒三十年上海書局本和民國十三年上海大成書局本;鉛印本則有大達書局本。
《綠野仙蹤》版本研究新成就,主要集中在:
(一)手抄本和刻印本關系。侯忠義指出“抄本在前,刻本在后;抄本是‘繁本,刻本是‘簡本;抄本是‘原本,刻本是‘節本(刻本本身也有個繁簡問題)”。這一意見為蘇興、蘇鐵戈所認同,但蘇文對問題闡述較為細致:八十回刻印本對百回手抄本的刪改,除相同情節中個別詞語及詞句改刪外,情節改刪還有三種情況:一是單純的刪減,靠上下文自然銜接,或稍加幾字使上下文銜接起來,以至于減少內容,合并回目;二是刪減的同時,在刪削處有增改;三是情節有調整。翟建波《(綠野仙蹤)版本、作者再證》根據“北大本刪節了的文字,刻本有”和“刻本與俄本一樣,都沒有作者自序,而北大本卻是有作者自序”的現象,斷定后世流傳的八十回刻本是由俄本做底本,“另有其人”刪改而成,他在刪改時“只能是沿襲舊文,即俄本之文”。
(二)《綠野仙蹤》的祖本。鄭其興《(綠野仙蹤)>“印圖本”價值淺論》比勘了北大圖書館所藏百回手抄本和美國印地安那圖書館所藏百回手抄本,根據“印圖本”上多出的陶序補記及其保留了許多“北大本”所缺漏的文字、保留了祖本情節推進的邏輯性、保留了祖本情節敘述的豐富性、保留了祖本情節刻畫的細致入微處等現象,指出“‘印圖本較‘北大本更完整地保留了《綠野仙蹤》祖本的原貌”,它“有力地證明了《綠野仙蹤》另有一個祖本的存在”。作者認為:陶家鶴所見并為之作序的本子可能是作者李百川的手稿本,或者是李百川自己把手稿本謄抄又加上傍注、評語的定本;“北大本”與“印圖本”便是以這個本子作為祖本,由不同抄手抄錄于不同時間的抄本;八十回刻本也是以這個本子作為刪改的原本,而非以“北大本”或“印圖本作為刪改的原本。
(三)手抄本之間的比較研究。翟建波《(綠野仙蹤)版本、作者新證》指出美國儉亥俄大學圖書館藏百回手抄本與印地安那圖書館藏百回手抄本“二書”一字不差,抄寫一模一樣,因而知二書實為一書,其中當有一書為另一書的影印或摹印本”,進而比勘俄亥俄本與北大本,根據二本對應處俄本語意通順合理、刪改后的北大本正文與保留下的夾批相矛盾、俄本批注語被北大本誤入正文三大發現,認定“北大本實為俄本的一個刪改本。俄本在前,北大本在后;俄本是原本,北大本是節本;俄本是繁本,北大本是簡本。北大本與俄本相比,大約刪去六七萬字,為全書的十分之一左右”,根據比勘第一回就發現二本有一百多處異文,以及北大本“不僅正文有刪有改,而且批注也有刪有改,還有增加。而多數的刪改,并不影響本書的價值,對讀者了解作者的思想或者說讀者了解冷于冰的思想意識并無多大妨礙”的事實,推知“北大本為作者自刪自改的另一種傳本”。因為“若是抄寫者致誤,斷不至于如此之多”,這是很有見地的。
三、關于構思、結構和主題
早在上世紀初,魯迅就認同黃人關于《綠野仙蹤》“蓋神怪而點
綴以歷史者也”的論斷。文革結束后,再版的北大中文系《中國小說史》指出《綠野仙蹤》“通過明代嘉靖年間冷于冰求仙得道的故事,表達了作者對現實的看法和政治見解”。其后林虹認定《綠野仙蹤》由神魔、講史、人情三個方面內容有機構成,而“選取冷于冰求仙得道這個神魔內容作為全書線索,將講史和人情內容串連起來”,并指出作品神魔、講史、人情三大內容又各取前人之長,神魔板塊取《西游記》以中心人物貫穿始終,而以冷于冰為線索;講史板塊取《水滸傳》圍繞聚義、忠義大業的人物傳遞法,呈現出一人引出另一人、一事激發另一事的連鎖反應結構;人情板塊取《金瓶梅》家庭切入法,不受時地限制地展現多個家庭,對小說結構的分析相當精當。侯志義則一針見血地指出《綠野仙蹤》“托明代嘉靖之名,實寫清代乾隆之世,借冷于冰求仙得道故事,寄寓他的政治理想”的構思特點。
由于《綠野仙蹤》既有神魔又有講史和人情內容:所以對它主題的看法難免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究其本質無非兩種意見。一種認為,社會和人生情節是《綠野仙蹤》的主體,主人公以出世的方式行入世之事,表達了鏟除人間不平的主題;另一種認為,神魔內容是《綠野仙蹤》的重心,主人公不停地度人成仙,反映的是道家文化,表達了人世是苦海、出世方逍遙的思想。
林虹、侯忠義、董建華持第一種意見。林虹認為,神魔內容不過是講史和人情內容的線索,講史和人情才是作品主體,因而《綠野仙蹤》的主題是入世的,“表現在貫串全書的一種人生哲學,即作品第二回首次出現以后又屢次提及的四個字‘窺時順勢,大到朝廷政治斗爭,小到閨房家事之爭,這種觀點都一以貫之,在作者看來,違背了這條原則,在政治斗爭中不僅會有殺身之禍而且事業無成,在家庭糾紛中也會被動失勢甚至身死名滅”。侯忠義認為,作品中棄家訪道、伏鬼降妖情節不足憑,入道后的主人公蒼白無力、非常概念化,倒是冷于冰要點化的對象溫如玉、連城璧等人物寫得有血有肉,小說所寫世俗生活和忠奸斗爭讓人趣味盎然。這說明“小說中某些人物和情節,完全來自現實生活,而在這些故事和人物身上,又寄托作者的感慨、牢騷和不滿”。董建華《從(綠野仙蹤)看作者李百川的心態》指出,《綠野仙蹤》的主題是表現功成名就思想。首先,主人公冷于冰“求仙訪道,與其說是消極退隱,不如說是曲線救世”,他利用道技仙術參加歸德平叛,發起平涼放賑,成就他人功名;作者現實中不能實現的愿望,通過作品中朱文煒、林岱的成功去表現,入世用意是十分明顯的。其次,作品在宣揚道教文化的同時,也不時表達對道教學說的懷疑。“作者的理想天堂勝境就是人間的高官厚祿,富貴奢華”,而這恰好是他人生理想的翻版。再次,李百川生于末世而不敢發泄對末世的不滿,就“借助作品,讓自己在虛構的世界中自由自在地徜徉,尋求希冀與寬慰”。
李峻鍔、徐潤拓持第二種意見。李峻鍔《道教文學作品(綠野仙蹤)淺析》認為,《綠野仙蹤》是宗教文學作品,“通過描繪社會生活,宣揚宗教思想”。他還從作品賴以產生的明代背景分析這種出世主題的根源,“在尖銳復雜的各種社會矛盾交織之中,社會上很大一部人就幻想要脫離現實以超脫于尖銳復雜的社會矛盾之外。宗教小說《綠野仙蹤》中極力宣揚的摒棄富貴、割斷塵緣、修道成仙的思想,就是這部分社會意識的反映”。徐潤拓《(綠野仙蹤)求仙主題中的死亡意識》認為,小說主人公冷于冰一生經歷了兩個重大轉折,“一是由仕進到退隱,二是由現世到求仙”,第一個轉折是對社會現實理想的幻滅,由奸臣當道的社會現實所造成;第二個轉折是對生命長駐希望的幻滅,在無路可退的情況下,出于對死亡的恐懼,只能將獲救的希望寄托于神仙道術上,認定了小說的出世主題。
伍大福持論介于上述兩種觀點之間。其《試論(綠野仙蹤)的非儒思想》認為作品寫封建末世儒家文化的衰微,而張揚道家、俠義文化救世的理想。一方面,“時至明清,士人言順行悖儒學的本旨已盡現儒學的衰微。《綠野仙蹤》正是借小說中的形象對儒學這一根本價值觀進行了現實的反思,讓我們得窺儒學沒落的迂腐和蒼白”。證據是儒家思想核心是內“仁”外“禮”,但小說中葉體仁:周璉等人卻為富不仁、為人非禮;儒家思想基礎是“內圣外王”,但小說中的皇帝卻荒淫昏庸、忠奸不分,權臣嚴嵩只知貪污受賄、黨同伐異,致使士人“‘身不能修,‘家不能齊”;儒家政治理想是“立德、立功、立言”,而作品中的儒家君子離開仙道幫助就不能成一點功業,等等。
四、關于作品成敗和文學地位
《綠野仙蹤》神魔、講史、人情三大板塊,一般學者都認為人情部分寫得最出色,其次是講史部分,神魔部分最蒼白,侯忠義認為:“就像這部小說的主人公、仙人冷于冰,是一個蒼白無力、非常概念化的人物,倒是作者并非著意的連城璧、金不換等人物,卻寫得有血有肉、可真實感一樣,我們肯定有較高認識價值的,是指書中所反映的現實內容。”林虹指出《綠野仙蹤》真正出奇的恰恰是在寫日常起居的人情部分。理由是人情部分以家庭為畫面充分展示了明代多姿多彩的社會生活,成功塑造了許多世俗人物群像。林虹還分析了《綠野仙蹤》問世以來沒有引起轟動效應的原因,間接指出了它的不足之處,第一,藝術表現極不均衡,小說最出色的是人情部分,而神魔部分卻多所依傍,缺少創新。第二,作品中心人物冷于冰形象過于理想化以致遠離人世、脫離現實,流于蒼白浮泛;假如寫一部貧士冷于冰的現實經歷更能打動人心。第三,作品創作于所謂“乾隆盛世”,社會己到了盛極而衰的轉折點。面對這個行將崩潰的時代,作者缺乏對傳統思想文化的反思,缺乏同時期《紅樓夢》和《儒林外史》中的強烈的反叛精神。
李國慶《綠野仙蹤·前言》指出,作品在小說史的地位,是它“吸收了前人在各方面的成功經驗,將歷史、神魔和世情熔于一爐,為中國古典小說增添了一道獨特而亮麗的風景,雖然對這一大膽的藝術嘗試之得失見仁見智,卻無法否認它為中國小說發展史留下了寶貴的研究個案”。董建華《試論(綠野仙蹤)題材類型的多元化》揭示了類型多元化的必然性:“一是憑空搗虛的難,二是小說發展到清朝中葉,各種小說體制都已完備,并且都出現了難以企及的典范之作,為了有所突破,有所創新,只好從題材角度加以翻新或者寫前人尚未挖掘過的題材,或者將性質不同的題材融為一體,《綠野仙蹤》屬于后者。”都是中肯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