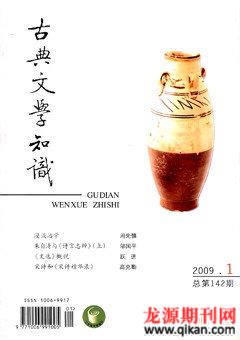明太祖之“稍遜風騷”
李 鵬
在歷代帝王中,明太祖朱元璋并不以文采風流見稱。由于出身寒微,他并沒有受過什么系統教育,只是在皇覺寺當和尚時因為學習佛經掌握了一些粗淺的文字。但在起事之后,他與身邊文士朝夕過從,憑著過人天資與勤奮好學,居然從一個識字不多的半文盲,逐漸變成一個提筆就能賦詩作文的人。而且,隨著社會地位的改變以及對詩文創作神秘感的消失,他居然以大化教主、文章高手的姿態指點古今文人應該如何寫作。這不能不讓人驚嘆,同時也更令人好奇:朱元璋的詩文創作水平究竟如何呢?
一
照劉基的說法,朱元璋是“兼全文武”(《御制文集后序》),不僅起兵從元人手里奪得天下,還有《明太祖集》二十卷傳世,其中除了應用性質的行政公文如詔、制、誥、敕等之外,還有不少記敘、議論文字以及詩賦等,文之眾體,粲爛俱備。
集中有些文字,讓人讀后覺得和飽學宿儒、文學俊秀之作似無分別,例如,《明太祖集》卷一○《時雪論》寫道:“俄而風生八極,云幕長空,良久雨降,自朝抵暮,萬物被澤。至夕,翩翩飛舞,雪墜九霄。曉來辟戶以觀,近山五砌,遠景銀妝,此天地嚴凝之氣至矣。”這和卷一四《睹春光記》開頭那段以及卷一六《跋夏珪(長江萬里圖)》、《題(趙千里江山圖)》等,不僅物象摹寫生動,而且辭氣整麗卻又不失流蕩,極具語言文字之美。只是這類文字好得超出人們的想象。因此不免讓后人懷疑是否經過了宋濂、劉基等詞臣的潤色。
不過,文集中一些粗枝大葉、淺俗雄直的文字應該確實是朱元璋所作,其中盡顯朱氏之本色。
卷一四有《皇陵碑》一文,記敘的是朱元璋自己的艱難身世,在回顧往日艱辛時飽含感情,絕非儒臣代筆的粉飾之文。例如記敘他棲身的寺廟解散后,他不得不托缽流浪,形同游丐:“突朝煙而急進,暮投古寺以趨蹌。仰穹崖崔嵬而倚碧,聽猿啼夜月而凄涼。魂悠悠而覓父母無有,志落魄而俠佯。西風鶴唳,俄淅瀝以飛霜。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滾滾乎沸湯,”這段文字極具感染力,可是讀者若從文字渲染的情境中抽身出來對文字本身加以細細體味,不難發現朱元璋雖然很恰當地用了文人常用的“猿啼”、“鶴唳”、“飛蓬”等意象語詞,辭氣卻仍顯得拙澀,缺乏老練文人筆下常見的整齊與流暢。整篇文章雖然粗枝大葉,但敘事明晰,更兼通篇用韻、貫注而下,因此粗服亂頭亦顯雄豪之氣。
如果說朱元璋寫《皇陵碑》這樣的文字還有點勉為其難的話,那么他寫《諭西番罕東畢里等詔》(《明太祖集》卷一)這類的文字就顯得當行本色多了。詔文不長,迻錄如下:
奉天承運的皇帝,教說與西番地面里應有的土官每(引者按:們)知道者,俺將一切強歹的人都拿了。俺大位子里坐地,有為這般上頭諸處里人,都有我行拜見了,俺與了賞賜名分,教他依舊本地面里快活去了。似這般呵,已自十年了也。止有西番罕東畢里、巴一撒他每這火人,為甚么不將差發來,又不與俺馬匹牛羊?
今便差人將俺的言語去開與西番每知道:若將合納的差發認了送將來時,便不征他;若不差人將差發來呵,俺著人馬往那里行也者。
教西番每知道:俺聽得說,你每釋迦佛根前,和尚每根前,好生多與布施么?道那的是十分好勾當,你每做了者,那的便是修那再生的福。有俺如今掌管著眼前的禍福俚,你西番每怕也那不怕?你若怕時節呵,將俺每禮拜著,將差發敬將來者,俺便教你每快活者,不著軍馬往你地面里來,你眾西番每知道者。考慮到聽詔書人的語言理解力,詔書是用淺俗的白話寫的,有很多語氣詞,讀起來和元雜劇里的說白并無二致。雖然語言明白如話,但在結構安排上卻層次井然:先是說明自己政權的合法性;然后是利誘,說歸順了的人得到諸多好處;再次就是威逼,倘若不順從,就要大軍壓境;最后從對方的信仰入手,言下之意自己是掌管現世禍福的神佛,增加對對方心理上、思想上的威壓。全文猶如“嚇蠻書”,態度強硬,語氣狂橫,有帝王君,臨天下的氣勢。
在《戒庵老人漫筆》卷一“半印勘合戶帖”條也記載了朱元璋一詔書:“說與戶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戶口不明白哩……”語氣聲口,如話家常。而該書卷一“太祖御札”條所載朱元璋在登基前寫給手下將領吳國興的四封親筆信,也是如聞其聲。這類口氣生動的文字在《天府廣記》卷六、《皇明制書》里還能發現一些。這些文字,如果拿文人傳統去衡量,不免被視為鄙陋;但若從發揮文體實際功用的角度看,則這類“我手寫我口”的文字更容易實現傳播和交流的目的。
除此之外,集中像卷一六《江流賦》中“岸邊綠葦,滴溜溜風擺旌旃;堤下青蒲,孤聳聳露依劍刃,白蘋渡上,有一攢一簇白沙鷗:紅蓼灘前,有一往一來紅甲雁”之類文字,與文人賦的典雅厚重距離較大,顯得淺俗不少,讀者從中也能讀出元雜劇曲詞的味道。
朱元璋的詩歌,大多極力追隨文人傳統意趣,偶爾也有稍佳之作,如《明太祖集》卷二○《早行》:“忙著征衣快著鞭,轉頭月掛柳稍邊。兩三點露不為雨,七八個星尚在天。茅店雞鳴人過語,竹籬犬吠客驚眠。等閑擁出扶桑日,社稷山河在眼前。”此詩首聯粗糙;頷聯和頸聯分別化用辛棄疾“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以及溫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句,頗為貼切;尾聯氣勢磅礴,此聯一出,全詩頓時為之生色。此外還能覓出一二稍佳之句,如“禁城新柳葉成帷,隱映黃鸝深處啼”(卷二○《鶯囀皇州》其二)、“薄暮欲歸星月上,流螢點點近船舷”(卷二○《巨罟叟漁魚》)等。
但最能體現朱元璋特點的,是那些不假雕琢、放筆寫去的詩歌,它們往往于粗豪中見天然野趣。例如《明太祖集》卷○《詠雪竹》:“雪壓竹枝低,雖低不著泥。明朝紅日出,依舊與云齊。”同卷《詠菊花》:“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都嚇殺。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廠兩首詩都是通過詠物來抒懷,心氣極高,后一首脫胎于黃巢《不第后賦菊》一詩,但比起原詩宋更為直露,也更顯得殺氣騰騰。同卷《不惹庵示僧》:“殺盡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劍血猶腥。山僧不識英雄漢,只恁嘵嘵問姓名。”詩里盡顯粗豪之氣,倒也符合作詩者身份。
總之,朱元璋文才有限,那些真正屬于他自己創作的詩文因此不免粗淺直白,但不假雕琢中頗見雄豪之氣,讀其文不難想見其人。正如趙翼評價的那樣:“明祖以游丐起事,目不知書,然其后文學明達,博通古今,今所傳御制集,雖不無詞臣潤色,然英偉之氣自不可掩。”(《廿二史札記》卷三二“明祖文義”條)
二
朱元璋是從社會最底層的“布衣”成為最高統治者“天子”,他自己對此并不諱言,在建國之初頒布的一系列免糧稅、求言詔書里,一再自稱“朕本淮右布衣”、“朕本農夫”等,很是清醒和低調。此后朱元璋竟然能像風雅的文人士大夫那樣做起詩文來,除了他自身的勤奮好學以及聰敏過人,絕對離不開他身邊像宋濂、劉基這些著名文人的熏陶。雖然如此,朱元璋并沒有把這些文士視為“師友”。在和文士的關系中,朱元璋一直居于主導地位,即使是最初的禮遇背后也暗藏著緊張,最后連表面上的禮遇也撕去時,文士們愈發如履薄冰。
培育文學藝術方面的能力,按照凡勃倫的說法,應該是有閑階級為了彰顯自己身份不同于粗鄙之人的一種做法(《有閑階級論》)。出身社會底層的人,有很多是像劉邦那樣具有反智傾向的,不讀書,并且對讀書人加以肆意嘲弄;有些則是渴望通過讀書使自己能夠融入到這個被他們認為更高貴的階級里去。在朱元璋身上,恰恰兩者都有,這就使得他和文士之間的關系復雜起來:一方面,是羨慕和渴望接近;另一方面,文化上的自卑很容易被激化成對掌握文化的文士的敵視,而且由于他擁有絕對權勢,往往通過對文士的任意打擊來獲得心理補償。
關于前者,我們從朱元璋攻下集慶(今南京)后立即禮聘夏煜、孫炎、楊憲等十余人,攻下鎮江后禮聘秦從龍,攻占浙江等地后建“禮賢館”延請浙東四大文士(劉集、宋濂、章溢、葉琛)等類似行為中不難看到,所謂“禮賢下士”,雖然掩蓋不了居高臨下、為我所用的實質,但此時朱元璋對文士起碼還有表面上的禮遇。
關于后者,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三二“明初文字之禍”條有一說法很值得注意:跟隨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對朱元璋重用文士不滿,他們提醒朱元璋“文人善譏訕”,當初張九四厚禮文士,可后來他請文士幫自己取一個文雅的名字時,文士們給他取名“士誠”,而《孟子》里有“士誠小人也”句,張士誠被文士罵作小人還美滋滋地以為取了個好名字。朱元璋聽了這個故事之后,“覽天下章奏,動生疑忌,而文字之禍起云”。趙翼把明初的文字獄歸因于朱元璋學問不夠好、對文字理解有誤顯然過于簡單,但若說朱元璋因為文化上的自卑而對文士產生疑忌心理卻頗為合理。
文化上的自卑促使朱元璋對文士采取更為嚴苛的態度,其極端就是通過毫無道理的文字獄來迫使文士承認他朱元璋是至高無上的統治者,文士們再有才、再有學問,都必須絕對臣服于他,文士的尊嚴被他肆意踐踏、蹂躪,而他則在生殺予奪中享受著極權帶來的威嚴與快意。《明史》卷二八五《文苑傳·張孟兼傳》載劉基對朱元璋說過:“今天下文章,宋濂第一,其次即臣基,又次即孟兼。”可這文章三甲在朱元璋手里的命運最終都不怎么樣:宋濂被安置茂州,卒于夔;劉基被羈管于京城,據說是被毒死:張孟兼棄市。翻檢《明史·文苑傳》,不難發現明初著名的文人像蘇伯衡、戴良、王彝、高啟、楊基、張羽、徐賁都不得其死(可參看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三二“明初文人多不仕”條)。明初文士們選擇出仕往往意味著頭顱難保,《稗史匯編》卷七四“皮場廟”條說當時京官每天早上去上朝時,都得跟家人訣別,等到傍晚平安回來,舉家歡慶又多活了一天。
但是,此時的文士們又無法像傳統文士那樣飄然遠舉、歸隱山林。王佐“性不樂樞要,將告歸。時告者多獲重譴,或尼之曰:‘君少忍,獨不虞性命邪?佐乃遲徊二年,卒乞骸歸”(《明史·文苑傳·王佐傳》)。可見,在明初告歸退隱是有性命之虞的。個中原因,從《明太祖集》卷十《嚴光論》一文可以略窺一二。嚴光是東漢著名的高士,是文士傳統中一個具有象征意義的人物,但朱元璋在文中認為,嚴光在東漢建國之初急需人才時不為中興貢獻才智,反而以隱逸為高尚,純屬“處心有邪者”、“沽名釣譽者”,是國家最大的罪人。正是基于這樣的看法,朱元璋在《大誥三編》第十三條“蘇州人材”里明確規定:“寰中士夫不為君用,是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在朱元璋看來,有學問才識卻不為君用就是目無君上,這樣的人留著也沒用,就該殺頭抄家。朱元璋也許讀過《韓非子》一書,因為類似觀點深得《韓非子》論君臣關系的精髓。
顯然,碰上朱元璋這樣的君主,文士們是進亦憂,退亦憂,無所措其手足。
三
為了獲得更大的心理優勢,朱元璋不僅對文士施以高壓,還對他們加以恣意評點或指斥。
作為務實的一代雄主,朱元璋骨子里和他前面的漢武帝以及他后面的乾隆帝一樣,對文士是“倡優視之”,認為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是干不了什么大事的(劉基是個例外),只是用來備備顧問、點綴點綴升平。例如,朱元璋對宋濂的真實看法就是“爾濂雖博通今古,惜乎臨事無為,每事牽制弗決,若使爾檢閱則有余,用之于施行則甚有不足”(《明太祖集》卷三《翰林承旨宋濂誥》)。他認為宋濂雖然才華學識出眾,但缺乏決斷,辦不了什么實際的事情。號稱“開國文臣之首”的宋濂尚且如此,其他人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
即使是對于文士們最擅長的詩文創作,朱元璋也越來越不以為然。洪武七年(1374),朱元璋擬于獅子山上建閱江樓,讓眾文臣“作文以記之”,文臣們把文章交上來后,朱元璋瀏覽之后認為:“節奏雖有不同,大意比比皆然,終無超者。”(《明太祖集》卷一四《閱江樓記有序》)由于覺得所有文臣包括宋濂所作都沒有什么突出的,他干脆親自寫了兩篇《閱江樓記》,一篇是用自己口氣寫的,另一篇是“假為臣言而自尊”,即用臣子的口氣寫的。這一事件頗有意味,表明朱元璋內心深處潛藏的文化自卑在其君臨天下后轉化為極度的妄自尊大,此時的他認為自己的文才超過當代所有文士。不僅如此,朱元璋甚至對歷史上公認的古文大家韓愈、柳宗元的文章也頗有微辭,他在《諭幼儒敕》(《明太祖集》卷七)、《駁韓愈頌伯夷文》(卷一三)、《辨韓愈訟風伯文》(卷一三)一系列文章里指摘韓、柳,儼然以帝王之尊來指導人們該如何寫作(參看郭預衡《朱元璋之為君和宋濂之為文》,《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6年第3期)。
文學藝術才能本來是屬于文士們最引以為傲的看家本領,同時也恰恰是出身寒微、缺乏文學藝術教育的朱元璋最薄弱的地方,而登上權力巔峰的朱元璋偏偏要在這一領域證明自己比古今文士都高明。不難想見,在朱元璋對古今文士肆意指斥、橫加羞辱的過程中,他最初的文化自卑心理終于獲得了最大限度的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