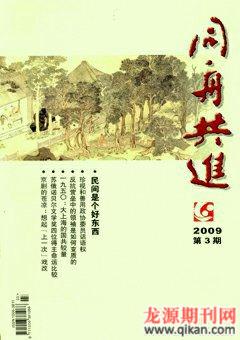文明的道路:“禮失求諸野”
余世存
作者簡介 文史學者,1990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曾任《戰略與管理》執行主編,有《非常道》、《重建生活》等著作。
中國的現代化轉型已近兩百年。初期的應戰,幾乎且戰且退,從技術、制度到文化等領域,我們的傳統在人家的現代化面前一敗涂地。經過慘烈的國內外戰爭、改良、改革、革命、動亂、亂動等社會形態,我們最終確立了一個近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框架,只是個人、國家和社會的現代性價值仍處于探索之中。今天,最近一輪現代化改革也已30年——我們的現代化道路通往何方仍是一個聚訟紛紜的問題。
傳統社會對禮樂崩壞的應對很簡單——“禮失而求諸野”。孔子這樣的圣賢都明白,在社會劇烈變遷過程中,要從民眾那里獲得變革的基礎,從民間獲得創新禮樂的靈感,以重建我們的生活方式和文明模式。這種民本主義的思想是最簡單也最偉大的思想。
我們的現代化是一種后發性的現代化。它的好處是可以很快地復制出一種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體制;但它的負面因素在于,后發現代化難有積累,思想相互攻伐,遲遲不能進入持續不斷的社會變遷,呈現出楊小凱所說的“后發劣勢”。更為關鍵的是后發現代化最容易把民眾當工具。因此,一個常見的現象是,后發現代化國家的知識精英們與民眾日益拉大距離:他們的思想是發達國家的思想,有一種近乎媚時的觀念崇拜;他們對民間社會的態度情緒化,一會兒無限地仰望,一會兒無限地蔑視;他們對民間避而遠之,甚至從發達國家那里學會了如何教訓民眾。
起第一代啟蒙思想家于地下,他們會對當代社會的戲劇性現象目瞪口呆。
在我們的民眾之間、官民之間、人與自然之間,價值似乎已是奢侈品,甚至已被廢棄,許多東西都以勢利、價格來衡量了——不要只說官員腐敗,官腐民敗在某種程度上已成為新的社會規則。
“禮失而求諸野”,這樣一句古老的圣言在今天有著更新鮮的含義。
跟傳統文明中民間鄉野保存并發展著傳統的禮樂精神不同,今天的“求諸野”更是一種價值指向,是一種文明的反哺。
今天的“求諸野”并非經濟學意義的財政轉移支付,或單純政治學意義上的藏富于民,而是一種文明品質。從生生之為大德、天人合一、推己及人,到“明德、新民、至善”,再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說明還權于民、啟智于民、藏富于民的社會才是人類社會演進的至上標準。
今天的“求諸野”更非對自然的予取予奪。不是打著保護環境的名義,將草地鏟去再種上整齊劃一、聽話如茵的小草;不是借口綠化指標,就將世代居住的家園“拆了”,把原地變成所謂的現代公園……
“禮失而求諸野”,自然還有其他同樣重要的文明意義。
因為我們失掉的不僅是簡單的生活生存禮儀,在生老病死、吃穿住行、婚喪嫁娶方面,我們完全被流行或湊合主導了。我們也失掉了最為基本的交往溝通規則,至今還未能產生理想的文明關系及其制度。尤其是后者,使得眾多國民生活得飄忽不安,甚至不無憂懼。
我們的成就和危機同樣引人注目,如何擺脫這種格局,就在于“拿來”文明并跟中國社會博弈出一種自家的禮儀制度——
“求諸野”并不限于民間,“拿來主義”也是它的固有內容。從商開始,甚至更早,華夏文明就不斷學習、師法先進的有用的文明成就。胡服騎射、魏文帝南遷洛陽、宋儒援佛道入儒,都是“求諸野”的表現。這種拿來主義為孫文、黃興、胡適、魯迅等一代啟蒙大家所明認。孫中山甚至從細節入手,希望“拿來”其他文明的規則制度以改進中國的會議效率。
他們的做法值得今人深思。在前賢的成就面前,那些全盤否定他人文明的論調同全盤肯定傳統者一樣,不過是在搗糨糊、拆爛污。固然,今天的國際環境不同于以前,發達國家經受著考驗,但我們仍可以關注它們自我療救的文明能力、制度優勢。“禮失求諸野”,它們的經驗乃至教訓對于轉型中的中國仍是有益的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