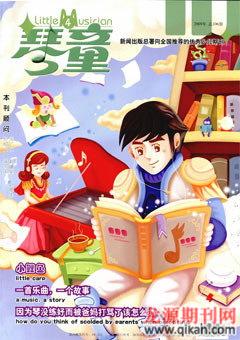馬勒與他的《第八交響曲》
孫 奎
孫奎中提琴演奏家。2000年5月,以優異成績進入中國愛樂樂團,圓滿完成2001-2008年間7個音樂季和7屆北京國際音樂節的演出,同時還參演了大量中外著名交響作品的演出。2002年6月隨團赴美,參加在圣何塞、洛杉磯和舊金山等地的美國西海岸巡演。2003年9月出訪歐洲,在著名的巴黎國家歌劇院、華沙國家大劇院和維也納金色大廳舉行了輝煌的演出。作為演奏家一員,2005年2月至4月隨團遠渡重洋,歷時40天,在美國、加拿大、意大利、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英國、德國等國家的22個城市成功舉辦了交響音樂會。
在我的藝術生涯中,馬勒是我最喜愛的作曲家之一。作為中國國家愛樂交響樂團的一員,我演奏過馬勒的全部交響作品,尤其令我震撼的是作曲家的《第八交響曲》。2002年,一年一度的北京國際音樂節迎來了中國音樂界空前的藝術盛事,這就是:由指揮家余隆執棒在保利劇院首演馬勒《第八(千人)交響曲》。這是這部巨型交響作品第一次在中國亮相,由來自海內外8位歌唱家、3個交響樂團、7個合唱團和1個童聲合唱團組成強大的演出陣容。我和愛樂的演奏家們在舞臺上縱觀數百歌手組成的合唱隊,加之我們二百多人超大型的交響樂隊把二十多米深的舞臺占據得滿滿當當。指揮家余隆面對這場中國從來沒有過的交響樂演出,激情四射,輝煌起棒,近千人的合唱進發的聲浪驚撼整個大廳,感動著全場1400名觀眾,這就是中國交響史前所未有的巨獻——馬勒《第八交響曲》演出時的壯觀場面。80分鐘的音樂在藝術家的演繹中徐徐進行,而我胸中涌起對作曲家的尊重和敬仰……
馬勒生活的年代,正是資本主義走向帝國主義階段的時期。馬勒所生活的奧匈帝國,是一個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交織在一起的、危機四伏的國家。雖然同是日耳曼民族,但因為德意志比奧匈帝國強大,因此奧地利人常常受德意志人的欺凌;在奧匈帝國內部,波希米亞人又作為被壓迫民族而受奧地利人的歧視。馬勒常說,“我是三重的無家。在奧地利作為一個波希米亞人,在日耳曼人中作為一個奧地利人,在世界上作為一個猶太人,在哪里我都是闖入者,永遠不受歡迎。”這樣的社會背景,促使馬勒對當時黑暗的社會現實有著清醒的認識。早期的作品曾寫過一首名為《塵世的痛苦》的歌曲,真實反映了農民的生活現狀。
“媽媽呀,媽媽,我餓死啦快把吃的給我呀!”
“稍等待,稍等待,我心愛的兒,等我快快未收割莊稼!”
當莊稼剛被割下,孩兒又在叫媽媽:“媽媽呀,媽媽,我餓死啦快把吃的給我呀!”
“稍等待,稍等待,我心愛的兒,等我快快把稻谷打!”
當稻谷剛被打下,孩兒又在叫媽媽:“媽媽呀,媽媽,我餓死啦!快把吃的給我呀!”
“稍等待,稍等待,我心愛的兒,等我把面包來烤好!”
當面包剛剛烤好,這小孩已經餓死了!
馬勒的音樂活動遍跡維也納。面對黑暗的現實,音樂家有兩種不同的態度:一種是否定現狀卻找不到出路,因而悲觀、迷茫;另一種則是粉飾現實、鼓吹醉生夢死。馬勒持第一種態度卻不斷找尋出路。在他創作的9部交響曲以及聲樂作品中,表現出對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對理想生活的憧憬,我們可以聽到他那優美極有生命力的交響力量以及對大自然和人生的贊嘆。同時馬勒的音樂又會流露出對黑暗現實的不滿和嘲諷,出現一些怪誕痙攣的節奏,尖銳喊叫般的音響,真實反映了作曲家的心理掙扎;有些作品馬勒從哲學、宗教的角度對人生問題進行求索,甚至消極得出人生是虛罔的,生靈只有在天國才能得到安息的迷惑。反映了處在帝國主義時代的知識分子世界觀的局限。
在藝術風格上,馬勒的作品繼承了后期浪漫派音樂的傳統,拓展交響樂的表現力,發揮每件樂器的表現性能,造成音樂色彩絢麗的配器效果。從極其纖柔的輕奏到濃重而震撼人心的音響,瞬息萬變、五彩繽紛。他探求龐大的樂隊編制,根據音樂的需要擴展樂曲結構,用以表現巨大飽滿的樂思,馬勒將合唱加入交響樂并采用大量的民間音樂元素,如:波希米亞民間音調和奧地利民間舞蹈的節奏,均在作品中有特別的表現。在19、20世紀之交,像馬勒這樣在創作中積極采用民間音樂的作曲家,是難能可貴的。
馬勒的交響曲在形式上具有構思宏偉,規模龐大的特點,只有巨型的交響樂隊才能演奏,在風格上,他力求發展維也納古典交響樂的傳統一作品形象鮮明,題材淵源于維也納民間風格性音樂。除《第一交響曲》外,其他交響曲都加入了人聲合唱,大大豐富了交響樂的表現力,對20世紀音樂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馬勒的《第八(千人)交響曲》是一部輝煌的前無古人的龐大作品,其編制規模稱得上是古典交響樂中的“巨無霸”。在馬勒之前,沒有作曲家可以將交響樂的編制擴大到如此規模。這部交響曲于1910年9月12日由馬勒親自指揮首演時,共選用了858位歌手(兩個混聲合唱團,一個童聲合唱團,八位獨唱演員)以及171人的交響樂團(四管編制,另加管風琴)。馬勒對指揮家門蓋爾貝格說:“這是我以往作品中最大的,無論從內容上還是形式上,都是不能用語言加以表達的獨特性作品……所有我以前的幾部交響曲只不過是這部交口向曲的前奏曲。在那些交響曲里還有我個人的悲劇因素,而在這里則是偉大的喜悅和榮光。”作為馬勒本人,他的愿望是通過這部交響曲,能夠像他所尊敬的貝多芬《第九交響曲》那樣,借助于對上帝、天國的贊美,宣揚人類之愛。
作品第一部分根據9世紀的一首贊美詩而創作,命題為《造物主圣靈降臨》;第二部分是一部連續演奏的交響詩,命題為《浮士德的結束場景》。馬勒生活在世紀之交的年代,他的作品傳達出了對往昔的回顧和對新世紀的向往。一種氣勢磅礴和催人奮進的音樂情緒使這部作品有著以往音樂家創作所沒有的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力量。總體布局上,第一部分占時二十多分鐘,第二部分將近一個小時。由于題材不同(前者為歌頌性質,后者為敘事型),因此體裁上也有所變化(前者更接近眾贊歌,后者則更靠攏清唱劇);如果說第一部分在一個相對集中時段讓我們幾乎一直處在興奮和激動的高潮當中,那么,第二部分隨著戲劇性的展開,令聽眾處在有序的張弛體驗之中。面對美妙的人聲交響,欣賞時除了把握一般感受上的龐大空間中的渾厚音響復雜層次之外,還要注意音樂在起伏、厚薄、濃淡諸多層面的分離和聚合,比如:終曲部分當游離的各部音樂開始大面積多重合流,整體力度開始長時段地持續高漲時,那種聲音的透徹和敞亮更是極其輝煌震撼,再現最初的音樂元素,通過指揮的聚合最終實現終極轟鳴的瞬間,妙不可言,令人感動。那是靈魂深處升華;音樂的力量通過高強度的緩釋,大面積的緩沖,再通過高能量的緩動,一種雪崩塌瀉和熔巖噴射般的壯觀頓然顯現。就像歌德《浮士德》末尾詩句所說的:“一切無常者,不過是虛幻;力不勝任者,在此處實現;一切無可名,在此處完成;永恒的女性,領我們飛升。”《第八交響曲》中,人聲參與解釋和發展整個交響套曲的音樂思維,使馬勒成為20世紀流行的“歌曲中的交響樂”體裁的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