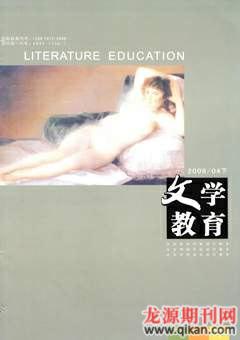語文課堂精細化教學策略
語文教學走過了一條“由瑣細到粗放”的曲折的山路。以前重語法分析,一篇文章被分析到支離破碎,弄得學生只見樹木不見森林,被有識之士斥為“語言研究”。現在,時髦的語文教學又搖身一變,成了全武行式的“說書”,“聽眾”對什么感興趣,“說書人”就投其所好,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泛語文化”,還要美其名曰“延伸”“拓展”,而真正決定文本價值的東西卻鮮有涉及。這樣一堂“虛假繁榮”的課,學生如墮五里霧中,恐怕是難以培養學生語文素養根基的。
要走出目前語文教學的困境,課堂教學實施“精細化”策略,實屬當務之急。
這里的“精細化”不同于企業管理的“精細化”。語文課堂教學的“精細化”指的是著眼于文本,通過對決定文本意義的知識點的具體而細致的分析和探討來完成對文本的解讀。這里的“精”指決定文本意義的知識點(理所當然它也是課堂教學目標),“細”取具體而細致之意。語文課堂教學,每一堂課應該也必須給學生明晰的知識點(學習目標)——這個(或者這些)知識點是“提綱挈領”的“綱”和“領”,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發”——通過師生對知識點細致入微的討論,讓學生在有限的時間內獲得最大的收獲,從而提高課堂效率。
要在語文課堂上真正科學地做到“精細化”,關鍵是教師要找準文本的“綱”和“領”或者是“發”,確立好科學有效的課堂教學目標。比如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開》,學生沒有哪個字不認識沒有哪句話不理解,要讓學生們背下來也很容易。那么,是不是學生這樣就把文本讀懂了呢?是不是這樣老師就完成了教學任務了呢?顯然不是。只有抓住詩中的“從明天起”“我只愿”這些字眼,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海子一直是孤獨地一直是童真般單純地生活在自我的精神世界里,他也毫無悔意地執著地生活在自己的精神家園里。這才是詩中的“我”,這才是這首詩的價值所在。比如史鐵生的《我與地壇》,作者在第一章里對地壇景物有十分生動形象的描寫,學生對這些文句也非常感興趣。課堂教學時,教師如何處理?是定位于語言賞析,引導學生如何讓語言生動形象更有韻味?還是定位于如何借景抒情情景交融?教師在一堂課上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分輕重、蜻蜓點水。比如李樂薇的《我的空中樓閣》,語言有特色,形式上又突出了散文“形散”的特點,立意上托物言志又極其含蓄隱晦。教師如何取舍?可是,就有教師在課堂上煞有介事地大談特談《面朝大海,春暖花開》的作者海子這名字應該怎么念,是該念成hǎi﹒zi,還是念成hǎi zǐ,對海子臥軌自殺面朝哪個方向手上拿著什么書津津樂道。還有教師在課堂上讓學生討論《我的空中樓閣》的作者李樂薇是男性還是女性。這些東西對理解文本有決定性意義嗎?如果目迷五色耳亂八音,教師不能從實際出發確立具體的教學目標,或者確立的教學目標不科學,課堂教學必然是無序的,課堂教學效率必然是低下的。
語文課堂教學的“精細化”首要的是確定一定的教學目標。文本和學生的學習實際是確定課堂教學目標的最主要的依據。
語文課堂教學的“精細化”還特別注重過程。為了達成一定的教學目標,教師的教學活動和學生的學習活動必須是具體的。教師在課堂教學中,依據預設的教學目標,激發興趣,循循善誘,啟發點撥,師生互動,在學習的過程中自然地達成教學目標。這一過程,既是教師的“導”的過程,更是學生學習、感受和體驗的過程,也是學生生成知識的過程。比如《〈吶喊〉自序》,魯迅先生旨在說明自身經歷、思想發展變化與《吶喊》問世的密切關系,所以序文極其精練地介紹了自己不同時期經歷的幾件具有代表性的事例以及探索救國救民思想發展變化的進程。在課堂教學中,教師引導學生理解魯迅先生的生活經歷、思想的發展變化,討論它們與《吶喊》的關系,思考作者“吶喊”的緣由和目的。自然而然,文本的寫作目的學生理解了,序言的性質學生也弄懂了。這樣的學習,學生目標明確,過程踏實,收獲具體而扎實。
須要注意的是,語文課堂教學的“精細化”,體現在課堂教學目標的確立上,教學目標不一定是單一的,可以是多維度的,如知識、能力、情感等等;體現在過程方面,可以有不同的學習方式,如交流、合作、探究等等。
“精細化”的語文課堂教學,可能是診治語文教學“少、慢、差、費”頑癥的一個好方子。
高國營,教師,現居湖北武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