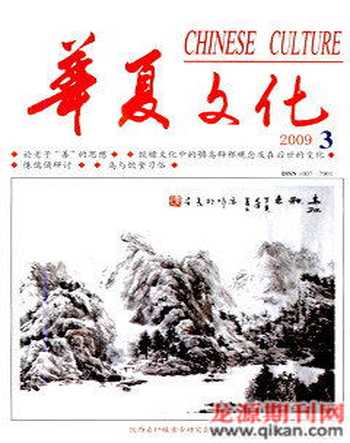漫談古代的長隨
劉文瑞
古代的官員到一方任職,人生地不熟,面對著隊伍龐大、精通各種關節、操持當地政務的六房書吏和四班衙役,必須打點起十二分精神認真負責對付。弄不好,一旦長官的舉措妨礙了這幫人的財路,他們就會在不知不覺中給長官設個套,挖個坑。所以,任何官員,少不了警戒提防之心。而長官用來監督牽制吏胥的,主要是長隨和師爺。
按照趙翼《廿二史札記》“長隨”條的考證,在明代,長隨本來是那些跟隨大宦官的小宦官,就像金庸小說中冒充小宦官跟隨海老公的韋小寶那樣的角色。到了清代,長隨成為對官員跟班的俗稱。“今俗所謂長隨,則官場中雇用之仆人,前明謂之參隨。”清代長隨的身份,是長官的私人雇員。這種私人雇員,有可能是來自家庭仆人,但更多的是來自熟悉行政情況的官場油子。因為家仆雖然忠心耿耿,但多數不了解官場運作。而長隨需要熟悉衙門的各種成文不成文規矩,尤其是要熟悉拿不上桌面的行情慣例。比較老實的官員,往往依賴于同年相好、鄉梓前輩以及座師恩公給他們物色和推薦長隨。長隨的好壞,對官員影響極大。
長隨是官員的私人跟班。州縣長官到任時,要提防書吏和衙役,可以依賴的就是長隨和師爺。師爺的主要作用在于出謀劃策,長隨的主要作用在于監控吏胥和行政執行。他們雖然被吏胥尊為“先生”和“二爺”,但不屬于官方雇員,僅僅對主官個人負責。由于長隨是事務性的,所以比師爺人數多,一個知縣,長隨少則一二十,多則上百人。如果說吏胥構成官府的“外衙”,師爺和長隨則構成主官的“內衙”。從漢代開始的“中外朝”格局,至此滲透到政權末梢。
長隨中最主要的,有負責把門的司閽(或稱門上),負責文書簽轉的簽押(或稱稿案),負責保管和使用印信的用印,以及司倉、管廚、跟班等。有的還有公堂值勤的值堂,負責通訊的書啟等。由于長隨是主官的親信,而主官往往要提防六房書吏,所以,時間一長,長官就會委派長隨掌管書吏事務,如負責稅收的錢糧,負責監所的管監,負責驛站的管號,負責雜稅的稅務等。長隨的職能有:監督進出衙門的人員,通稟來客來訪,充當州縣長官與書吏衙役的中介,收發公文并監督公文處理程序中的各個環節,監督案件審判的準備情況,參與案件審訊,處理審案瑣務,監督獄卒和囚犯,查看稅冊,解送稅款和漕糧,監管倉庫和驛站,辦理相關雜差等。“長隨非在官之人,而所司皆在官之事。”(徐棟輯:《牧令書》卷四)總之,長隨一方面協助處理日常公務,以減輕長官負擔;另一方面協調衙門各部門各類人員的關系,監督吏胥運作。長官須臾不可離開長隨,他們沒有“上下班”的時間區分,這也是長隨得名由來。
官員任職期間,對內,要依賴長隨對書吏和衙役形成監督牽制;對外,要靠著長隨建立關系網絡。一般來說,長隨是主官信賴之人,主官用長隨監督書吏衙役,執掌官印。處理公事,同時由長隨負責地方的士紳聯絡和官府的迎來送往。尤其重要的是,對于存心腐敗的官員來說,沒有一個中高級官員會親自受賄,長隨的賄賂中介人角色不可缺少。所以,凡懲治腐敗,往往要從長隨身上打開缺口。
長隨的性質,決定了他們對長官的忠誠程度至關重要。盡管作為私人雇員,長官對長隨要比吏胥更信任,但是,也不得不提防著長隨壞了自己的事。而且長隨壞事,要比吏胥對官員的傷害更大。所以,頭腦清醒的主官,同長隨之間的關系是十分微妙的。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記載,長隨的職業神叫作鐘三郎,這位紀大才子判定這個鐘三郎就是“中山狼”的諧音,由此也可看出官員對長隨的一種下意識恐懼。官場經驗極為豐富的汪輝祖,在談到衙門人物品德時,把幕賓排在前列,吏員次于幕賓,而對長隨簡直深惡痛絕,稱其“罔知義理,唯利是圖,倚為腹心,鮮不僨事,而官聲之玷,尤在司間”(《學治臆說》用人不易條)。
明清還有一種十分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票號推薦長隨。票號玩的是錢,官員玩的是權,權與錢的結合點就是長隨。明清的票號,不但向商家放貸,而且向官員放貸。不但向現任官員放貸,而且向候補官員乃至延伸到在讀秀才放貸。這種貸款的收益如何,全靠票號掌柜的眼力。窮秀才沒錢讀書,那些慧眼識英雄的票號掌柜,把寶押在窮秀才的未來發跡上,資助他讀書科考。這種資助不算放貸,當事人如果一輩子出不了頭,資助就打了水漂。至于候補官員以及現任官員的放貸,那是沒有這種風險的,所以就純粹是生意。票號放款給某人捐個官職,幫某個現任官員渡過銀錢難關,這是鐵定有收益的。而收益之一,就是票號有權給當事人推薦個長隨。這樣的長隨,自然就成為官商勾結的關鍵環節。
長隨的自身利益,同吏胥有一致性。他們的收入,主要是同書吏衙役分享規費。有些規費屬于長隨獨占,如門包。另外,長隨常常從所經手的款項中克扣一定比例,替長官收禮時收取“小費”等,這些都有慣例可尋,只要不出格無妨大局。州縣用長隨監督吏胥,而長隨與吏胥勾結往往又是他自己的收入來源。所以,長隨又經常同吏胥伙同起來欺騙長官,這才是長隨可怕的地方。為了防范長隨與吏胥勾結,有的州縣長官甚至規定:長隨不準與吏胥交游、飲酒和賭博,一旦發現哪個長隨同六房書吏及四班衙役稱兄道弟,那肯定立馬讓他走人。即便長隨沒有絲毫不端,除了個別親信家人,一般也只能跟隨長官一任。這固然有官員防范長隨熟悉了官場弊竇而為害幾率增大的因素,也有長隨自己見好就收的因素。有些從一開始就心懷鬼胎的長隨,往往使用虛假身份名字。跟隨的長官任期一滿,馬上到另一地方換個姓名重新開張。正如《閱微草堂筆記》所說:“州縣官長隨,姓名籍貫皆無一定,蓋預防奸贓敗露,使無可蹤跡追捕也。”有些長隨,在跟隨主人的同時,暗中記錄主人的種種隱私,厚道一點的用這個來防身,奸邪一點的用這個來訛詐主人。當然,多數長隨對主人是忠誠的,但長隨出事對官員的傷害太大,所以,官員往往會把長隨的鄙劣作為前鑒。紀昀的《閱微草堂筆記》記錄了許多長隨害人的例子,實際上就是出于這種心理。從明清的官場推斷,大多數長隨還是能得到官員信賴的。否則,長隨與吏胥之間的監控關系就難以運作。
在長隨中,門房和簽押是關鍵崗位。所以,清朝的《學治一得》強調“司聞者須老成壓眾之人”。其他長隨,各有自己的職業規范。長隨自己的抄本《各行事件》(即經驗總結性的工作手冊)稱,“司閽之職,要知世道交接,律例稿案明悉。言語吩咐,不亢不卑。事分緩急,量其輕重,察其大小,須要井井有條。如官府新到任,即細查閱地界遠近、村莊疏密、民情風俗。熟悉于胸中。土役何人妥當,士紳誰興利除弊,訪查明確,以備不時之用。”稿案、錢漕要弄清與戶房刑房打交道的種種關節,負責對外聯絡的執帖更要弄清與長官有關的各種外圍信息。所謂執帖,就是專管“名片”的公關秘書。他們要收集當地的鄉紳情況,了解上司衙門的往來關系,編制出長官必須送禮道賀的“百壽圖”,以備聯絡。掌管印信的簽押,則更是政事中樞,《學治臆說》稱,門房和簽押這兩個位置在長隨中最為重要。“此二處官之聲名系之,身家亦系之”。陋規中的“心紅銀”,本義就是蓋印的用費。至于貼身跟班,主要是打點伺候主官個人,則比門房和簽押的重要性要稍遜一籌,但也得聰明伶俐。“雖在門、印之后,而未曾在辦公之列,亦須練達勤能、聰明機警之人方能勝任。”
袁枚《子不語》中記載,淮寧知縣華雍,派長隨張榮去接待一名欽差。張榮花了上百兩銀子安排公館;結果欽差臨時調整行程沒來,剛好江西巡撫阿思哈被革職拿問路過,張榮就自作主張代表長官接待了阿思哈。事畢回來報銷,華雍罵他多事,師爺指出張榮的做法不過是為報銷找個名目。但錢已經花了,只好認賬。不料,阿思哈重新起復后擔任山西巡撫,華雍恰好又轉任山西。當年阿思哈落難時張榮的接待,成為后來華雍飛黃騰達的契機。
鴉片戰爭后的中英談判中,欽命大臣是伊里布和耆英,而實際談判人員是伊里布的跟班家人張喜。按照史家的說法,張喜在接待應酬、察言觀色方面精明強干,面對懵懂無知的外交事務,他一心想的是為主人爭面子,善于打小算盤,卻把非常重要的領事裁判權拱手相讓。張喜的經歷,一方面反映出長隨的重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舊體制的落伍。
傳統中國的州縣衙門,在長官的統領下,吏胥幕隨四種人物,互相牽制,形成一種十分精細的運作方式。由此而生成的官場習俗和慣例,對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簡單地肯定或者否定,都失之于膚淺。掌握其中的竅道,則能夠對“中國式管理”有更深入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