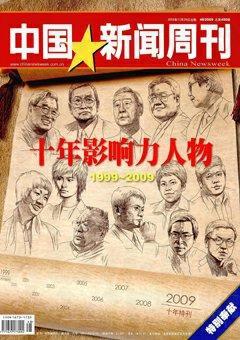茅于軾:經濟學家的“富平”之路
楊涵舒
獲獎理由
作為學者,他堅定地宣講以經濟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作為實踐者,他積極推行農村小額貸款等實驗,為進城農村青年創辦家政培訓學校;作為社會良心,他關注民生,針砭經適房腐敗、18億畝紅線告急等時弊。當下中國,經濟學家因他而產生全新定義。
人物簡介:
茅于軾,1929年1月14日生于南京。1993年從中國社科院退休,與其他四位經濟學家共同創辦天則經濟研究所。現為該所法人代表。
言論:
“作為慈善事業的扶貧,只能有少量熱心人士參與,它成不了正規的金融業。要使小額貸款成為農村金融的一個角色,必須能夠商業化,能夠吸引大批資金進入。”
“扶貧應有利于財富的創造,而不只是財富的轉移。”
——茅于軾
富平,字面上的意思是:財富平均,諧音則是“扶貧”。經濟學家茅于軾選擇了這個一語雙關的詞,來命名自己的第一所職業技術培訓機構——北京富平學校。2002年3月16日凌晨6點,當時74歲高齡的茅于軾和學校工作人員一起,在北京火車站接來了第一批學生。
從最初的“幫助農村資金流轉”,到現在的“幫助農民進城”,這是茅于軾等經濟學家在幫助農村弱勢群體方面,做出的新的嘗試。
富平七年
經過數次搬遷,北京富平學校現落腳北京通州區西集鎮的一片田野間。不大的學校里,教室和宿舍都是平房。學生宿舍很小,每間4張高低鋪,住8個人。學員穿著統一的粉紅色制服,在校園里穿梭。
這所學校提供的是家政服務培訓,只面向農村地區的婦女開放,身體健康、無傳染病、身份清楚就可以申請。茅于軾說,因為她們是“弱勢群體中的弱勢群體”。
學烹飪、熨衣服、給地板打蠟,使用家電……富平學校給她們進行為期1個月的培訓,并負責100%推薦上崗,現在的最低月薪已經漲到800元。
這并不是茅于軾的第一次扶貧嘗試。事實上,開辦富平學校的契機,是在山西開辦小額貸款基金時產生的。富平學校的首批學員里,大部分是當時小額貸款的受惠人,山西臨縣龍水頭村的“老關系”。
“那個地方很窮,但更重要的是缺水。為了省水,當地人不洗臉、不刷牙,干旱時打水要走十幾里地。鎮里有一段時間通過水管供應泉水,很快(水管)就壞了。屬于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方。”2001年,在一次從臨縣回北京的路上,茅于軾和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的首席經濟學家湯敏產生了新的想法:當地自然資源的稀缺造成的貧困深淵,光靠小額貸款不能完全解決。必須幫助農村的剩余勞動力離開農村,去城里找工作。
在兩位經濟學家最初的設想里,家政服務業只是農民進城的第一步,因為這是“門檻最低”的行業。最好以后還能辦“園丁班”“賓館服務員班”等,總之只要能讓農民進城的專業都辦,如果辦學能達到一定規模,也許就可以通過教育融資來形成農民進城的規模化之路。
然而富平學校的培訓效果,并不像想象中的立竿見影。學校除了家政技能培訓外,專門組織了體驗一天“城里人”生活、參加“家政服務員文化節”等活動,茅于軾、吳敬璉等人也參與自辦文娛晚會,幫助學員們適應巨大的環境變化。但接受完培訓的婦女們,仍有一半左右選擇回了老家。
茅于軾對此有些遺憾:“我都鼓勵她們留下。有些人是到了年齡要結婚等家庭的原因,但大多數還是因為不適應。她們很多人是頭一次從農村出來,環境的跨度、文化的跨度都太大了。”馬桶、冰箱、微波爐等城市居民“司空見慣”的家用品,有些學員過去從未見過。
孤獨的樂觀主義者
報名人數不夠的問題,在與一些地方的扶貧部門聯系后得到了解決。但是富平學校的生源也參差不齊。學校培訓最初不向學員直接收取學費,而采取了學費由政府扶貧款支付一半,小額貸款墊付一半、等學員就業3個月后還清的方法。“很多人就抱著反正有人出錢,純粹來北京旅游一趟的想法,玩一圈就回去了。”茅于軾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所以我們后來開始向學員收一點,他們掏了這個錢,就覺得還是要好好把培訓課上完。”談到這個用經濟學中基本的成本和效益來解決了問題的方法,老人現出一個帶點孩子氣的微笑。
富平學校在成立之后,至今已經虧了100萬元,最初出資的5個股東換了3個,只有茅于軾和湯敏還在繼續。以學校為依托的富平家政服務中心去年開始盈利后,又遇上了一場官司。服務中心從學員中推薦的家政服務員在照顧雇主家的孩子時,孩子意外從沙發上跌下,由于腦外傷死亡。這對孩子的家人也好,對剛剛穩定的富平也好,無疑都是一場“無妄之災”。
來自貧困地區的服務員最終回了鄉,富平家政服務中心則被告上法庭。判決要求賠償孩子的家人53萬元。仍然是通過茅于軾的籌集,注冊資本為3萬元的這家小公司償清了這筆費用。
“最初創建的時候,我甚至沒有想到過它會有現在這樣的規模!”茅于軾說,“到現在,我們培訓過的總人數已經超過了17000人!”茅于軾喜歡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算這筆賬:我們5個人出了50萬,如果以一個人的月薪800元計,再加200元左右的食宿開支,1萬多人可創造1億多GDP。這是多合算的投資!
有人評論說:富平學校就如它的創辦者一樣,是個孤獨地尋找出路但始終樂觀的理想主義者。
小額貸款“授人以漁”
與富平學校相比,山西龍水頭村小額貸款基金的開始則更加簡單。“最開始就是我自己掏了幾千塊錢,寄給了雒玉鰲,讓他借給有需要的村民。”茅于軾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雒玉鰲是龍水頭小學的教師,當地少有的高中畢業生。茅于軾在龍水頭小學的學生們給他寫來的希望工程捐助感謝信里,讀到了這個名字。1993年,雒玉鰲被選中成為龍水頭扶貧基金的負責人,茅于軾開始在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中籌集資金。素不相識的兩人通過頻繁的信件來往,搭建起基金貸款的基本框架。
按照最初的規定,基金可以用于三種用途:治病治傷、求學和生產。前兩者可以貸款一年,不收利息;用于買化肥農藥、打工經商等生產用途的貸款卡可以貸6個月,每月付1%的利息。并規定了逾期不還的利息辦法。借款手續也很簡單,取得茅于軾委托的3人管理小組中兩人以上同意,寫借條就可以借錢。治病借款必須出示醫院證明,因上學而貸款者必須由管理人員至少兩人調查核實。超過4000元的借款需要寫申請,經茅于軾批準。
“當地農民的生產或別的需要數額都不大,一般就是千把塊錢,這個數目在銀行辦不了(貸款),到親戚鄰居家借又未必借的到。現在我們可以借給他,而且不需要抵押。”茅于軾解釋:“城市里的家庭只是一個消費單位。但農村家庭卻不同,既是消費單位,又是生產單位。因為從事生產,就有資金的流入流出。春天需要投入資金,買種子和化肥;到秋天因為出售農產品,有資金的流出。其他生產活動也一樣,都有資金的流入流出。如果像現在那樣,要資金的時候借不到錢,生產就會停頓。所以農村金融對農民和農業至關重要。”
中國登記在案的小額貸款機構目前有110家。但由于中國金融政策對個人集資的限制,大多數由國際組織援助并提供資金。與在孟加拉得到的 “鄉村銀行”模式相比,中國農村小額貸款“只貸不存”的現狀被“鄉村銀行”創始人、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尤努斯批評為“砍斷了一條腿”。
龍水頭小額貸款最初只由茅于軾籌集來的資金作為貸款金。2002年,他們開始在當地吸收存款,給存款村民提供6%的月息,資金規模一下擴大了4倍,并成為國內唯一一家能夠既存又貸的小額貸款機構。他們在保持了95%的高還款率同時,也踏入了“非法集資”的灰色地帶。
“必須要有投資,必須是商業化,才能有持續運轉的能力。”茅于軾強調。80歲的他已經從基金的管理中逐漸退出,而今年6月,新的永濟市富平小額貸款有限責任公司以3000萬元資金正式注冊成立,將以合法身份繼續前行。盡管按照目前的規定,小額貸款公司仍然只能經營貸款業務,不能吸收公共存款。
站在風口浪尖上
耄耋之年的茅于軾生活依舊忙碌。從早上6點起床到晚上11點就寢,會議、演講、研究、寫作排滿了日程。對他來說,除了規模的大小之外,小額貸款也好,富平學校也好,和他資助貧困大學生、在臨縣教育扶貧等行為沒有實質的差別。“天則所才是我的工作。”他說。
作為民間機構,天則經濟研究所匯集了盛洪、樊綱、吳敬璉、周其仁等經濟學家,目前的重點研究項目是:中國貿易保護的代價、中國經濟人權及其指數、中國公共治理指數等。近幾年,從“廉租房應該沒有廁所”到“18億畝耕地紅線沒有必要”,茅于軾的觀點動輒被斷章摘句,并在網絡上招來激烈討論和一些人身謾罵。
他對此處之泰然,并仍筆耕不輟。12月,他的博客上最新的一篇文章是《恢復農民對土地財產的所有權》。他說自己歡迎一切關于學術問題的辯論,“我只不過是提出了經濟學上的道理,但是社會到底朝哪里走,是多種因素起作用的結果,也有不少的偶然性。”“我絕不是想給出一個結論,更不希望政府不做認真的研究,就按照我的意見去辦。”
他堅定地支持以經濟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但并非對其缺陷視而不見:“市場經濟有一萬條好處,但是有一條極大的壞處,那就是貧富不均。”而“限制貧富差距就要限制特權,要對富人溫和地剝奪。”這是茅于軾眼中“富”“平”的關鍵。
“現在的社會不公平已經到了一個很嚴重的程度。如果經濟結構調整不過來,不同群體的社會矛盾繼續加大,我對明年的情況很擔心。”天色將晚,在談話的最后,茅于軾第一次露出憂心忡忡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