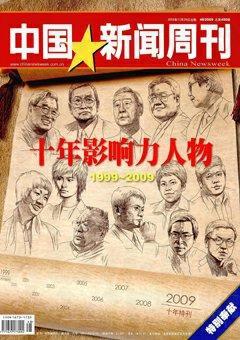江平:布道中國法治
韓 永
他奠定了當代民法的基石,在亂世之后的法治啟蒙中,他堪稱中堅。他的法學造詣和人格魅力獲得廣泛尊重,被視為法學界的良心。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僅兩年有余,卻被稱為“永遠的江校長”。他參與起草并鼎力推動《物權法》的頒行,踐行了民生至上的理念。
江平十年來的主要貢獻,除了參與一些重要的立法外,還在于他矢志做一個法治的“布道者”
由“制”到“治”
江平說,自己以前曾有一種想法,認為制定了法律,有了“法制”,自然就會有“法治”。
他說,這源于自己在改革開放之前對法律虛無主義的深切體會。1957年,剛從蘇聯學成歸國的江平,因響應號召,帶頭寫了一張大字報,在那場“引蛇出洞”的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從此開始了22年的曲折生涯。在這段顛沛流離的漫長歲月里,他常常想一個問題:“中國為什么會變成這樣?”想到的一個答案是,在中國沿襲了幾千年的人治傳統,會輕而易舉地破壞秩序。而解決之道,在于制定法律。
“文革”中,江平原來任教的北京政法學院被解散。他挖空心思從蘇聯帶回來的幾箱法律書籍,也在他徹底對前途感到絕望之際,被當作廢紙賣掉。
1978年,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前身)復課。講課頗受好評的江平開始在政法大學聲譽鵲起,并最終在1988年獲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
從1986年開始,江平參與了很多重要的立法工作。包括《民法通則》《行政訴訟法》《合同法》《國家賠償法》《公司法》《證券法》《票據法》《合伙企業法》《獨資企業法》《信托法》等,并在《行政訴訟法》《合同法》等法律的起草小組中擔綱組長。
2007年10月1日,《物權法》在全民矚目中開始實施。該法的頒布,讓作為這一法律起草小組組長的江平,對中國財產性法律的貢獻尤為凸顯;在中國另一部重要的財產性法律——《合同法》的起草中,他同樣擔任起草小組的組長。有學者評價說,近幾年私權在中國大張旗鼓,如論功行賞,江平居功至偉。
但這些近距離參與立法的經歷,并沒有從根本上提升江平對中國法治的信心。他在由自己和吳敬璉共同創辦的上海法律經濟研究所的一次年會上表示:我們搞法律的人,在改革開放的時候有一個天真的想法,經過20多年的法律虛無主義之后,我們認為只要有了法律,就可以解決國家治理的問題了。但二三十年過去了,我們發現法律有好的也有壞的,有了法律不見得就有法治。
江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很多法律的最終定稿,與專家拿出的最初的草案早已大相徑庭。北大一位行政法學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變化主要有兩塊,一個是部門之間的權力分配,另一個是權力與權利之間的平衡。他說,這兩種變化都不取決于專家,前者取決于相關部門在利益上的搏殺,搏殺的結果往往是破壞了后者的平衡,而民眾的權利往往因此成為犧牲品。“有些法律剛一頒布,其部分條款已是惡法。”
而那些良法可能又會面臨執行的問題。與此相關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在中國,一部法律制定后,并不像國外一樣同時宣布其他與其相沖突的法律或法條無效。而在多法并存的情況下,很多部門還是選擇對自己有利的法律執行。“比如《物權法》通過后,與其相沖突的《拆遷條例》并沒有被宣布無效,而拆遷主管部門又多選擇后者來適用。與《立法法》相沖突的《勞動教養條例》在前者頒布很多年后仍在適用,也是一個例子。”
江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法制”與“法治”巨大落差的背后,是一個理念問題。其中最重要的理念,是憲政理念。而憲政理念的核心,在于民主和自由。
江平說,如果要找一個能貫穿自己一生的東西的話,就是民主和自由。從18歲起,江平就參加了中共地下組織,“一為追求物質上的富強,二為追求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在一次講座的提問環節,有人提及江平在60年前和60年后為了同一個目標而不懈努力時,現場一片唏噓。
放不下的“江湖”
在中國從“法制”走向“法治”的過程中,江平多年來一直在做兩項工作,一個是個案監督,一個是法治布道。其實現的渠道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媒體,一個是講座。
在多起在外界看來非常敏感的事件里,常能看到江平為受害者請命的簽字。業內人士的共識是:這些事件的參與,除了充分的勇氣外,還要有非同尋常的智慧,否則有可能一腳不慎,自己也跟著落水。
在另一些不甚敏感的公共事件上,江平則努力秉持法律的公正邏輯,既不諛上,也不媚下。在重慶“釘子戶”事件中,他因“逆潮流而動”,說吳蘋一家拒絕拆遷的理由“不涉及公共利益”不能成立,遭致網絡圍攻。在許霆的案件上,他也曾有過不順應“民意”的表態。
這種表現,已被業內很多人視為一種重要的個人魅力。他自己對此的解釋是:“做法律的人要公正,但是不是一切都以群眾的感覺作為最高的感受呢?恐怕不行。”
理論上的“布道”,江平則主要通過強調中國法治的兩個特點來實現:一個是中國的法治總的來說是“進兩步,退一步”,另一個是中國法治的實現,要靠官方和民間一起來推動。
江平說,前一個特點,決定了中國法治的推動不能借助于拔苗助長式的過激方式,而應該把握各種政治的底線。張星水與江平在私下里聊天,有時江平會提到,做事要講究方法和策略。與江平常相往來的賀衛方有時也會收到這樣的勸導。
在法治的兩個推動力上,江平認為,隨著網絡的大行其道,民間的力量越來越處于難以被壓制的地位,官民之間的博弈越來越向著有利于民間的方向轉換,這將有利于改變公權力與私權利之間的嚴重傾向前者的狀態。
江平說自己是一個喜歡講臺遠勝于喜歡寫作的人。很多業內人士表示他的講座總是一票難求。張星水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江平的幾乎每一個講座,都會講到法治。
從2008年年底因中風住了兩個月醫院后,江平說自己已經“保命第一”了。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在凌晨兩三點鐘爬起來,看那些讓他心潮澎湃的歐洲足球聯賽。“生了一場大病后,連吶喊的精神都沒了。”他說。
但一說起近期引發熱議的北大5教授上書全國人大,要求修改《拆遷條例》一事,江平的語氣卻突然激越起來,生出一種如由己出的神采意氣。
在中國法律界起伏激蕩半個多世紀后,年近八旬的江平,終究還是放不下這個“江湖”。 ★
人物簡介:
生于1930年的著名法學家江平,最初的理想是做一名新聞記者。這來源于他1948年~1949年就讀于北京燕京大學新聞系的經歷。但在新中國成立不久之后的1951年~1956年,江平被選為新中國第一批赴蘇留學生學習法律,并于1957年回國后在北京政法學院任教。
但回國之后的江平迅速被劃為“右派”。在北京政法學院解散后,江平曾在北京延慶中學教過英語和政治;1978年~1990年,才得以重返北京政法學院(1984年改名為中國政法大學),并先后任民商法教研室主任、副校長、校長。
1990年,江平被免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職務。
1988年~1992年,擔任中國法學會副會長。
1995年至今,任北京仲裁委員會主任,并為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民商法博士生導師。新世紀以來,江平等法學家推動了《物權法》起草等多項法律的基礎性工作。
言論:
“中國的民主建設和政治建設,必然要走曲折的道路。我還是相信,現在中國總的情況是,進兩步退一步。
有人問我,為什么法律規定得不到貫徹實施?我說如果法律都能夠那么容易得到實施,那還要法律工作者干什么?甚至法律都不必規定了。
我們國家不能只有一種聲音,各種不同的聲音交織在一起,才叫和諧,英文上的“交響樂團”這個詞就是這樣來的。”
——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