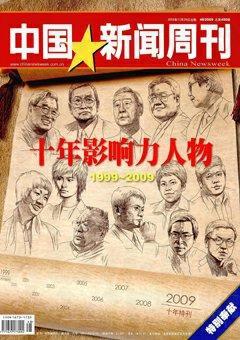李銀河:被“裹挾”進去的斗士
黃 衛
提名理由
性,仍是無法在中國獲得正常身份與屬性的字眼,過度的泛濫與過度的禁忌,同時存在于這個既開放又保守的社會。這也注定了中國最著名性學家李銀河的命運——常有“驚人之語”,每每引發爭議。她致力于在性的領域消除歧視,實現平等,雖艱辛卻未敢懈怠。
人物簡介:
李銀河,中國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會學家,著名作家王小波之妻。1952年生于北京。美國匹茲堡大學社會學博士。1999年被《亞洲周刊》評為中國50位最具影響的人物之一。
言論:
“如果說當代中國人對于經濟、政治、人身安全之類的個人權利已經有了要求,那么在性的領域個人可以擁有哪些權利卻完全沒有概念。在伸張個人的性權利方面,人們還遠遠做不到理直氣壯,反倒是心虛氣短得很。”
——李銀河
2007年2月的一個不眠之夜,李銀河在反復思考關于英雄的問題。最后,她想通了三件事:第一,她不是英雄;第二,她不適合當英雄;第三,這個時代不需要英雄。
促使她陷入這一哲學思考的是剛過去的、極不尋常的2006年。
這一年,從某種程度上,是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李銀河作為一個學者和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分水嶺。此前,她的主要角色是潛心性研究的社會學家,影響所及限于學界和同性戀群體中;2006年,她高調亮相,從同性婚姻合法化提案、南京講座“惹眾怒”事件到采訪收費事件,她一次次成為新聞焦點,對她的關注和非議都爆發式增長。
這一年,她獲得了“英雄”和“燈塔”的無上贊譽,也被評為“2006十大最欠揍人物之一”。
她形容她最崇敬的大學者福柯,到后來每說一句話都是新聞事件。2006年起,她基本上也獲得了這種地位。通常總是這樣的,社會上一個敏感話題出來,媒體就去找她點評,而她的每次點評,都會遭遇聳人聽聞式的解讀。比如,她說“憧憬”性的多元化,報道就說她“憧憬多邊戀”,于是輿論嘩然;她說換妻的提法不對,應該叫換偶,報道就說她提倡換妻又換夫,輿論再次嘩然……
“她有多大壓力?你問她自己吧!但作為她身邊的人,我都感覺到壓力。”跟隨李銀河長達十多年的助理、經紀人鄭宏霞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但李銀河對于壓力的話題并不津津樂道,反而輕描淡寫地說,搞科研相對來說是最寬松的。跟她的主張容易給人造成的“斗士”印象相反,她在采訪中的態度不但是溫和的,而且是溫柔的,平安喜樂的,仿佛已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禪境。
她把自己的角色定位為watchdog(看門狗)。碰到一些不對的事情,又是屬于自己的研究領域的,責任所系,“你總得出來汪汪兩聲吧”?
三提同性婚姻提案
稱贊李銀河是英雄的,是澳大利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67歲的邁克爾?科比,一個公開的同性戀者。他在2006年1月上海舉辦的“性、政策與法”耶魯-復旦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把李銀河比作中國的金賽(美國性學家,其所著《金賽性學報告》引發了西方性解放運動)。
中國最有影響的“同性戀”資訊網站——愛白網的主編江暉也參加了這個研討會。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個“很好玩的老頭”說起李銀河,一口一個“My hero”。但江暉對李銀河的印象是:說話輕聲細語,現場的氣場不夠,“面”了點,遠不如她的文章有力量。
然后兩個月之后的“兩會”期間,李銀河就用這樣的輕聲細語,提出了擲地有聲的《關于同性婚姻的提案》。
這是她第三次提出這一提案了。前兩次,都石沉大海。
很多人誤會,以為李銀河是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可以直接提交提案。其實,她什么都不是,只能四處找朋友幫忙。
第一次是2001年“兩會”期間,她委托一名人大代表提交“同性婚姻”議案。但因找不到30名代表附議,只能作為“建議”提交。
第二次是在2004年。她這次瞄準的是政協,因為政協的提案一個人就可以提交。社科院有不少政協委員,但都以“不是自己的研究領域”“不了解”為由拒絕了她。最后她總算找到了一位愿意幫忙的朋友,對方要求她不透露姓名。
其實,李銀河自己都記不清她到底努力過多少次了。碰壁是家常便飯,有人肯幫忙也都會要求保密,提交沒提交不知道,提交了當然也不會有任何下文。
第三次,2006年“兩會”,她的聲音終于被聽到了,而且,振聾發聵。媒體蜂擁而至。全國政協新聞發言人吳建民在接受采訪時表態,說同性婚姻的思想太過超前。
其實連江暉這個“同性戀”運動的組織者都認為,當下最緊迫的是反歧視,同性婚姻立法的時機遠未成熟。在他看來,李銀河提出同性婚姻提案,更多的是一種策略考慮。
對此,李銀河自己有個“平行四邊形”理論。即,有些人往左走,有些人往右走,最后得到的將是一個平行四邊形,社會會走向二者中間的方向。為了平衡強大的右翼保守力量,她必須堅持向左走。
從次年開始,“兩會”前夕的2月份成為中國“同性婚姻倡導月”,江暉他們每年組織“同志”中的志愿者上街宣傳造勢,呼應李銀河可能采取的提案行動。而猜測她當年是否提出提案,也成為“兩會”期間的保留熱點話題。
喊出“皇帝沒穿衣服”之后
李銀河很快就品嘗到“登高一呼”的滋味了:不是應者云集,是罵者云集。
開始,反同性戀者跑到她的博客上,盡情傾瀉著罵街式的語言暴力。她哪里見過這種陣勢,只好把博客評論功能一關了之。
2006年7月的“南京講座”事件后,罵聲則是鋪天蓋地而來,關也關不掉。
“七夕”前夕,李銀河應邀到南京做了一個關于愛情的講座。李銀河自己的感覺是,講座反響很好,“只有個別老年人提出異議,別的聽眾還‘噓他”。但《金陵晚報》的標題卻是:“李銀河憧憬‘多邊戀,前衛性觀念南京惹眾怒”。李銀河說:“我是用過‘憧憬這個詞。我希望能有一個多元性文化的社會。我不是憧憬‘多邊戀,而是憧憬多元化。”
這篇報道被各大網站爭相轉載,甚囂塵上。
這些,她還能頂住壓力,但來自行政系統的壓力,她卻頂不住了。
領導找她談話之前的那個月,她接受了多家媒體的采訪:10月9日“鏘鏘三人行”談性問題,10月17日視頻聊同性戀,10月19日“一虎一席談”聊“為二奶維權”,10月24日網聊“換偶”問題……反復闡發在“自愿、私密和不涉及未成年人”三原則下,成年人有自由選擇權的觀點。
社科院領導找她談話了,主題是“研究無禁區,宣傳有紀律”。領導勸她要考慮中國國情,那就是:現階段還是溫飽階段,性還是一個奢侈品。
李銀河不服氣,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算宣傳嗎?但她內心非常掙扎。她也理解領導的難處,外界會把她的個人觀點看做社科院的觀點。
她做出決定:第一,盡可能少接受記者采訪。第二,盡可能少發表與性有關的言論。“雖然我覺得犬儒主義不好,不對,也許只能如此了。”
也就是在這時候,她看清楚自己,不適合當英雄,因為缺少戰斗性和獻身精神。
罵她的人,也是因她受益的人
但李銀河知道,她是不可能閉嘴的。雖然,她只是個被“裹挾進去的戰士”,但,既然被“裹挾”進去了,戰斗就只能是她的宿命。
把她“裹挾”進去的,是她選擇的研究領域。選擇這一領域,既有必然,也有偶然。
必然是:從她的教育背景來說,她是美國匹茲堡大學的社會學博士,而性是社會學的經典研究領域之一;從她的性格來說,那些年人們越是談性色變,她越想將它看個究竟。在她看來,“搞性的研究有點像當年革命者搞地下工作,有一點冒險犯難的挑戰感覺;有一點越軌犯規的淘氣感覺;外加一點先鋒前衛的叛逆感覺。”
偶然是:她剛回國時做了10個社會學課題,在做“單身”這個課題時,碰到一個因同性戀而選擇單身的男士。這給她提供了寶貴線索,使她得以通過他接觸到其他同性戀者。就這樣“滾雪球”,李銀河完成了開創性的同性戀研究專著:《他們的世界——中國男同性戀群落透視》,在香港出版。
1998年,這本書經過增補,更名為《同性戀亞文化》,在中國大陸出版,引起巨大轟動。在黑暗中苦苦摸索的大陸“同志”將之視為“圣經”。李銀河也因此在1999年被《亞洲周刊》評為中國50位最具影響的人物之一。
愛白北京圖書室收藏了這本書的香港和大陸兩種版本,還有《虐戀亞文化》(1998)、《酷兒理論》(2000)和《福柯與性》(2001)等李銀河的代表作。據江暉介紹,借的人并不多。因為李銀河的書大家都有,教育程度較高的“同志”家中幾乎人手一本。
2009年12月,重新收錄了這些經典舊作的《李銀河文集》出版,其中還包括兩部新作:《后村的女人們》和《社會學精要》。李銀河下一步的計劃是,寫作新中國60年性史。
當被問到是否考慮過從政,李銀河說,現在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已成了一種榮譽。“爭榮譽我不樂意。但如果是為利益群體代言,我應該出來做這事。”
不過在江暉看來,李銀河并不是最適合代表這個群體的人。“需要有更懂得語言技巧的,不能被人逼問兩句就臉紅的。”
但是,他非常欽佩李銀河孤軍奮戰的勇氣。“一般的學者做不到,只有那種不囿于學術圈子、時刻關注民生和社會問題的公共知識分子才能做到。”
他認為,李銀河對性少數群體最重要的貢獻,并不在于有什么理論創新,或是提出了同性婚姻的提案,而是,她為這個群體爭取了話語權。
但,李銀河的貢獻并不止于性少數群體。江暉說:“很多人并不理解,她是在幫每個人爭取自己的權利空間。很多人只看到性,想到性本身以及那些性的畫面,于是就覺得骯臟,然后就對李銀河潑臟水。而那些罵她的人,其實,也是因她受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