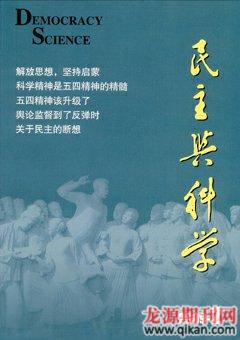思想創意的優先權
孫慕天
在自然科學中,長期存在優先權(priority)之爭。科學社會學家齊曼(J.M.Ziman)說:“關于什么人、在什么時候作出什么發現的問題,經常產生激烈的爭論。按照慣例,做出某項特殊發現的優先權的權利,屬于首次發表論文報告該項發現的作者們。”
早在17世紀,伽利略在《試金者》一文中就痛斥了四個試圖想要與他爭奪優先權的人:一個是關于望遠鏡的發明,第二個是關于太陽黑子的發現,第三個是關于木星衛星美第奇的發現。后者是一個叫馬里于斯(Simon Marius)的人,宣稱是他而不是伽利略首先發現了美第奇衛星,而使用的手段卻極不光彩:他在公布這一發現的刊物上注明的日期是根據儒略歷,而不是格里戈里歷,這就使他的發現趕在了伽利略的前面。伽利略憤怒地斥責說:“他使用了一種狡詐的方法企圖確立他的優先權。”而牛頓則更深地卷入了優先權之爭。首先是關于一些光學和天文儀器的發明,其次關于平方反比定律的發現,胡克和牛頓發生優先權的爭執,胡克甚至聲稱牛頓的一系列發現全都是由他發起的,以致后來牛頓不得不在自己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中插入一段聲明,指出胡克也是平方反比定律的發現者之一。
關于牛頓和萊布尼茲誰最先創立微積分的爭論,是優先權之爭最典型的案例。牛頓創立微積分是在1665年,他在解決加速運動的瞬時速度問題時,發明了流數法,這有他1665年11月13日的筆記為證。1669年他在致巴羅的信中闡述了這一方法。而1672年2月10日,他曾在致科林斯的信中明確提到他發現的這一新方法及其在方程論中的應用,這封信后來成為牛頓對微積分學原創性貢獻的有力佐證。1671年他寫了《流數方法》的手稿,詳盡論述了關于流數的思想。萊布尼茲在1674年在研究用無窮級數求曲邊形面積時,考察了求構成曲邊形的元素之和的方法,進而創立了微積分學。他的筆記和手稿表明,在1675到1676年間,他開始嘗試使用獨特的微分和積分的記法。萊布尼茲曾于1673年訪問倫敦,結識了皇家學會秘書奧爾登貝格(Henry Oldenburg),1677年他寫信給奧爾登貝格,說明了求曲線的切線的方法及相當于求積分的逆問題的解法。1684年他在一篇文章中系統地闡述了他所制定的微分學原理,提出微分學的關鍵是一個算式所依賴的變量的無窮小增量,稱之為“差分”(difference),并用字母d來表示,寫作dx、dy。后來他又論述了作為逆運算的積分學原理,并用其本質是求一個量的相繼元素之和(summa),因此用一個拉長的字母s- 來表示。牛頓與奧爾登貝格稔熟,很可能通過后者了解到萊布尼茲的工作。1676年,牛頓寫信給奧爾登貝格詢問萊布尼茲的情況并提到自己的流數法,翌年萊布尼茲致信奧爾登貝格回答了牛頓的詢問,介紹了自己的方法。但問題是,牛頓《流數方法》的概略盡管于1703年以《求曲邊形面積》為題作為《光學》一書的附錄予以披露,但全書遲至死后9年(1736年)才發表。這就造成了一種印象,即牛頓似乎是在萊布尼茲之后提出流數法的,況且微積分的正式記法是由萊布尼茲給出的。1705年,萊布尼茲在一篇對牛頓《光學》的匿名評論中,說牛頓的流數是對萊布尼茲差分的改頭換面。而1708年牛津物理學講師薩維尼則反唇相譏指斥萊布尼茲剽竊了牛頓,萊布尼茲遂就此提出上訴。1712年英國皇家學會為此任命了一個委員會進行審理,發表了支持牛頓優先權的報告,但沒有對萊布尼茲的貢獻作出評價,卻認為萊布尼茲在1676年已看到了關于牛頓流數法的文件,并受到了啟發。萊布尼茲對此向皇家學會提出抗訴,該會在一次有外國大使參加的會上就此進行審議,根據與會者的建議,牛頓與萊布尼茲進行私下磋商,但并未得出結論。
今天看來,一方面,牛頓在其開始于17世紀60年代的力學研究中,已經開始創立并使用了微積分學的方法。他在1687年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中,明確提出:“量消失時的最后比實際上不是最后量的比,而是無限減少的這些量的比所趨近的極限。”這是關于導數的最早的科學定義,并制定了流數(fluxiones)這一專門詞匯,給出了x、y上加一點的記法。同時,正是牛頓把這以數學方法應用于實證科學研究,開啟了使用數學物理方程的先河。這確實略早于萊布尼茲。不過,萊布尼茲雖然遲至十多年后才提出自己的微積分理論,但看來確實是獨立提出的。19世紀中葉英國數學家莫干對這樁公案做了詳盡的考辨,證明萊布尼茲沒有看到過牛頓關于流數法的原始文獻。牛頓1676年的信在談到流數法時有意使用了字謎式的隱語,所以萊布尼茲不可能從中取巧。更重要的是,萊布尼茲創立了微積分記法,由于該記法被克雷格用于1685年出版的一本書中,而這一記法因其簡潔、方便和完善而被廣泛采用,對微積分學的發展和傳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并一直使用到現在。其實,牛頓早在原理第一版中,已經肯定了萊布尼茲的工作,說:“十年前在我和最杰出的幾何學家萊布尼茲的通信中,我表明我已知道確定極大值和極小值的方法、作切線的方法以及類似的方法,但我在交換的信件中隱瞞了這方法……這位最卓越的人在回信中寫到,他也發現了一種同樣的方法。他并訴述了他的方法,它與我的方法幾乎沒有什么不同,除了他的措詞和符號而外。”從這段曲折復雜的歷史中,可以看出,公正地評價一個科學家的真正貢獻,正確地確定發現的優先權,有時常常是一件十分嚴肅的事情,決不應草率行事。
科學上關于優先權爭吵絕不是無謂之爭。黑格爾認為,真理是個過程,自然科學知識正是從相對真理走向絕對真理的過程。從本質上說,這一認識是對客觀自然對象及其規律的正確反映,盡管科學理論的更迭存在著范式的轉換,但卻總會構成一個逐步提升的認識階梯,所以牛頓才說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最先做出發現的科學家理所當然地占據前面的一級階梯,成為那一特定階段科學所達到的高度的界標,肯定這一點是對歷史的尊重,也體現了學術公平原則,從而保護了學者的創造積極性和科學生產力。優先權體現了科學的求真和向善兩種本質要求的統一,誰最先作出了發現和發明,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尊重這一事實就是捍衛真理。同時,為了認識前所未知的自然規律,科學家必須致力于原創性的探索,不能容忍任何投機取巧的違規伎倆,遵守這一原則就是維護科學道德。甚至可以說,是否尊重科學發現和發明的優先權是衡量一個科學家學術品格的試金石。既然知道了別人在同一課題上已經得出了正確結論,如果秉持求真的意愿,所應做的就只是對該成果的改善和推進,再重復同樣的結論就完全是多余的了。問題是,由于優先權問題與科學的社會建制有關,涉及到與知識產權相聯系的財富、權力、榮譽的獲取,結果如科學社會學家默頓所說,優先權問題已經“在很大程度上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的科學價值觀和規范的結果”,于是在個人利益的驅動下,就出現了妄圖竊取優先權的卑劣行徑。在評論默頓關于優先權的研究時,斯廷奇科布(Arthur Stinchcombe)歷數了科學界為爭奪優先權而發生的丑聞:“喜愛爭論、堅持己見的要求、怕別人占先而保密、只報告支持某一假說的數據、毫無根據地指控別人剽竊、甚至偶爾偷竊別人的思想以及在極少數情況下編造數據——所有這些行為,在科學史上都出現過。”
優先權問題的權威研究者默頓明確指出,圍繞優先權的爭論“社會科學中的情況幾乎一模一樣”。斯科特在《亞當·斯密:學者和教授》中,列舉了亞當·斯密的朋友弗格森和羅伯遜都剽竊過他的見解,而前者為了“確定優先權”,被迫公開發表演講,“把他的新思想列了一個相當長的清單”。另一個典型案例是,圣西門指責歷史學家基佐盜用他在《組織者》一書中的觀點,嘲諷說:“公眾和我本人都極希望他像以往對待我首創的思想那樣,盡可能充分盜用它的內容。”就連馬克思也不例外,他曾經義憤填膺地斥責海德曼是自己思想的明目張膽的盜賊,而且對馬爾薩斯和巴斯夏剽竊前人思想的行為嗤之以鼻。
優先權的核心恰恰是新思想、新觀念的最初創意,而且正因這種創意是無形的,其最本質東西只是一種思想閃光或精神火花,它雖是一切創造的源頭,是特別寶貴的,但一旦原創者發表了這些想法,它們就特別容易被有心人借用,而當這些創意被當作借用者的原創時,實際上已經是對真正創造者優先權的侵犯。然而,這種初始創意卻尚未體系化、賦形化,也未納入社會學術體制,因之對它們的優先權保護是不可能規范化的,基本上只能憑借道德約束,訴求于應用這些創意的人自己的學術良心。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麥克斯韋電磁場方程的發現。麥克斯韋關于位移電流和交變電磁場的思想,追本溯源來自對超距作用的懷疑,這來自堅持電磁作用要通過“中間物質的中介而發生”的信念,并且認為這種作用的傳遞是沿著法拉第的力線逐點連續發生的。麥克斯韋明確指出,他的這一信念是受18世紀意大利哲學家波斯科維奇(Roger Boscovich)的啟發:“波斯科維奇提出的理論是,物質是數學點的集合,每一個點都按照一定規律而對另一個點施以引力或者斥力。”須知,波斯科維奇1758年發表《存在于自然中的力還原為單一法則的自然哲學理論》一書,提出力點論;而麥克斯韋在《論物理學的力線》一文中首次提出交變電磁場的惰輪模型,時間是1861年。兩者相隔103年,而波斯科維奇并不是聲名顯赫之輩,他一生顛沛流離,最后客死他鄉,麥克斯韋祖述這樣一個塵封于歷史記憶中的過氣人物,絕對沒有攀附之嫌,而是對前賢的由衷敬佩和對優先權的自覺尊重。
哲學思想是一種領悟,其核心觀念的產生是靈光一閃,形態雖極簡約,義理卻是宇宙和人生的真諦,其啟發價值是無可估量的。哲學觀念的作用猶如傳說中的哲人之石,所謂點石成金,它是撬動思想巉巖的智慧杠桿。但唯其蘊藉不彰,漫汗無跡,也極易被人忽略。盡人皆知計算機改變了人類歷史,但是計算機的發明與哲學思想的關系卻幾乎淹沒無聞。圖靈被計算機的現代電腦的主要設計者馮·諾伊曼譽為“計算機之父”,他指出“計算機的基本概念屬于圖靈”。就在1939年,圖靈與哲學家維特根施坦討論數理邏輯中的矛盾。在《邏輯哲學論》中,維特根施坦認為矛盾是毫無意義的,并相信有一種完美的理想語言,可以避免任何歧義;圖靈不同意這一觀點,二人發生了爭執。事實上,維特根施坦當時也正在修正他早期的觀點,認為公眾采用和發展的是包含內部矛盾的語言,亦即日常語言。這場討論啟發了圖靈,使他深入把握了計算機語言的性質。圖靈機是一種不考慮硬件形態的計算機邏輯結構,圖靈甚至提出一種“萬能圖靈機”,用來模擬任何一臺圖靈機的工作,從而首創了通用計算機的原始模型。這里明顯地有維特根施坦理想語言論的影子。英國學者愛德蒙茲和艾迪諾在談到這件軼事時說:“在圖靈思考原始計算機波姆貝(Bombe)的邏輯設計時,他們爭執的這個記憶也許起了作用”。雪泥鴻爪,雁過無痕,哲學思想的作用一向如此,正是由于哲學思想的這一特殊性質,與科學成就不同,哲學發現的優先權問題甚至未見有人提出過,哲學思想首創者的權利往往輕易被輕忽,被侵凌,被踐踏。
時代久遠,典籍佚失,一些重要哲學觀點的原創者隱沒在歷史的深處,后人不加深究,常以自己的見解充作前人未發之覆;等而下之者,則專以“盜墓”為業,以為無法起古人于地下,與之爭奪優先權,從而可以遮盡天下人耳目。其實,哲學上的原創者和科學大師們一樣,他們的開創性功績并不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我們既然不能掠美于時賢,也同樣不能掠美于古人。在這一點上,哲學和科學一樣,也有累積效應,哲學家同樣也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現代西方分析哲學、哲學邏輯和語言哲學真正的創始人是弗雷格。他于1879年發表《概念文字》一書,1884年出版《算術基礎》,并在19世紀90年代發表《論概念和對象》、《論意義和意謂》等開創性的論文。弗雷格第一個提出了意義和指稱的區別,奠定了構建形式語言邏輯演算系統的基礎,是羅素、卡爾納普等人當之無愧的先驅。他長期在耶拿大學執教,但他所使用的符號和形式演算方法過于艱深,很少有人理解。他的課堂常常只有三個學生,其中一個就是卡爾納普,校方對他的課評價一直不高。弗雷格的思想太超前了,而他又極度低調,從來不會炒作自己,相反,作為一個嚴謹的思想家,最高追求是所構建的理論體系的完美。1902年,在他的著作《算數的基本法則》第2卷即將付印時,他收到了羅素的一封來信,羅素在高度評價他的工作的同時,也指出他的邏輯體系導致矛盾的可能性,這就是著名的“羅素悖論”。這封信強烈地震撼了弗雷格,他說:“在工作之后發現那大廈的基礎已經動搖,對于一個科學工作者來說,沒有比這更為不幸的了。”他隨即放棄了原來準備出版的《算數的基本法則》第3卷的計劃。弗雷格始終沒有從這一打擊中恢復過來,在郁郁寡歡中度過了生命的最后二十余年。這以后的弗雷格差不多已經被世人遺忘了。直到1973年,在弗雷格去世四十八年后,才由達米特在其巨著《弗雷格:語言哲學》中,全面肯定了他在現代哲學中的開創作用和現代語言哲學奠基者的地位。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主流話語霸權的遮蔽和掌控。經濟、科技、軍事霸權往往帶來文化霸權,當今世界的西方中心主義和英語文化的主流化,把其他民族國家的文化統統邊緣化了。于是在哲學領域就出現了一種風氣,似乎只有西方特別是英語國家的哲學才可以登上哲學廟堂,其他國家的哲學文獻都不屑一顧。即使非西方國家的學者作出了獨創性的發現,也完全可以視若無睹。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對待蘇聯哲學研究的態度。雖然在長達七十年間蘇聯學者在哲學上走了許多彎路,但在許多領域和一些重大的哲學主題上,蘇聯學者也做出了超越西方學者的原創性成果。奇怪的是,就連我國的許多哲學研究者也對這些成果視若無睹。其實,被國人當作新發現公諸于世的一些觀點,人家早就做了深入的討論,并且遠遠超出了他們的學術水平。在這些人的眼里,對英美學者的成就必須尊重,而蘇聯學者的成果似乎不屬于“地球人”,可以棄之如敝屣,即使那些成果擺在那里,仍然可以繼續大搞重復勞動,并面無愧色地宣布自己擁有發現的優先權。
哲學研究的另一個特殊性是與政治關系密切。在威權主義時代,由于統治的意識形態是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于是哲學上的思想創造就被看成是政治領袖的專利,一般學者只配充當領袖思想的注釋者、解讀者和宣傳者,覬覦哲學創造則被視為狂妄之徒,乃至反革命野心家。事實上縱觀哲學史,對哲學作出偉大貢獻的人卻并非政治領袖,而是純粹的學者。兩千多年的哲學史上,在有獨創性哲學思想的哲學家中,只有古羅馬的奧勒留是一位帝王。拿康德說,他的一生真是平凡得很,不過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學究而已,甚至可以說有一點“冬烘”。康德研究者奧特弗里德·赫費說:“關于康德很難寫出一部扣人心弦的傳記;他的外在生活過得平穩單調。我們找不到一個他讓同時代人十分激動的事件,也沒有一次能夠抓住后人好奇心的冒險行動。康德不像盧梭過著一種不穩定的漫游生活;也不像萊布尼茲與他同時代的所有大人物都有通訊往來;不同于柏拉圖和霍布斯,他從未參與政治活動;不同于謝林,他從未卷入‘女人故事。他的生活作風中也沒有任何越軌的行為;從不著引人注目的服裝和發型,也從未有過狂飆突進時期人們所喜愛的慷慨激昂的姿態。”雖然如此,康德卻“屬于西方最偉大的思想家,他對近代哲學的影響無人可比”。
在我們的時代,難道不會再出現康德式的思想家嗎?信息時代的符碼效應,使人們的眼球紛紛轉向名人和明星;學者不甘寂寞,也全身心的浮躁起來,潛心治學的人越來越少了,動輒鴻篇巨制,著作等身,自封“大師”“泰斗”。近年來,國內標榜學術評價科學化的做法大行其時,并儼然成為政府行為,于是在定量化的指標體系規范下,以多為勝成為不成文法,在一陣高過一陣的量化喧囂中,有誰還會關心什么人最初提出了什么創意呢?上世紀前半葉英國牛津大學奧斯汀被評價為“偉大而又富有獨創性的哲學天才”。正是奧斯汀在哲學史上第一次提出言語行為的概念,斯臺格繆勒說:“對于那些2500年來以任何形式從事語言研究的來說,這真是一件丑事,而且是一件帶有恥辱性的丑事,即他們在奧斯汀之前這么長的時間內,沒有作出奧斯汀的發現——就是借助語言表達我們可以履行不同種類的行為。特別是在我們時代哲學轉向語言研究已經過去了數十年,直到一位哲學家作出了有語言行為的發現。”但是,用時下流行的標準看,奧斯汀實在不能算“大師”和“泰斗”,因為他生前僅僅發表了區區七篇論文,沒有任何專著,他的大量創造性的思想是來自講演和交談,所謂“述而不作”。人們重視的是他的原創性的思想,盡管這些思想甚至并沒有用文字固定下來,但是奧斯汀擁有發現它們的優先權,卻是無可置疑的。
看來,問題僅僅在于,從老子和泰利士諸位老先生以來,你究竟說了幾句從來沒有人說過的話?
(作者單位:哈爾濱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