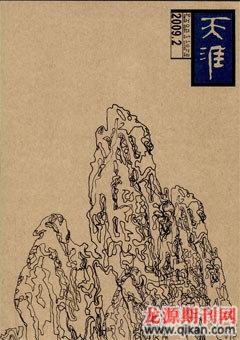低調
張執浩
一
很多寫作者面對既有的文學傳統都經歷過這樣兩個不同的階段:反對與聲援。前者往往視自己為“孤兒”,視自己的寫作是對文學傳統的背叛,即所謂“如果我寫的是詩歌(小說),那么你們的則不是”,云云;而后者往往視自己為“長子”,視自己的寫作為對文學傳統的全面繼承,于是乎,就在某種當仁不讓的情感力量的驅使下,將自我毫無保留地納入到了聲援傳統的隊伍里。從“孤兒”到“長子”,看似兩張面孔迥異的“身份證”,其實只是寫作者不同時期的“工作證”,因為并不存在與生俱來的文學孤兒,也不存在天經地義的文學長子,兩者之間的身份轉換其實就在一念之間;而此“念”的關鍵就在于我們該怎樣去解讀傳統。傳統的內核究竟在哪里?應該說,這早已不是一個新鮮話題,但它仍然是困擾著一代一代寫作者的問題,因此才會常談常新。
艾·巴·辛格在與理查德·伯金的長篇訪談中,曾經猛烈抨擊過一些作家在從事著“歪曲現實”的寫作,他說,“我感到當今的文學有一種歪曲事情本來面目的趨向,它不是為了創作偉大的藝術品,而是通過歪曲去求‘新穎。歪曲和新穎已經變成了同義語,然而事實上兩者相差十萬八千里。”他還指名道姓地指出品脫“就在這么干,他只會歪曲現實……”辛格是我極喜愛和信任的作家,在閱讀這篇談話時我比照了一下自己的寫作,發現也有過一段熱衷于“歪曲”的經歷,不獨我,包括我們這一代所謂的“新生代作家”都有過類似的經歷,且以此為樂。但我不以為這是什么不光彩的經歷。設若沒有當初的“反對”,我現在的“聲援”還會如此堅定么?我想不會。只有當寫作不再是一種姿態,不再需要某種“身份”來給自我定位時,或者說,當我們毋須再借助任何策略、手段而直接面對文學本體時,當我們真正是赤手空拳的時候,寫作的意義和文學的力量才終于體現出來。
接下來的問題是,是否有一種永遠無法被歪曲的“現實”存在呢?
對這個問題的追問貫穿了我近幾年來的寫作與生活。為了找到一個相對可靠的答案,我重新閱讀了一遍那些存活在自己的心目中的大師們的作品,我相信,答案是現存的,現在我不過是用在一顆平實的心靈來感受它們罷了。這些無法歪曲的現實應該是我們人性里面公共的那部分情感,比如說恐懼感、嫉妒心,當然還有憐憫,向善之心,等等。上帝給予我們每個人大致相若的肉體,同時也在我們每一具身體里埋下了這樣一些精神的“種子”。但是由于土壤有別,這些種子在我們身體里將遭遇不同的命運,有的會生根發芽,開花結果,有的則無端夭折;有的盡管長勢茂盛,卻因為處在僻靜的角落,而被忽視;還有一種情況是,某類種子可能會一直沉埋在某個地方,耐心地等候著陽光和雨水,等待你去發現……種子們的不同境遇造成了寫作者之間的千差萬別。盡管如此,我仍然相信上帝是公平的,而不公平的恰恰是我們自己,是我們對待體內的種子的態度出了偏差,存在著厚此薄彼的行為。辛格曾經寫過一篇膾炙人口的小說《傻瓜吉姆佩爾》,塑造了一個被謊言包圍的小人物充滿戲劇性的一生,最后,作者借用老年吉姆佩爾之口說出了他本人對命運的真實發現,他寫道:“……我越來越懂得實際上是沒有謊言的。現實中沒有的事情晚上會在夢中遇見。這個人遇到的事,也許另一個人不會遇到;今天不遇到,也許明天遇到;如果來年不遇到,也許過了一個世紀會遇到。”嗚呼,連“謊言”這粒被我們視為邪惡的種子尚且這般生機盎然,何況其他的呢?我想,這就是文學的現實,它源于生活,源自于我們的血肉之軀,從來不會消失,也難以因被“歪曲”而被抹殺掉。我們這些寫作者的工作就是要不斷清理日漸雜蕪的內心世界,發現這些種子的下落,盡可能準確地預見它們的長勢、趨向和結果。
事實上,對于一個寫作者而言,真正復雜的工作還在于,當這些種子在不同的時代發生變異后,你是否還有能力去清晰地把握它們。譬如,當愛與惡交織在一起時,當一個人被這兩種完全不同卻又幾乎對等的力量同時撕扯、扭曲時,你還能否辨認出他(她)的出處呢?譬如,當道德的底線被公眾的趣味不斷僭越,底線不斷下滑時,我們又該如何作出相應的反應。而且既不隨波逐流,又不是隔岸觀火?我們的知識(文化)大都來自于已有的闡釋系統,而時代的風尚總是以求變求新為手段,因此,我們每一次與新事物的遭遇就構成了一次挑戰。為了安全起見,更多的寫作者會選擇那種貌似永遠正確的寫作,即,返回到闡釋系統之中,以“長子”的身份占據有利地形。可是,仍然會有另外一些人勇敢地選擇了被貶謫的命運,他將自我放逐進時代的洪流中,以一種感同身受的方式來理解這個時代,來觀察上帝撒下的那些種子在這個時代里結出的奇花異葩。我想,一個真正優秀的寫作者就應該是這樣一類人:他抱定了玉石俱焚的勇氣和信念,也理所當然地承擔起了這樣一種新的傳統,一種真正“在場”的傳統。
二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詩人越多,詩歌愈少。這樣的判斷近乎悖論,卻正好印證了當下詩界的現實。由于龐大的詩歌數量的存在,導致了閱讀的模糊;又因為清晰之必需,所以數量會進一步繁殖,以擺脫身陷模糊之困境……以此類推,惡性循環,我們最終得到的報應是,真正的閱讀被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瀏覽,是對速度的推崇,對量的無止境的渴求。于是,遮蔽不可避免。當我們看不見詩歌的時候,詩人為了反抗遮蔽,為了證明“我在”,便會以某種極端的面貌出場。
而詩歌恰恰是一種指向“少”的藝術,一首詩甚至可以簡化為一個詞。詩人的生命力并不在于他“說出”了多少,而在于他“發現”了什么。這就需要我們在更多的時候放下筆來,放棄“寫”,而專注于“看”。一棵樹矗立在窗前,也許終其一生它都不會被挪走,但它沒有哪一天是靜態的,它與這個世界構成了某種關聯。這是“看”的結果,是“發現”。寫作最終要達到的就是這樣的效果:從“發現”出發,找出事物之間的相互關聯,然后找到那個最適應安妥自我心靈的位置。
但是,在這樣一個時代終究是沒有幾個人愿意做減法的,更多的寫作者迷信“多”,在他們看來,“多”意味著創造力,意味著強大。“泥沙俱下”固然可以呈現出一種生命狀態,倘若你對浩蕩的江流有所認識,你就會發現,每一段江水其實都在做減法,都善于舍棄。
減掉心中的貪欲、牢騷,抱怨和忿懣,才能變得輕盈起來。我從來不相信這世上存在所謂“生不逢時”的人,如同我相信任何時代都可以塑造深刻、偉大這樣一些命題一樣,我更信任那種敢于“把牢底坐穿”的人,他們是日常生活中的烈士,是我們最終能夠將平淡無奇的生活過得熱氣騰騰的原動力。
三
將一首詩寫得像詩,或將一首詩寫得不像詩,這兩種說法都經不住推敲,如同說一個人長得像人,或長得不像人一樣。我們正被某種模棱兩可的洪流裹挾著進入一段彎道,在
這里,方位莫辨,標準失衡。“像”,帶來曖昧、混沌,遠不如“是”來的痛快淋漓。但為什么仍然有那么多似是而非的東西盛行和暢銷呢?回答類似的疑惑并不難,難的是任何答案都顯得答非所問,至少是無濟于事,模糊的將繼續模糊,曖昧也將繼續如薄霧一般蒙罩在所有事物的表面。這無疑是一個審美出了狀況的時代,其鮮明的表征之一,就是美被懸置,真被懷疑,善必須通過某種極端的方式才能得以體現。具體在寫作上,“好好說話”居然也變成了一樁極具挑戰性的事情。臟話、鬼話、神話、胡話、夢話、笑話……不絕于耳,就是很難聽到一句人話。似乎每個寫作者都必須先有了一副扮相才敢于走到人前:似乎做一個尋常人真的是那么艱難。“語不驚人死不休”。于是,詩人們殫精竭慮,茶飯不思,為得一言而愁腸千結。我現在越來越見不得那種整天作若有所思狀的寫作者了,因為我知道寫作其實是一樁再也簡單不過的事情,撇開其特殊的技藝而言,寫作僅僅是把你想說的話從內心深處搬遷到紙面上罷了,而紙張需要通過生活來賺取,還需要通過生活來保障你有寫的力氣和一直寫下去的能力。
“我靠敗筆為生,居然也會樂此不疲。”這是我在一首詩中的坦言。在我看來,一個承受不起“敗筆”的詩人肯定照樣承擔不起“經典”。詩人工作的危險性和殘酷性就在于,他必須花數倍于其他人的努力,才能勉強進入“不朽”的序列之中,甚至根本就與“不朽”和“經典”無緣。他一直在“說”,卻永遠沒有聽眾,或者聽眾近在咫尺,可人家根本就不屑于聽。因此,做一個詩人就或多或少地帶有絕戀或單相思的意味,他從來就無法保證自己能否獲得繆斯女神的垂青,但是他又得必須時刻保持著懷春者的情懷。在這種境況下,“敗筆”對寫作者來說,其實是一種情緒上的舒緩,而非移情。
四
我的詩歌寫作也許過早地暴露出了個人的“胎記”,留心過我作品的人大概知道我要說的是那首《糖紙》。這首詩寫于1990年夏天,后來獲得了當年《飛天》雜志舉辦的全國詩歌大賽頭獎。一首曾為我帶來過榮譽和獎金的詩歌,同樣為我帶來了困惑。在此后的好長一段時間里,我的寫作始終沒有辦法擺脫它的陰影,即,被外界評論為“甜”與“膩”的寫作風格。無論是后來的《蘋果堆》,還是《野花開放》,都沒有超越那張“糖紙”所給予我的更為明晰與直接的力量。我曾經無數次剖析《糖紙》一詩寫作的動機,并試圖通過解構的方式來洞察它之所以為人喜愛的原因,最后只得出了一個結論:與其說它純凈,不如說它簡單。時至今日,每當我想起它時,腦海里就會回蕩起那段由無數個閑云野鶴般的日子所串連起來的旋律:十來個放棄了“理想”的大學畢業生散漫地坐在一座剛剛成立的三流大學的臨時青年教工宿舍前,細瞇著一雙雙空虛的眼睛眺望山崗下凌亂無序的小城,水泥鋪就的籃球場邊堆放著紅色的磚頭,麻雀和雞在草地與石子的縫隙間覓食,遠處,有更為茫然的青年正在跟隨一架老式的卡口錄音機哼唱姜育恒的《再回首》……正是在這樣的一個正午,一個男孩趔趄著走進了球場,從白得發亮的地板上撿起一張玻璃糖紙,對著太陽張望起來。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這個男孩最終看見了什么,但我知道我看見了詩。準確地說,這應該是我第一次近距離地與詩歌遭遇。
幾年以后我曾經寫過一篇隨筆《內心的糖果》,在追憶過童年時代對糖果的向往之后,我在結尾處不無悲憤地寫道:“那時候,我們不可能想到會在有朝一日離開糖果,即使是最為甜蜜的糖果,我也會有毫不動心的時刻。我甚至武斷地認為,凡是牙齒健康的人都是我童年的伙伴,而那些齲病患者活該倒霉,因為他們吃了太多的糖,在我吃不到糖的年代里。這才應該是‘以牙還牙的真正涵義。我這樣憤然地想著,我想面對今天咬牙切齒,卻感到滿口的牙齒在隱隱作痛。”
很多優秀作家到頭來都承認,一個人的童年經驗會對他的寫作產生致命的影響。正是緣于早年物質生活的貧乏和精神上的渾噩,才導致了那個正午我與一張糖紙的遭逢。有人通過一塊石頭,或者一截銹蝕的廢鐵,重新認知那個蜷曲在他內心深處某個角落里的名叫“宿命”的家伙,而我肯定是通過它:糖紙,一種介于塑料與玻璃之間的神秘物質,幾只蜜蜂在飛,但翅膀是靜止的。
然而,我萬萬沒有想到,當我在后來寫作了大量的苦澀、沉痛的作品之后,當我自以為已經徹底擺脫了這張《糖紙》時,它居然又鬼魅般出現在了我的另外一首詩歌中:《高原上的野花》。許多朋友在閱讀此詩后都給予了它應得的褒獎。我說它“應得”,是因為直到今天我都不肯承認它是我“寫”出來。就像我在一篇文章里所堅信的那樣,詩歌不是寫出來,如果你承認它是奇跡,你就得培育自己等待奇跡的耐心,并為這個奇跡的光臨而做好一切準備。我相信,只要是稍具文才的人如果親臨那片野花蕩漾的神秘高原,都可以毫不困難地隨口吟誦出大同小異的詩句來。而我不過是提前到達者之一。
和《糖紙》一樣,《高原上的野花》也是一首極簡之作,除了幾處顯而易見的隱喻,幾乎沒有任何多余的形容詞。全詩用五個“愿意”將高原和野花提升起來,將我和老父親降下去,以此促成一種歷經滄桑之后的澄明心境,以及人與自然相互通融的理想境界。至此,單個的“小女孩”已經變成了漫山遍野的“小美女”;當年目光空虛的年輕人已經成長為“一個披頭散發的老父親”。場景在轉換,但一個寫作者的內心卻沒有發生本質的變異,不過是由小而大,由單純日趨繁復。寫作的意義就在于,我們毫無保留地將自己扔在時光的砧板上,任其切割,直到使時光感覺到自身的老邁和無趣。這時,詩人站立起來,開口稱頌自己的敵人,稱頌那些無情的時光成就了他抗擊打的能力。
五
我在黃鶴樓下居住了將近二十年。推開門窗,星月皆無,唯有這樣一座高樓雄踞于視野之內,作展翅欲飛狀。黃鶴樓,你甚至不是建筑,不是傳說中的大鳥,不是李白的沮喪和我此刻的迷惘,那么,你是什么?二十年來,我從湍急的青年逐漸向平緩的中年過渡,你見證了一個寫作者無以名狀、難以遣懷的悲傷和喜悅。你不說話,我卻能夠聽到你的呼告和吁求;你沒有眼睛,我卻被重視和盯蹤。黃鶴樓,這么多年來,我搬過七次家,但無論我怎樣試圖躲避你,你都會以各種方式與我內心構成一種緊張的對峙關系。屈指算來,我總共登臨過三次黃鶴樓,一次是1984年秋天,我以一介學子的身份膜拜在你的面前,激動得幾乎不能自持;第二次是1998年夏天,我陪一位來自越南的年輕漢學家爬到樓頂,氣喘吁吁。我問她登臨斯樓有何感受,她笑道,以前只知道中國人多,但從高處望下去,我才發現,中國人比我想象的還要多;第三次是2004年夏天,我陪一位從李白故里來的詩人拾級而上,繞梁數圈,俯瞰荊楚,心中涌蕩著渾濁的江流……
“連江水都改變了顏色,我們干嘛還要寫詩?”你拍打著這一切,仿佛灰塵
需要安慰,大地上全是你的親人
這是我1999年寫給小說家李修文的一首名為《黃鶴樓》的詩中的幾句,那時他剛從東瀛轉道東北,回到武漢。我清楚地記得,那幾年我們一干人在一起度過的那些個荒唐的夜晚:凌晨過后的電話鈴聲,以及清澈的啤酒、干凈的牌局。“我們干嘛還要寫詩?”這是個問題。但只有當我逼近四十歲時,這個問題的嚴峻性才如此真實具體地凸現出來。
不久前,我寫過一篇題名為《說愛》的隨筆,在那篇文章中,我對自己這么多年的寫作動機進行了真誠的檢索,最后我發現,唯有愛才是促使我以“寫作者”的姿勢走到今天的原因(請注意,是姿勢而非名義)。愛什么、為什么愛、如何愛?這些本來早已被人回答過無數遍的問題,一次次擺到了我的面前,迫使我直面生活并心甘情愿地為之付出高昂的代價。
我曾經一度以為愛就是善與美,但現在我認識到,善是好的,美是好的,然而,它們只是愛散發出來的光暈。愛在更多的時候像一個不聽話的孩子,她并不循規蹈矩,她偏執、任性,甚至有時是壞的。愛從來不依附于他物,如同一個獨立的、有自決能力的人,即便你斫去她的雙足,她依然會不顧一切地爬向自己命定的目的地。“你可以消滅他,但你無法打敗他。”同理,你可以剝奪他愛的權力,但你無法終止他去愛。愛的復雜性就體現在這里,因其無限近似于死卻又不甘心于死,愛有時會與死建立起某種同盟關系,從而與“生之幸福”的人類終極理想形成難以調和的悖論。
不得不承認,日常生活的磨蝕對一個寫作者的才能會產生巨大的耗損。在生活這個嘈雜的現場里,寫作者沒有豁免權,他所扮演的角色與任何人沒有二致,他是父親、兒子和丈夫,是家長、納稅人、洗碗工、采購員、煙民、酒徒,也是“新聞聯播”或“足球之夜”的忠實觀眾……他是若干人的混合體,沉重、沮喪、亢奮,仿佛一只鳴器,只有當萬籟俱寂塵埃落定之時,屬于他個人的那座隱秘的蓄洪;回才會悄悄打開。這就是為什么我始終傾向于將寫作者當作“地下工作者”來看待的原因。我一直難以將自己的寫作置于“光天化日”之下,無論何時何地,我都要拼死捍衛那個專屬于我一個人的角落,它幽密、慎獨、安靜,同時又進退自如——必須有一條值得信賴的通道,讓我與日常生活保持從容的對接關系。這通道就是寫作者的肚臍,一再提醒著我的來歷和出處。所以,在我這里,寫作從來不是炫技之術,也不是簡單的抵抗,甚至不是庸常意義上的“揭露”和“批判”,它是耐心地守候,和閃電般地突然一擊,是一次次奇跡的光臨,更是對隱藏在這些“奇跡”背后的那個龐然大物的好奇之心。如同嬰兒對母乳的依賴一樣,我依賴生活,時常饒有興致、得寸進尺地把玩它的每一個部位,并試著說愛。有了愛,寫作者就有了足夠的底氣,有了根據地。接下來才是如何提升自己愛的能力的問題。在我個人的詞典中,愛遠不止是一件防御武器,她是一塊磁石,一塊海綿,她能吸納許多敵對的事物,并予以消化,變成心靈的給養。你若愛親人,他們會化為你身邊的空氣;若愛家園,它們會化成你的靈魂;若愛敵人,你便具備了抗擊打的能力。對于一個優秀的寫作者來說,愛從來都不是單純的表達,不是簡單的索取和給予,甚至不是古典意義上的“海枯石爛”,而是寂寞的耐心,是懷著感恩去承接,為了理想而隱忍,是絕望中的自救,是“向死而生”,是“心中有美卻苦于贊美”。有時,愛還與惡交織在一起,在我們的內心深處搏斗,使我們即便遠離硝煙,也能夠時刻感受到人性之復雜。如是,文學的豐富性才得以彰顯,寫作者才得以愈來愈強大,成為真正獨立的“這一個”。
那么,沒有愛,還剩下什么呢?是不是只剩下了恨呢?答案是否定的,恨作為愛的對立面,并不是愛最可怕的敵人,無數事實已經一再證明,愛的主要敵人是虛情假意。虛情假意對愛的傷害遠大于恨,它借助愛的外殼來蒙蔽受愛者,以期逃脫屬于自己的擔當;它通過量的積累來折磨愛的精力,最終使愛加入到了恨的行列。而恨的因子一旦成為一個時代的主流,冷酷便會大行其道。我們這個時代的寫作由于愛的缺席而招致了文本力量的喪失,作者和讀者幾乎同時變成了生活的旁觀者。當愛成為稀罕之物后,物質化、技術主義便不斷對我們的心靈施壓和圍剿,它們使寫作變成了一種拓展自我疆域和領地的手段,要么,淪落為打發時光的玩具。這種寫作表現為:抖勇講狠,不說人話,代神立言,或者甘愿與禽獸為伍。文學不再是用來凸顯與揭示生活意義的利器,而寫作者也一步步淪落為人群中最為軟弱的“那一個”。
我始終認為,當“寫什么”和“為什么寫”都不再是問題,當我們只剩下了“怎樣寫”的時候,文學就走到了自己的末日。沒有人懷疑形式主義能夠帶來“詩意”,但我懷疑,詩意與詩之間的距離,如同月光不是月亮一樣,那些拋撒在我們身邊的灰塵也不是泥土本身。
“刀子捅進去,為什么沒有血?”這是多年前我在一首詩歌中所發出的感嘆,如今這樣的感嘆依然成立。如今,我依舊徘徊在黃鶴樓下,但我心中不再畏懼,我清楚,盡管已經有那么多的崔顥、李白“題詩在前”,但我已經把自己納入傳統的一分子,也將愛視為全人類最深厚、最有活力的傳統的源頭。
六
如果說文學是有意義的話,那么,寫作卻經常讓人看不到“意義”何在。當這樣的想法越來越清晰、固執地縈繞在我腦海里時,陽光正從遙遠的天際射進這間冬日的書房,我感到領口微微發熱。外面傳來一陣陣水泵的轟鳴聲,那是工人們在清理污水,再過一段時間,這座滿是淤泥的都司湖就將煥然一新了。我一邊暢想著蕩漾的碧波,一邊在心里對自己說:瞧啊,這里又坐著一個無用的人。是的,無用;而且是“無用而頹廢”。這樣的感覺令人沮喪。作為一個整日與文字打交道的人,我現在對眼前這種畫地為牢的生活已經忍無可忍,每當心靈被如上挫敗感所侵襲,我就會不由自主地站起來滿屋子走動。多年的寫作終于成就這樣一個事實:坐在這里的人是個失敗者。
承認失敗了,然后正視這個結局,這并不羞恥。真正的羞恥在于,你一味地寫著,卻從來沒有感覺到失敗已經成為了宿命。所以,被我視為同道的作家,應該是這樣一種人:他心懷絕望卻永不甘心;他把每一次寫作都當作一次受孕,并調動起全部的情感來期待這一刻的來臨;他是生活的受迫者,同時還有能力成為自己的助產師。這樣的寫作者最終可以從宿命出發,抵達不知命運忘其命運的境界。
幾年前,我讀到余笑忠的長詩《俯首》,在第八節,詩人這樣寫道:“寒冬在加深。一群鄉村小學的孩子,在墻角彼此撞來撞去。他們這樣相互取暖。”讀到這里,我渾身涌蕩著一股暖流。此后,“撞身取暖”一詞就深深地烙進了我的心中。在我看來,完全純粹的寫作就是這種面向自生自滅的寫作,朝向灰燼、墓穴,和虛無。既如此,發表何益?交流何益?我想,我們之所以還可以容忍自己與這個俗世勾肩搭背,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盡管你是孤獨的,但你相信自己并不孤立。于是,你一再心存熱望。希望有朝一日能夠在這個世界上碰見可以與你“擅身取暖”的人。
七
已故詩人宇龍在一篇關于詩歌的隨筆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寫作是什么?寫作就是私設公堂!”語氣肯定,毋庸置疑。很長一段時間里。“私設公堂”這幾個字被我寫在了電腦桌前的一張紙片上,在一堆散亂、潦草、無厘頭的字跡中。我總能一眼就看見它。眨眼間,宇龍已經離開我們四年,面對他給寫作下的這個亞“定義”,我時常思緒萬端。拆解這個成語是容易的,但若是要擔當起拆解之后所帶來的連鎖反應卻多少有些沉重。在我看來,宇龍的判斷至少包含了這樣幾層意思:
A、寫作是一樁“私事”;
B、就其指向來講,它關乎人類情感的“公共”部分;
c、它是一種“非法”行為;
D、寫作即審判。
作為一個寫詩者,只要稍具覺悟,就能夠做到A,再進一步達到B。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可以擔當C與D。C是反抗,且是反復的反抗;D是內省,遙遙無期地掙扎和等侯,是自我裁決。在這個文學價值與詩歌標準普遍喪失的時代,我寧愿信任一個詩歌烈士給出的這,樣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