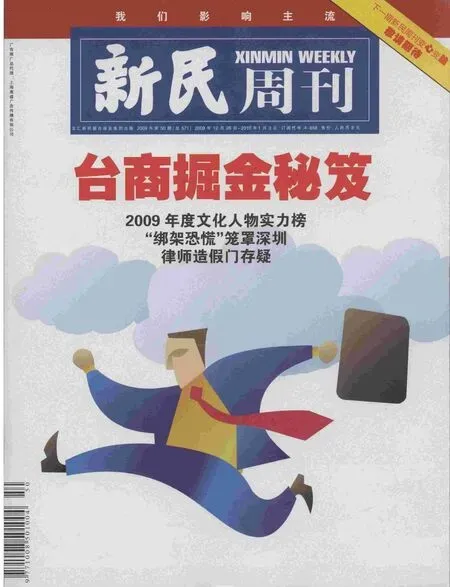臺商西進(jìn)三十年
季天琴



百變臺商
很難只用一種動物來形容臺商。他們是身段柔軟、“外形”多變的族群。
雖然海峽清淺,但大陸與臺灣在諸多領(lǐng)域的差異,還是讓第一批的弄潮兒頻頻嗆水。但他們迅速變形,兇猛生長,在政經(jīng)夾縫中左右逢源,以致后來者不禁喟嘆:這哪是賺錢,分明是在印錢啊!
如今,臺商西進(jìn)大潮已蔚為可觀,競爭趨于白熱。百萬軍中,唯變不敗。且聽臺商高手自曝創(chuàng)新心得。
這些臺商的跌宕人生,成為一個時代的注腳,一個社會的倒影。
人往高處走,錢往利處流。
大陸之于臺灣,曾經(jīng)是余光中詩中那“一灣淺淺的海峽”,最終停落在羅大佑的《美麗島》中,歌手柔腸低回地唱道:滄海遺珠啊,目光何烈如炬,故土夢里追,歸鄉(xiāng)共飄泊去……
時光流轉(zhuǎn),普通民眾在悲情與激昂中日益看清楚,民生的考量在兩岸的政治圖譜中究竟占有幾分位置。
未來,臺灣經(jīng)濟的發(fā)展要把大陸列為腹地。
如今,臺商投資大陸蔚為壯觀,回過頭來看,人為造成的阻滯終究擋不住經(jīng)濟上的相互需要,盡管阻隔依然存在。
臺商幾度沉浮,其實正是兩岸經(jīng)貿(mào)數(shù)十年融合的縮影。
解除“戒嚴(yán)”前后
1984年,臺商葉宏燈第一次來到北京,他從北京的機場下飛機,沿途所看到的景象是一片蕭條,連片綠葉子都沒有,這似乎印證了島上的宣傳,“大陸同胞窮得連樹葉都吃掉了”。過了一段時間,他才明白,這是北方大陸性氣候里正常的落葉。
同年,臺商黃益建從北京一路考察到福州后,經(jīng)過慎重評估,他做了一個決定:在福州投資。而這在當(dāng)時兩岸緊張的局勢下,可是一個冒險的決定。
他投資120萬美元,建了一個服裝廠,并在福州中心地段八一七路買了一塊地。1986年,黃益建向當(dāng)?shù)毓ど滩块T申請了營業(yè)執(zhí)照。領(lǐng)證那天,工作人員告訴他,他這本證件是福州市臺資企業(yè)001號,意味著他的閩臺行成為大陸第一家臺商獨資企業(yè)。
對于這個第一,黃益建感到有點郁悶,那時已有一些臺商到大陸投資,都不敢去申請執(zhí)照,這個“第一”,在當(dāng)時可不見得是好事。
那時,由于臺灣島內(nèi)生產(chǎn)經(jīng)營成本逐步攀升,島內(nèi)制造業(yè)生存環(huán)境日趨惡化,使不少臺商前往大陸尋覓商機。臺商能夠正式“試水”大陸,緣于1987年臺灣當(dāng)局解除“戒嚴(yán)”。
1987年3月中,農(nóng)歷春節(jié)剛過不久,家家戶戶團圓度歲的氣氛還未散去,蔣經(jīng)國在辦公室內(nèi)和一位親信幕僚談話時,忽然問到,唐詩有首描寫離家很久的人回鄉(xiāng)時心情的詩,你該記得。
幕僚答復(fù),頭兩句是“少小離家老大回,鄉(xiāng)音未改鬢毛衰”。蔣經(jīng)國接著說:“這正是現(xiàn)在榮民老兵們的心情,你們?nèi)ズ煤醚芯?盡快實施正式開放大陸探親的辦法。”
“行政院”依國民黨中常會的決議,通過“復(fù)興基地居民赴大陸淪陷區(qū)探親辦法”,隨即并宣布自同年11月2日開始實施,委托紅十字會總會著手辦理。
事實比想象更為熱烈,紅十字總會準(zhǔn)備了1萬份的申請登記表,3天之內(nèi)就被領(lǐng)光。而在當(dāng)年年底之前,啟程前來大陸的民眾已經(jīng)超過3萬人。
臺商開始光明正大地登上臺面。投石問路的多是中小型企業(yè)。
1988年7月,國務(wù)院頒布了《關(guān)于鼓勵臺灣同胞投資的規(guī)定》,進(jìn)一步促成了臺商投資大陸的第一波浪潮。在當(dāng)時許多臺商把大陸沿海地區(qū)作為加工出口基地,以臺灣接單——大陸生產(chǎn)——香港轉(zhuǎn)口——海外銷售的模式,大量轉(zhuǎn)移島內(nèi)以輕紡為代表的勞動力密集型產(chǎn)業(yè)。
在當(dāng)時的臺商們中間,流行著這樣一個詞——“打帶跑”。打帶跑原本是棒球運動中的一項專業(yè)術(shù)語,意思就是擊球的同時運動員也要跑壘。
這是一些臺商早期投資大陸的經(jīng)營理念,意思就是在大陸投資的同時,也要做好隨時抽身離開的準(zhǔn)備。
缺乏認(rèn)同感、顧慮重重,是早期臺商投資大陸的真實寫照。雖然投資大陸,擁有相對低廉勞動力成本和巨大的消費市場等優(yōu)勢,可是改革開放究竟能夠維持多久,大陸經(jīng)濟能否持續(xù)增長,在臺商們看來還只是個未知數(shù)。
從東莞到蘇州
1993年,東莞臺商楊永安驅(qū)車從廣州到東莞到后街,路上開了四個半小時。路況很差,他坐在車上就跟騎馬一樣。然后,他從后街到深圳,路上又是四個半小時。基礎(chǔ)設(shè)施的落后,讓他直呼受不了。
在當(dāng)時,廣東東莞還是一個并不起眼的農(nóng)業(yè)縣,一切都才剛剛起步。如今電子工廠聚集的石碣鎮(zhèn)還是一個小島,鎮(zhèn)里的人車進(jìn)出都要靠船運。在這樣的條件下,從上世紀(jì)90年代初期開始,東莞一步步成為臺商云集的淘金之地。
上世紀(jì)90年代初期,鄧小平南方講話和十四大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方向,為港澳臺資企業(yè)投資營造了良好的軟環(huán)境。
鄧小平的一席話帶給臺商更多的是心理層面的影響。葉宏燈回憶,“由于根深蒂固的對峙觀念,臺商不可能把自己的家當(dāng)投注到一個非常不放心的地方,鄧小平南方講話以后更堅定了開放,大家才一窩蜂地全部進(jìn)來”。
在臺商們看來,當(dāng)時最靠近香港的深圳經(jīng)過十多年的急速發(fā)展,地價和工資早已水漲船高,這讓勞力密集型產(chǎn)業(yè)的臺資企業(yè)很難承受。位于深圳、廣州之間,經(jīng)濟剛剛起步的東莞,就成了臺商們的首選目標(biāo)。
上世紀(jì)90年代初,開發(fā)開放浦東的戰(zhàn)略決策正式推出。這一決策使臺商在南下珠三角之后又開始涌現(xiàn)北上長三角的熱潮。1993年,作為第一家到蘇州新區(qū)投資建廠的臺灣地區(qū)計算機廠商,李錕耀從上海到蘇州用了三個半小時。“那時候可以看到更多的是農(nóng)田和莊稼。”李錕耀回憶說。
現(xiàn)在,沿著滬寧高速公路開車從上海到蘇州只要一個小時就夠了。
此前,剛從瑞士洛桑IMD管理學(xué)院學(xué)成回臺并接掌明基的李錕耀,決定在內(nèi)地設(shè)立明基的生產(chǎn)基地。
當(dāng)時,大陸吸引外資最集中的地區(qū)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廣東、深圳等華南地區(qū),李焜耀看了一眼就將其排除了,理由很簡單:早期工業(yè)地帶,產(chǎn)業(yè)規(guī)劃缺乏整體性和規(guī)范性,工廠雜亂無章,管理人員經(jīng)驗不足,城市規(guī)劃和市政建設(shè)比較混亂。李焜耀將目光移向了正在轟轟烈烈搞建設(shè)的未來中國經(jīng)濟重心——上海。
李焜耀去上海招商局談投資意向,負(fù)責(zé)接待的人是復(fù)旦大學(xué)計算機系畢業(yè)的大學(xué)生。李焜耀很奇怪:“你為什么不搞專業(yè),卻改行招商?”此人回答說,他的同學(xué)差不多都轉(zhuǎn)行了,很少有人在寫電腦程序,因為進(jìn)房地產(chǎn)這樣的企業(yè)更賺錢。
李焜耀由此知道:在上海工作的人,商業(yè)意識太濃,他們向往外面的世界,不會埋頭于自己的專業(yè)。如果在上海設(shè)廠,辛辛苦苦培養(yǎng)一個工程師,可能兩個月后就會跳槽到房地產(chǎn)行業(yè)去了。
李焜耀敏銳地抓住了問題的關(guān)鍵:商業(yè)大都市并不適合制造業(yè)建廠發(fā)展,制造業(yè)應(yīng)以商業(yè)大都市為中心,布局在其周邊100公里左右的衛(wèi)星城。蘇州恰恰符合李錕耀所說的設(shè)廠原則。“蘇州是一座古城,給我很寧靜的感覺”,李錕耀一踏上蘇州的土地,就喜歡上了這個有著2500年古老石板街的城市。
把明基的生產(chǎn)廠設(shè)到蘇州,在作出這個決定以后,李錕耀便開始積極說服明基的配套廠來蘇州投資,“我?guī)Я撕脦讚芘涮讖S商到蘇州來考察,但是最終決定留下來的不到三成”,“各種威逼利誘的手段我都用上了”。
直到五六年之后,明基所有的配套廠商才全部集中到了蘇州,也是在這段時間內(nèi),很多臺商縮小了在東南亞地區(qū)的投資規(guī)模,轉(zhuǎn)而大規(guī)模進(jìn)軍內(nèi)地市場。
2003年2月12日,投資大陸的各地臺商協(xié)會負(fù)責(zé)人春節(jié)聯(lián)誼活動在澎湖結(jié)束,100多名臺商座談后預(yù)計,如果5年內(nèi)還不實現(xiàn)“三通”,臺商將會因成本負(fù)擔(dān)過重而喪失競爭優(yōu)勢,不少臺資企業(yè)會倒閉。同年,一個倒閉臺商陳彬的《上海商機》問世,這是一年半時間里他出版的第四本書。
陳彬畢業(yè)于臺灣輔仁大學(xué)經(jīng)濟系。在上海開過不銹鋼廠、面包廠、餐廳、快餐店、火鍋店等,因經(jīng)營不善,這些店逐一倒閉。十多年搏擊商海的失敗者干脆躲進(jìn)書齋,拿筆寫書。
當(dāng)時臺灣正在“大選”,書店里暢銷的全是政治人物的書。他的書一直被冷落,連上架機會都沒有,機緣巧合,他上了李敖的“秘密書房”節(jié)目,在節(jié)目中他告訴人們該如何在大陸避免失敗,還大罵一些臺商熱衷在大陸包“二奶”,李敖聽了哈哈大笑。節(jié)目一播出,陳彬的書很快賣光。
第二本書《移民上海》出版時恰逢臺灣股票大跌,島內(nèi)經(jīng)濟下滑,很多人想移民,陳彬的書再次意外走紅。后來他寫的《我的上海經(jīng)驗》再版達(dá)28次之多。
從最早登陸的地方廣東珠三角以及與臺灣一水之隔的福建東南沿海,近30年的時間,臺商在大陸發(fā)展經(jīng)歷了北上、西進(jìn),他們的足跡與大陸的改革開放緊密相連。距離上海不到一小時車程的江蘇省昆山市,甚至獲得了“小臺北”的稱號。
不動聲色,不容置疑
事實上,沒有哪個地區(qū)像臺海兩岸這樣存在著政治對峙但民間交流頻繁且愈漸緊密的矛盾。這種巨大的張力,充分體現(xiàn)在臺灣人的思想中。對應(yīng)著海峽這邊的,是兩岸經(jīng)貿(mào)交往數(shù)據(jù)逐年不動聲色的攀升和一種不容置疑的眼神。
2001年9月4日,一個80多歲高齡的小學(xué)畢業(yè)生發(fā)表長達(dá)4萬多字的文章,嚴(yán)厲批評在李登輝和陳水扁“戒急用忍”政策的禁錮下,臺灣等于自我束縛和凍結(jié),就像一潭死水,業(yè)界束手無策,只能坐以待斃。
這個小學(xué)畢業(yè)生就是被譽為臺灣“經(jīng)營之神”的臺塑集團董事長王永慶。
隨著臺塑集團規(guī)模的迅速擴大,島內(nèi)早已不能滿足需要,用王永慶的話說:“彈丸之地,已經(jīng)難以容下石化王國”。可是,從李登輝到陳水扁,臺灣當(dāng)局死守“戒急用忍”,石化產(chǎn)業(yè)也在禁止投資大陸之列。
從第一撥以輕紡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產(chǎn)業(yè),到第二撥以石化為代表的資本密集型產(chǎn)業(yè),再到第三撥以電子為代表的技術(shù)密集型產(chǎn)業(yè),可以說,臺商在大陸的投資活動歷程,不僅密切了兩岸的聯(lián)系,推動了兩岸關(guān)系的發(fā)展,同時它也成為兩岸經(jīng)濟交流合作中最具活力的因素。
2002年,大陸市場芯片銷售總額為1100億元,增長23.6%,而且大陸IC產(chǎn)業(yè)還處在萌芽期。這一年,全球半導(dǎo)體帝國臺積電老總、臺灣“IC教父”張忠謀曾向陳水扁提出,開放8英寸芯片登陸,而島內(nèi)重點發(fā)展12英寸產(chǎn)品。
不過,臺灣當(dāng)局卻認(rèn)為,芯片產(chǎn)業(yè)代表著臺灣經(jīng)濟的最后一根命脈,不讓臺積電來大陸投資,可以阻滯大陸芯片業(yè)的發(fā)展。
在當(dāng)局的敏感神經(jīng)下,2002年1月,張忠謀揚帆西渡,到南京、上海等地考察。由于害怕臺當(dāng)局派人監(jiān)控,張忠謀曾在高速公路上數(shù)次換車。同年5月,臺積電在上海與松江科技園區(qū)秘密簽訂投資意向書,臺積電投入近10億美元。
張忠謀所代表的兩岸的經(jīng)貿(mào)趨勢,一是投資由傳統(tǒng)勞動力密集產(chǎn)業(yè)轉(zhuǎn)向芯片和液晶等高科技產(chǎn)業(yè);二是投資逐步向大型化發(fā)展,包括數(shù)千萬美元甚至數(shù)億美元的投資項目,最終臺灣上市公司有一半以上在大陸投資,在臺灣形成“大陸概念股”。
而這些臺商的跌宕人生,也成為一個時代的注腳,一個社會的倒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