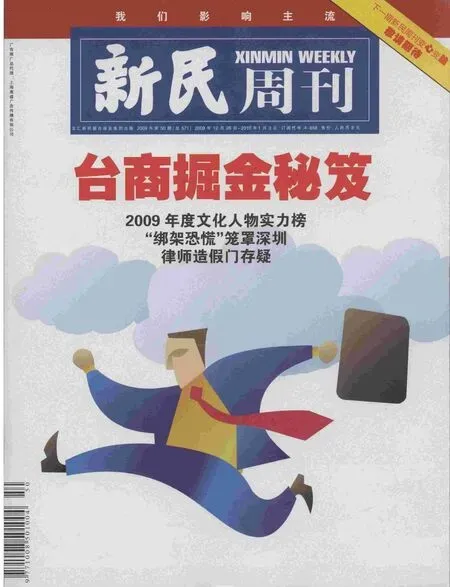律師不是“打黑”的反義詞
王 琳
由重慶“打黑”所引發的程序正義之辯,已在整個公共輿論領域蔓延開來。一名為涉黑嫌犯辯護的辯護律師被抓,更是掀起了輿情的千重浪。在法律圈,我們看到,本就不甚牢固的“法律人共同體”已然分崩離析。助理反水,同行相斥,教授們也放下嚴謹與沉穩的身段或贊或彈,忙著表態。小說《原諒我紅塵顛倒》中的虛構的黑幕在現實生活里真實地徐徐拉開。
對于一個未決案來說,過早進行價值判斷有失法律人的理性。從理論上說,“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警方不也出了那么多敗類嗎?有個別“黑心律師”一點也不稀奇。某個律師的“黑”與“不黑”、罪與非罪,有賴事實與法律的認定,現在還不是我們這些看客們所能評價與判斷的。這個律師之前做過什么,說過什么,也不是可以推論他“黑”或“不黑”的理由。
我們所能評價的,就是程序的當與不當。三十年法律恢復重建,盡管步履艱難,仍然留有不少足以令我們彌足珍貴的司法遺產。比如“無罪推定”,比如“控辯平衡”,還比如“從公檢法流水作業模式”到“控辯審三角結構模式”的轉型。
曾記否,我們一度無視司法規律,混淆偵、訴、辯、審職能,而堅持刑事司法的“專政”功能。這表現在刑事司法制度沿襲著從偵查到起訴到審判的流水作業模式,公安、檢察、法院與司法行政機關雖然機構獨立、職能各異,但在打擊犯罪上,卻往往被從政治的高度要求統一步調,擰成合力。因而,公、檢、法、司也成了政法系統中的兄弟單位,至于辯方,則被人為忽略。當然,在律師吃著“皇糧”的那個時代,作為司法行政機關的國家工作人員,律師同樣要服從“公檢法流水作業”的大局。
隨著刑事司法現代化步伐的加快,尤其是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訂以后,控訴、辯護與審判之間的關系得到進一步厘清,律師在訴訟中的作用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認同。
司法公正離不開律師,這是因為被告人作為被追訴的對象,對追訴機關有畏懼之心。且被告人通常被適用了某種強制措施,人身自由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因此不能自行深入全面了解案情,收集有利于自己的情況和材料。而隨著法律的日益技術化,被告人多數缺乏足夠的法律素養,不能正確運用法律為自己辯護。由律師擔任辯護人,一方面,律師可以通過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供法律服務,使其免受非法侵害,或在遭受侵害后能及時得到法律上的救濟;另一方面,律師職能的充分發揮,也成為約束公安司法機關公正執法和保障法律正確實施的必備條件。
由于深受國家本位主義的影響,我國刑事司法制度長期以來過于注重對犯罪的追究和懲罰,而輕視對被追訴人人權的保障。雖然1996年《刑事訴訟法》的修訂大幅加強了被追訴人及其律師在訴訟中的權利,但實踐中根本得不到應有的保障,以致出現了“會見難、閱卷難、取證難”等諸多怪現狀。更有甚者,立法還特別設計了一個“306條陷阱”,亦即刑法第306條所規定的“律師偽證罪”:在刑事訴訟中,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偽造證據,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留;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律師當然有可能觸犯偽證罪,就像警察也有可能偽造證據一樣。觸犯偽證罪的,都應追究責任。問題在于,是否有必要單獨存在一條“律師偽證罪”?將律師從偽證罪的諸多主體中單列出來,在律師頭上憑空懸掛一柄達摩克里斯之劍。刑事辯護的經濟利益通常較少,法律留給律師的回旋空間又不大,再加上難以預測的“306陷阱”,無怪乎不少律師都將刑事辯護視為畏途。
律師職能的有效發揮是實現程序公正的前提。法官就像一架天平,以無限接近精確為追求。而控辯雙方則分別位于這架天平兩端的托盤中。從控辯雙方占有司法資源的原始狀態看,它們之間天然便失卻平衡。這是因為代表國家追訴犯罪的控方在訴訟資源的配置上有國家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為后盾,而被告人及其律師則只能依靠微弱的個人力量來行使其權利。這種力量的失衡直接影響到控辯雙方調查取證的能力,進而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訴訟的走向。如果不通過某種平衡機制加以校正,公正便無以彰顯。
作為一個程序正義理念缺失且正在艱難建設“法治”的國度,媒體尤需承擔起揚法、弘法、護法及捍衛法律的社會責任。從網上言論來看,情況也許并沒有那么糟糕。支持律師依法辯護、呼吁打“黑”尊重程序正義的帖子也比比皆是。程序正義和打黑除惡,并非一組反義詞,律師辯護和警方打“黑”也可以并行不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