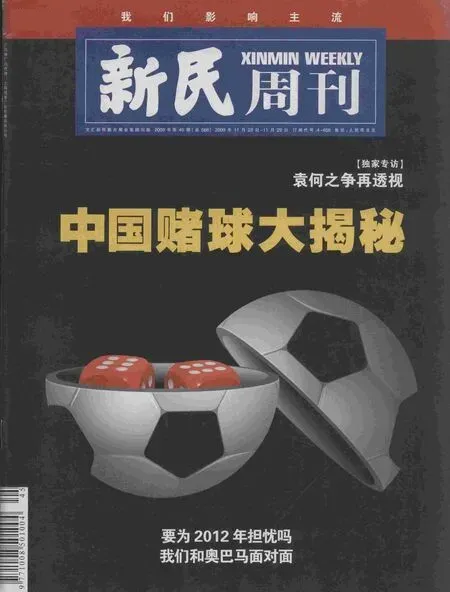愛與和平的保質期
B Y 言一
除了記憶之外,這世上大概沒有什么東西是不會過期的。就連“愛”與“和平”(這樣的“普世價值”),亦不例外。
李安新作TakingWoodstock在香港上映當天,李安蒞臨香港大學演講,我因有事無法前往,無法求證他這次拍攝Woodstock是否真的意在向Woodstock音樂節40周年致敬。從后來的報紙報道看,李安并沒有過多談到音樂節本身,而只是稱之為“自己的一段特別回憶”。
幾乎所有想去影院欣賞一場重現甚或打算“親歷”一遍Woodstock的觀眾,大多失望而歸。電影的鏡頭的確是寫實的,但基本未曾對準Woodstock的舞臺。取而代之的,是主角Elliot在“石墻之亂”后的尷尬生活處境,是他那待人待己都無比刻薄的母親,是遭受價值觀沖擊的小鎮居民,是蜂擁而至的嬉皮士們。在這些無比細微的鏡頭之下,你會發現李安長期關注的同性戀題材(從《喜宴》到《斷臂山》)依舊穿插其中,而他早期作品中重點處理的代際關系(生活三部曲)亦反復浮現。某種程度上,李安依舊是那個李安。
李安畢竟是那個李安。也許是出于對藝術史和音樂的興趣,即便是在電影中,我也會偶爾停下腳步,不再追隨鏡頭的腳步,駐足于某個鏡頭的瞬間,或是轉而在某段旋律中陷入回憶。盡管更多地偏愛李安早期的作品,但《斷臂山》中的畫面與音樂之美的確令人震撼,這次李安對于配樂的選擇依然出彩,可相比之下,影片中三人磕藥后的場景渲染卻近乎神來之筆——李安先是以鮮亮的色彩營造出維也納分離派作品的斑斕與絢麗,隨后這一原本屬于三人之間的斑斕與絢麗在一陣奔跑與嬉戲之后竟漸漸融入整個音樂節的無垠空間。所有的事物都在音樂的催化之下開始變形,旋轉;亮麗的燈火升騰為天際的群星,當紫色最終變得充盈,那最終呈現出的銀河般的意象似乎是在宣告:此時此刻,這里才是宇宙的中心。
繁華易逝,好景難存。即便是當年的Woodstock,所成就的亦不過是三天的“愛與和平”。三日之后,生活還當繼續——返工的返工,上路的上路;錢雖然是身外之物,人卻不得不去追逐。只是,“愛”與“和平”這兩個詞匯竟是承載了如此多的美好期望與想象,以至于人們不愿看到它們僅有三天的保質期,而希望它們可以長久留駐在生活當中。于是,我們看到了種種對Woodstock的向往與推崇,我們看到諸多對Woodstock的想象與哀悼。但不管愿景如何美好,我們卻依然必須直面Woodstock已死的現狀。對于國人而言,Woodstock早已淪為一種想象的符號;對于西方人而言則是現實中一種赤裸裸的消費。在這一點上,我無疑是同意詩人廖偉棠的。但與此同時,我卻并不贊同他對當初參加Woodstock的那40萬人的指責。換言之,我并不認為:剪去長發,去到硅谷或華爾街上班是一種需要受到指責的對自我的背叛。相反,我們更應該由此看出資本主義的邏輯,或者福柯所說的權力的收編能力是多么地無孔不入與強大。任何打算選擇反抗立場的人,恐怕都需要自問:自己是否足夠清醒,足夠堅韌。
無論是當年的Woodstock還是眼下的李安電影,在我看來并非毫無價值可言。也許,它們無力改變歷史的路徑,但卻作為歷史的一個事件已足夠引人注目;也許它們無力對所有人產生影響,但卻足以(至少部分地)改變部分人的部分人生。顯然,在這一點上,我贊成本雅明的看法:人們終究無法重歷歷史,而只能將之與個人記憶相連。
在王家衛的電影《重慶森林》當中,金城武曾說過這樣一句臺詞:“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在每個東西上面都有一個日子,秋刀魚會過期,肉罐頭會過期,連保鮮紙都會過期,我開始懷疑,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么東西是不會過期的?”而事實證明,除了記憶之外,這世上大概沒有什么東西是不會過期的。就連“愛”與“和平”(這樣的“普世價值”),亦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