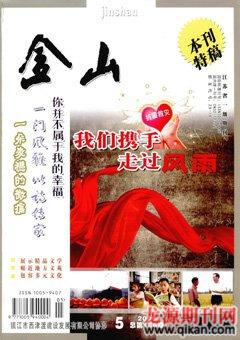一朵麥穗的微痛
馬 溫
風的方向為什么需要見證?
誰被賦予了見證者的身份?
山脈怎樣見證風的方向?
老槐樹怎樣見證?
星羅棋布的湖泊與列島又是怎樣在見證著?
對方向的眺望就是理想。對方向的熱情描述成為一門哲學。向這個方向投奔時,我們喘息,我們喊叫,我們甚至累倒在地,而這些不同力度的吶喊與呻吟最終成為不同流派的宗教信仰。
見證風的方向,就是為一場風的過程和結果作證,就是見證沙丘的移動,見證綠洲的脆弱,見證塵土對城市的洗禮,見證向日葵和甘蔗林的倒伏,見證狂濤對漁船的游戲,就是見證一種毀壞力如何以無序的回旋運動嘲笑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守則和范式。
當一個方向充滿了風量,當這種風量呼嘯著讓人難以抵擋時,其他的方向正在發生著什么呢?是什么也沒有發生,還是所有的脖子都被這股風奪走了意志力和注意力?
風是施蠱者。我們時常處于因受惑而產生的癲狂執拗中,以為原野上只有一種風向。我們衣服的褶皺和手臂的指向都和那個風向一致。很神奇當然也很荒唐的另一些事實是,森林中粗壯的樹干一齊向那個方向傾斜,放牧的羊群一齊向那個方向奔跑。
這是無法復原的傾斜,是沒有返程的奔跑。和風同一方向的奔跑讓我們成為風的一部分。我們被風的形態同化,我們不再具有骨骼和個體意志,我們化為不潔的碎片,和草屑、黃塵一起隨風而動。我們的加入壯大了風的聲威,而我們則在風的殖民號角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有沒有例外呢?是否有一個人,能夠成為阻遏狂風肆虐的山脈?是否有一個人,能夠偵探到遙遠的河谷間一場未名風暴的秘密集會?
而更大的例外和更大的期待是,一個人,能不能成為一場風暴的源頭呢?
風吹的方向,就是風活著的理由,風存在的證明。
風從來沒有喪失自己的目的性。風永遠懷揣著路書,永遠在出發。風的熱情,是刀劍的鋒刃,是鋒刃的冷焰。它用這種寒冷的青光保持自己的威嚴和帝王式的傲慢。
強暴、強勢、強健是風的血性。
風是毫不掩飾的傳播者,討伐者,是山川和面孔的涂改者。
人為何要見證?是因為自身缺少風的野性、強盛、摧毀力、自由奔放,人需要在閱讀風的過程中,大聲說出以上那些帶有野蠻音節的詞匯來補充自己的鈣質。撲面而來的飛沙走石,不容商量的席卷一切,張揚到極致的血氣之勇:這些蔑視理性樊籠的風語,也許能讓我們心底儲量稀薄的豪邁情懷有一次崛起和噴射。
偶爾,風會失去目標。風的雙眼布滿黑翳。風在絕望中變成龍卷風。龍卷風是是風中的盲人。風以被縛的受難者的扭曲形象,承受了觀望者的嘲笑與羞辱。風的超出想像的力量源于上帝的賜予,上帝當然有權沒收風的能量。每一場龍卷風都代表一次失敗的征討和被廢黜的雄心壯志。但我們很少看到龍卷風,因為風很少犯這樣的錯誤。
我們要承認,風的方向,也就是風的快樂,風的快樂之旅。風為什么不能享受快樂?
但風的快樂也構成一切事物的幸福感么?風的方向也是見證者的方向么?
我們的身體受物理性的制約,會不由自主地向風的方向搖擺。見證中充斥著順從,偃伏,迷信和尾隨,但也必然地萌發和傳播著懷疑情緒與背叛事件。
總是有極少的人,他的目光越過風的脊梁,風的滿足和狂笑,指向和風背道而馳的所在。
將見證篡改為背叛是深思熟慮的陰謀么?
這個人,成為一場新風暴的源頭。
他如果是寫者,風將從他的筆端,從那些赤紅的文字崖壁出發。他如果是一個歌者,歌聲就是風聲,風在他的丹田之處策源。這個成為風源的人,也許只是面對一棵樹說了幾個含混不清的字音,一場風暴就在它的寬廣的樹冠上橫空出世。這樣的風源不具有確定性,很像初秋迷離的螢火,它的產生完全遵循某種神秘原則。當此原則得到驗證,那個充當風源的人物在晦暗的背景下顯影,歷史的冊頁就被風吹皺。由這個人開始的風顛覆并重構了人們的思維季節。啟蒙的艱難時世、度盡劫波后身體與心靈自由的伸展,開始了。
從那片赭紅色山崖傳來的狂風,將在我們心中觸發一場超級地震。原有的思維和大山剝離了,泥石流阻斷了河川,一座有待命名的堰塞湖在我們心中形成。前所未有的地貌。前所未有的沖擊。前所未有的充足的氧氣和呼吸。一切不可能的事都成為事實。這場風讓河流在根本不能奔騰的峭壁懸崖中奔騰。它用一秒鐘的時間涂改了既定的一切,而我們目擊這一秒也許用了整整一生。
的確,只有很少的時候,很少的人物,能將一場見證變成勇敢的棄離和新生活的重塑。他迎風而立,他讓粗暴的風犁開自己的胸膛,土壤被深翻,空氣的顆粒、陽光的顆粒移植進泥土,山巒間鷹的振翅和滄海上的鳥鳴撒播進他的心靈。
一朵異樣的麥穗長出來了。
風被這個人物感動。風充當了見證者。風見證了一朵異樣麥穗的誕生。麥穗的芒刺在陽光下閃爍,讓看到的人感覺到久違的自由的微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