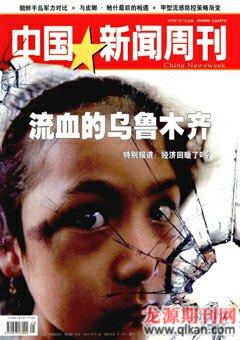美國高校如何防抄襲
周 琪
我的一位中學同學系中國政府高級官員,在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進修時,習慣于用中國的方式寫論文,下筆就說,“我認為……”教授對他說:“我不想知道你怎樣看,而是想知道你知道多少別人怎樣看。”
在美國讀博士時,一進校,學校對所有學生的入學教育的內容之一就是警告我們,抄襲被視為一個非常嚴重的道德問題,輕則本門功課不及格,重則會被開除學籍,甚至可能被要求承擔法律責任。
研究生們被告知,要想避免被指責為抄襲,必須在凡是引用別人的觀點時把提出該觀點的功勞(credit)記在原作者的名下,即用注釋來說明這是某人的觀點,在何時、何論著中提出。而且,如果你所引用的是被引用者的原話,還必須用引號標出,否則仍然會被看作是剽竊。甚至在使用例如“歷史的終結”這樣的短語時,由于這已經是福山家喻戶曉的觀點,必須隨時為它加上引號,表示這是個觀點是福山的專利。不過,如果一篇作品滿篇都是直接引語,固然可以免于被視為抄襲者,但會被看作是“偷懶”。
為了既不被指責為剽竊,又不被看作是懶惰,只有一種可供選擇的標準方法,即在引用作者的意思時,把原文所使用的所有的詞都用同義詞代替,還要盡可能改變句型或句子的前后順序,換句話說,就是用自己的話把作者的意思重說一遍。這是我們的英文寫作老師告訴我們的,而且她的主要工作就是訓練我們如何用自己的話復述作者的原意。
實際上,在我20世紀80年代末到美國大學學習時,對剽竊的判定標準還沒有像現在這么嚴格,那時我得到的印象是,如果你注明觀點的出處,就不算剽竊。但是,可能是由于在過去的一些年里美國學術界的抄襲現象日益嚴重吧,標準也變得越來越嚴格。現在的標準與我們所習慣的中文寫作有很大的不同:我們在用中文寫作時,為了準確傳達作者的意思,總是覺得一字不差地使用作者的原話是最保險的方法。
不過,英語老師提出的標準還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因為在學術論著中,有許多術語是難以替代的,例如政治、經濟、官僚等,不勝枚舉,如果不是一篇敘事文章而是一篇學術論文,我們怎么可能做到全部替換這類詞呢?最后,一位美國博士生對我解釋說,現在美國學術界中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如果一個句子中有三分之一的詞被替換,就不被認為是抄襲(當然你首先需要注明這是引自哪一位作者)。這個標準在我看來還比較可行。
這里所說的都還是在對一些數據、觀點給出出處的前提下,避免被視為抄襲的標準處理方法。至于對別人的整篇論文進行拷貝,再修改其中的一些詞和句子,那無論怎樣處理文字,都不能逃脫抄襲的罪責。博士生的論文都要在學校圖書館里存檔,可以向外借閱,如果發生抄襲,很容易被辨認出來。誰愿意拿自己的職業前途做賭注呢?
如果在中國研究生以就業壓力為由為抄襲辯護的話,那么美國學校的學生可能面臨的就業壓力更大。在我所在的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院里,博士生拿到博士學位平均花費的時間是7年(算上碩士學位),據說在哈佛平均是8年。
另一個與此有關的對博士生的訓練是,要嚴格按照標準格式或體例進行寫作,尤其是在引證方面。為了統一體例,我所在的學校要求以《芝加哥體例》(ChicagoFormat)為標準來撰寫博士論文(美國各大學的要求并不統一,但采用芝加哥體例的學校不在少數)。這是一本有1000多頁厚、像一塊磚頭一樣大小的工具書,它對所有可以想到的格式細節都做了詳細的規定。老實說,我為使自己的論文符合規定格式所花費的時間,遠比我準備論文答辯的時間多,后者只用了4天。如果一篇博士論文在體例上不合格,在它被送交學校圖書館裝訂存檔時就會被退回要求修改,而該博士候選人可能會為此耽誤了論文評審,從而在當年畢不了業。在準備答辯期間我覺得自己所做的一項工作是:在15天左右的時間內,學會做一名合格的英語雜志編輯。
可能有人會說,這是西方學術界故弄玄虛,制造繁瑣。他們會問,大量引證難道是必不可少的嗎?答案是肯定的,因為這是西方業已形成的學術傳統。其目的一是表明作者參考了在他之前的所有重要文獻,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完成的研究;二是給予前人成果和貢獻充分的肯定;第三,或許更重要的是,這體現了學術傳承,使得無論是前輩還是后輩的研究者,無論觀點如何不同,都使用共同的學術語言、站在同一平臺上對話或爭論。
我的一位中學同學,也系中國政府高級官員,多年前曾經到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進修一年,并按規定取得了碩士學位。他告訴我,最初他習慣于用中國的方式寫論文,總是一下筆就說,“我認為……”但是他的教授制止了他,對他說:“我不想知道你怎樣看,而是想知道你知道多少別人怎樣看。”這或許就是在西方學術界眼中學術與非學術的基本差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