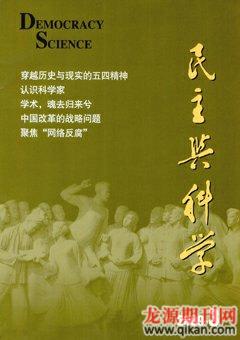首先要正確理解五四精神
劉志琴
對“五四”,我有一個文化情結,那就是民主和科學,這是我們前輩的追求,也必定會成為后輩的追求。30年前1979年的“五四”座談會,我也參加了,那時正值撥亂反正時期,與會者情緒高昂,大家歡欣鼓舞,對改革的前景寄寓莫大的希望。記得我發言的主題是“人的解放是五四運動的主潮”,現在看來當初的情緒過于樂觀,對可能發生的阻難估計不足,30年后的今天又參加同一主題的座談,卻有些悲哀。因為這些年來,五四精神受到很多質疑,有的認為根本沒有必要進行五四運動。有一種流行的看法,認為儒學在中國的中斷,是于“五四”時期激烈地反孔,使中國文化發生斷層,因此對中國道德文化危機的溯源,往往歸罪于“五四”時期的文化激進主義,這是不公平的。“五四”時期的反禮教,打倒孔家店,對思想啟蒙起了很大作用,對推進中國社會的改革是利大于弊,這無用贅言。真正使儒學在大陸衰落的是1949年后極左思潮的影響。
眾所周知,以階級斗爭為綱,曾經主導中國的一切事務,階級斗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深入到社會的每個角落,無人逃脫其外,間有非議的莫不受到沖擊或批判,階級斗爭熄滅論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參批。階級斗爭絕對化的傳播,肇成儒家的禮義仁愛被人唾棄。登峰造極的是在“文革”時期,大規模地評法批儒運動,席卷全國城鄉,抓了大人又抓小孩,江青在幼兒園中宣布要對幼兒進行“粗知馬克思主義”的教育,什么是“粗知”,就是從小就要接受“四人幫”那一套“階級斗爭”。我親眼看到,在我們社會科學院的大院內,一名出身不好的老人受不了批斗,縱身跳樓自殺,在圍觀的人群中有一個五六歲的小孩子,居然吐著吐沫,蹬著腳說:“活該,地主婆!” 看到這一情況我受到很大震撼,儒家所能剩下一點溫情脈脈的東西,全都被摧毀無遺。這又豈是孩子,大人又何嘗不如此? “文革”期間,紅衛兵沖進曲阜的孔廟,把孔子的塑像拉下神壇,挖了孔子的眼睛,對孔子剖肚開腸,到處抄家砸廟,焚燒書籍,毀壞先賢的遺跡和歷史文物,這才是對傳統真正的割裂。對這種滅絕歷史的行為和極左思潮,如今又清算了多少?
“五四”時期確實有一些知識分子對傳統有過激的批評,但都局限在精英的小范圍內,對社會的影響并不大,有個例證可說明問題。早在上世紀20年代“五四”以后,江蘇第一師范學校招生有一份考題,考卷中要求考生列舉崇拜的人物,應考的有300 多人,都是中小學生,統計的結果,列于第一、第二的是孔子和孟子。這份答卷實際上是個難得的民意測驗,他們的選擇和追求反映了小知識分子的思想走向。從這些答卷中可以發現,孔子和孟子的影響極其深遠,崇拜者有200 多人,占應答人數的三分之二,如果再加上顏淵、范仲淹、朱熹、王守仁等儒學名人,有絕對的優勢。由此可見,清末民初一些人雖然對封建禮教和儒學有過激烈的抨擊,但對中下層的讀書人影響并不大,在中小學生中尊崇孔孟的觀念仍很流行。時過70年,1994年10月10日《北京青年報》報道《專家警示:新一代正在忘卻歷史》說 ,有記者在北京一所中學初三班進行調查,發現全班50名同學,只有一人知道孔子的名字,無一人知道中國為何稱5000年文明。1993 年第3期《青年研究》刊載《中學生追星現象調查研究》一文足以引人深思。文章說,南京師大教育系對南京兩所中學進行民意測驗,要學生列出最崇拜的人物,統計結果前十名的人物按次序是: 家人、周恩來、劉德華、毛澤東、張學友、郭富城、林志穎、雷鋒、黎明、周潤發,其中除了家人和已故的現代人物周、毛和雷鋒以外,都是港臺明星,歷史上的儒家人物一個也沒有。
真正割裂傳統的是在十年動亂的“文革”,是一度愈演愈烈的極左思潮! 把“五四”當作替罪羊是不公平的,鑒于種種質疑“五四”的論調,歷史學家不去正本清源,是史學的悲哀。所以我們還要補上一課,理解“五四”才能真正弘揚五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