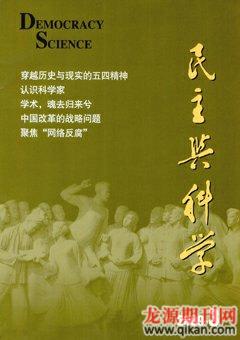不信東風喚不回
吳炳南
時屆耄耋,回眸60年文藝生涯,平淡無奇,乏善可陳。稍微有點意思的一件事,卻是與新聞勿搭界的“特約記者”的破冰之旅,可謂是歪打正著。
1979年2月4日,農歷已未年正月初八,時值立春,是個星期日。這一天,距1978年5月安徽省文聯恢復建制還不到九個月。黨組成員、知名小說《還魂草》作者江流要我出一趟差,說阜南縣吳兆洛、許春耘、李松崗三人合寫嗨子戲《犟隊長》,在阜陽地區調演獲獎后,受到公安部門的反對與打壓,賴部長(指賴少其,“文革”前任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時任文聯主席、黨組書記)收到三作者寫的人民來信,黨組會上決定受理,派我去做次調查,事關緊急,希望坐飛機盡快前往。我當時在文聯所屬省戲劇家協會工作,以組織劇本創作、學術探討、編輯內刊為業,癡長49歲,已近“知天命”之年,往昔30年文藝界的驚濤駭浪,憑直覺立即感到這份差事的沉重與風險。然而奇怪的是,我竟毫無退縮、畏怯之意,滿口承擔下來。我沒喝蒙汗藥,也不曾吃豹子膽,全因受當時省文聯氛圍使然。眾所周知,歷次政治運動,都拿文藝開刀祭旗,建國以來,諸如批胡適、批胡風、批《清宮秘史》、批《武訓傳》、批《紅樓夢》研究以至反右派、反右傾、文化大革命,中間還有批“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批《三上桃峰》、批《水滸》,甚至批意大利電影導演安東尼奧尼,批到外國去了,等等。文藝界屬重災區,文藝人則是挨整重點對象。安徽省文聯屢屢遭劫,被斗得人散樓空,單位被砸爛,門口被寫上“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的對聯,并久久不準涂沒,出入后院宿舍的老人孩子也蒙受羞辱,尊嚴喪失殆盡。粉碎“四人幫”后,迎來歷史大變革,以萬里為首的安徽省委在決定恢復安徽文聯建制后,又做出《關于堅決推倒“文藝黑線專政”論,為安徽省文聯徹底平反的決定》,宿州路9號(現改為55號)大院上上下下如沐春風,如淋夏雨,作家、藝術家孕積已久的社會責任感和創作激情,像地殼里的火山熔液噴涌而出,伏案難分晝夜。一筆一劃落在方格里、畫面中和音符上,藝術行政工作者也甩開膀子、邁開步子為全省出人才出作品而辛勤耕耘著。那真是“揚眉劍出鞘”的黃金歲月呀!正月初八,哪有什么“節后綜合癥”?星期日照樣工作,哪有“雙份工資”之說?人氣有互動作用,在那種意氣風發的背景下,我能不盡一個“文藝百姓”的公民職責嗎?!
我與王長安同志組成調查組,于2月6日清晨出發,途經阜陽轉車,當晚抵達阜南。在縣招待所投宿甫定,再次閱讀《犟隊長》劇本和作者的人民來信,把戲的內容、雙方糾葛癥結先了然于胸,然后確定應對方法及調查步驟。
盡管劇本還比較粗糙,劇中人物犟隊長堅持因地制宜種花生不惜冒坐牢 “辦學習班”的風險,頂撞下鄉蹲點的縣公安局長強行犁地改種水稻的“瞎指揮”,其維護農業生產自主權和農民人格獨立的立意無可指摘,與全國開展的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的精神正不謀而合。在地區文藝調演中,《犟隊長》獲得創作、演出二等獎,只因劇中被批判人物是公安局長,引起縣公安局某負責人不滿,便通過地區公安局個別負責人疏通地委宣傳部某副部長,擅改調演評議組在大會上所發的成命,將該戲在獲獎名單上除名,并扣發獎金。戲遭停演,作者繼而受到種種非議與責難。
書面上的是非曲直,一看即見分曉,但事實經過究竟如何,公安局方面還有哪些理由或依據還有待聽取與了解。次日早餐,在食堂與新上任不久的縣委書記陸庭植匆匆一見,他每天早出晚歸忙下鄉,我們除作自我介紹表明來意外,便趕往縣公安局開始了這次調查工作。我們認真聽了幾位同志的意見,覺得并沒有新的可站住腳的道理,反證明了作者的人民來信所述情況是屬實的。交談中,公安局主動給了我一份蓋有公章的《送閱材料》,時間是1979年1月4日。原來他們早在一個月前,以縣公安局名義向上級領導分送《送閱材料》并附上《犟隊長》劇本,將三作者列為被告了。《送閱材料》除了用似是而非的說詞和僵化觀點反對以公安局長為戲劇對立面外,就是上綱上線指責作者“鋒芒直指專政機關”、“否定無產階級專政”,“煽動群眾與專政機關對立”、質問作者“用心何在”?一股肅殺之氣撲面而來。一時間,阜南縣城彈丸之地,有說小戲是“毒草”的;有揚言要去“轟場子”(指演小戲的劇場)的,有勸作者“省點事”“認錯”的,還有對作者散布流言蜚語進行人身攻擊的。
回到招待所,院內結有薄冰,空闊房間床被冰冷,我與長安感受到冬去春來卻仍寒意陣陣,不由地頓悟到此次阜南之行不啻是一次破冰之旅。天氣冷、任務艱巨,心理壓力大,加上不合口味的飲食,寢不安神,從公安局訪問歸來的當晚,突然爆發腰病,錐心的疼痛,把我擊倒了。那種一條長水槽、固定時間統一沖水的廁所,蹲不下、起不來,幸有長安悉心照顧,得以堅持未竟調查工作,至今想來仍感懷不已。此后兩天,我們轉向縣委宣傳部、縣文化局、縣文化館走訪十幾位有關負責人和辦事人員,把該戲從彩排審查、獲獎前后變化到禁演的全過程了解得一清二楚,事件的每個環節,包括當事人、經辦者、具體時間、地點都記錄在案,并由當事人出具證明、加蓋單位公章和個人按手指印。各種證據剛接到手,省劇協辦公室來長途,轉達江流詢問調查進展情況,特告北京《文藝報》記者楊天喜也要來安徽調查《犟隊長》事件,江流意見如調查工作順利,楊可不必再奔阜南,留居合肥等你們的歸來。
返程在阜陽滯留一日,將所調查情況簡要地與地委宣傳部兩位部長、地區文化局長分別作了溝通,并表明態度,事件的緣起是對生活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之間的關系,雙方在認知上存在差異,魯迅先生說過:“人物的模特兒也一樣,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角色。”荒唐的“對號入座”,是產生這場糾紛的關鍵所在。溝通過程相當平和、予以認同。
2月13日,賴少其認真聽取我們匯報后,當即責怪我:“書呆子,這是打官司,對手是公安部門,太歲頭上動土哎!沒有當地黨委的意見,完了! ”但當他接過我交上的一大摞證明材料,透過老花鏡逐件過目,遂綻開笑臉當場拍板:“這就行了。文聯有保障作者合法權益、維護藝術民主的義務。”這位外柔內剛的老藝術家,運籌帷幄,發出臨戰號令,要我們以特約記者的名義連夜趕寫調查報告,連同劇本、作者來信和公安局《送閱材料》,出一期《安徽戲劇》增刊,發往全國進行公開討論,在討論中辨明是非、伸張正義。
增刊發出之日,正是全國沐浴十一屆三中全會春風之時。迅疾掀起一陣犟隊長事件熱,阜南三作者每天收到來自全國相關單位或個人的聲援信,有的稱贊他們勇于突破禁區,有的感嘆文藝工作者一向任人宰割,聽人拿捏,今天破天荒打了個翻身仗,省劇協、《安徽戲劇》編輯部也接到支持、評介的文稿。《文藝報》相繼發了楊天喜的文章,連公安部《人民公安》雜志也載文指責一些人的“舊警察老爺作風”,著名美學評論家王朝聞在一次講話中也提及安徽的“犟隊長”事件具有時代進步的意義。始料未及的是,此事件在震動全國的同時也波及海外。1979年初秋,萬里為團長的安徽省代表團抵達美國馬里蘭州訪問,該州州長休斯與之會晤交談中,居然提到犟隊長,并且取出劇本《犟隊長》、特約記者的調查報告以及報刊發表的有關此事件的評論文章等資料匯集。代表團成員之一、阜南縣委書記陸庭植會晤時也在座,引發出一段有趣而活躍的對話。訪問歸來,陸庭植約見三作者,作了如實的傳達。
憶昔貴在益今。阜南三作者在人民來信中云:“民主不是什么人賜予的,必須用斗爭來取得。”小戲恢復獲獎、照常演出,固屬勝利,而贏得藝術民主權利,開文藝史之先河,更具普世價值。北宋王令詩:“子規夜半猶啼血,不信東風喚不回。”三作者以“啼血”抗爭喚回東風,世人當可推而廣之,由藝術進而經濟、政治,均有促進民主的天職,惟有執著“啼血”,不信東風喚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