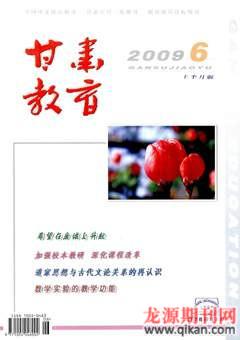道家思想與古代文論關系的再認識
朱炳宇
〔關鍵詞〕 道家思想;古代文論;關系
〔中圖分類號〕 G643.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0463(2009)
06(A)—0054—02
在中國文化史上,老莊的思想及其一系列基本理論范疇,影響中國文化幾千年,至今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它們在成為中國文化元典的同時,也為古代文論的發展提供了重要思想資料。本文力求探討道家思想與中國古代文論之緊密關系,追尋其對中國古代文論的滲透與影響。
一
道家思想體系在中國人的傳統文化心理結構上得到融合與統一,成為兩千年來支配中國人思想的兩大精神支柱之一。道家主張“絕圣棄智”,“致虛極,守靜篤”,“復歸于樸”,崇尚自然,否定人為的藝術。認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家的集大成者莊子繼承老子學說而加以發展,明確表示:“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就是說,既有成,便有虧;唯無成,才無虧。昭文不奏琴,則自然之聲,無意而鳴動,自然而自在,和諧完美;而一奏琴,聲韻既作,便有消歇,而且鼓角則喪商,揮宮則失徵,反倒五音不全,破壞了自然天籟的完美諧和。從這種思想出發,莊子以為語言文字乃是一種粗跡,最高的真理當求之于語言文字之外。他說:“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可見道家所追求的,正是一種超乎言意之表、越乎聲色之上的“自然”、“樸素”之美。
唐代司空圖所謂的“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以及宋代嚴羽的“羚羊掛角,無跡可求”云云,亦不外是“文已盡而意有余”的別樣說法而已。在這里,“文已盡而意有余”或曰“言有盡而意無窮”,與莊子所追求的超乎言意之表、越乎聲色之上的“得魚而忘筌”、“得兔而忘蹄”、“得意而忘言”的觀點,卻又是息息相通的。
應當指出,莊子雖然表面否定文藝,但論其實質,對中國古代文藝及其理論的影響并不亞于孔孟。其文論思想所表現出來的中國藝術精神遠非其語言符號所能詮釋清楚的,并深刻地影響著中國文人的藝術生命和藝術見解。如老莊的“虛靜”說和“有無相生”的觀點,雖說有“無知無欲”、“絕圣棄智”的消極出世的一面,但它更有另一方面的啟示意義,并對后來的文藝創作和理論批評產生巨大影響。莊子云“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這些話語講的都是虛靜和有無的辯證法。正是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后世文論家對道家思想不斷進行著理論上的發揮。如陸機《文賦》:“課虛無而責有,叩寂寞而求音”;劉勰《文心雕龍》:“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司空圖《二十四詩品》:“素處以默,妙機其微”;蘇軾《送參廖師》:“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如此等等,不勝枚舉。
二
中國的文藝理論與西方不同的是,講究“風骨”、“氣韻”,提倡“妙語”,標舉“神韻”、“性靈”和“意境”,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藝理論鏈條。個中原因固然很多,但與道家思想體系的影響密不可分。
“風骨”、“氣韻”之類的概念,原是用以品評人物的。六朝時期由于老莊及佛教思想的普遍影響,社會上對于形、神關系曾有過激烈爭論。受道家重意輕言、重神輕形思想的影響,人們對于放浪形骸之外,不受封建禮法束縛的行為或精神風貌常常給以激賞,講求瀟灑不群、超然自得、無為而無不為的所謂“魏晉風度”。“目送歸鴻,手揮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成為一代風流的楷模。如此之氣韻與風貌,便是當時士大夫階層的審美趣味和理想。反映在文論中,是以“風骨”論文,如劉勰的《文心雕龍·風骨》,要求文章在思想藝術方面具有感動人的力量和挺拔遒勁的文辭,就像鷹隼盤旋于晴空那樣“骨勁而氣猛”。同時又以“氣韻”評說繪畫,如謝赫在《古畫品錄》中要求“氣韻生動”,即繪畫要生動地表現出人的內在精神氣質和格調風度,表現出外物的生機意趣、特色及內涵。在詩論中道家的影響應該說更為明顯。真正以味論詩的首創者鐘嶸認為,詩歌應當“有滋味”,“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韻味”說的倡導者司空圖講:“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豈容易可談哉?”嚴羽《滄浪詩話》則認為,詩的最妙處“瑩澈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所以他主張“詩道亦在妙悟”。以上所言及者,都可以在道家思想中找到根據,可以說其哲學基礎就是道家的“無為”、“無言”和離“形”而得“神”等理論。《滄浪詩話》雖用以禪喻詩的方法論述詩歌的藝術特征,但它在包括老莊藝術精神在內的中國傳統美學中本來就有深廣的思想基礎。所有這些特點,無疑都打著道家思想的烙印。而袁枚的“性靈”說,雖從儒家的“詩言志”說推衍而來,卻與“神韻”說極為相近,同樣重在個性、重在自我,所不同的是“神韻”說抽象而“性靈”說具體。
王國維是中國傳統文論界最后一座豐碑,“境界”說是其文論思想的核心。他對嚴羽、王士禎等人的詩論進行了清理,并在此基礎上作了新的發揮。注意到嚴羽一味地強調作家主觀的“妙語”,過分追求清閑淡遠的情趣和不可捉摸的言外之意,雖顯膚淺,但在反對以理入詩、重視突出詩的藝術特點方面還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王士禎則更加強調“興會神到”,追求作品中含蘊不盡的“韻味”和淡遠之美,進一步把創作引向脫離客觀現實的道路。王國維汲取了嚴羽總結的“言有盡而意無窮”之類的抒情詩歌藝術經驗,但又不像嚴羽、王士禎那樣片面地強調抒發作者的主觀感受而忽視情感的客觀基礎,而是從主、客觀兩方面來揭示“境界”的內容,正如他在《人間詞話》中所說:“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在《元劇之文章》中亦云:“何以謂之有意境?曰: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
目,述事則如其口出是也。”至此,中國古代傳統文論的發展愈臻完滿。
三
同時道家思想也關注到了影響人和社會存在的天人關系。道家強調的是個體“和”于自然,以天合天。道家一貫主張本然之天、天道自然和自然無為,認為那種自然而然、不受人為作用的天然狀態才是天性,才是最完美無缺的。他們認為人的未被社會環境干擾的自然本性才是符合天或天性的,同時它們也能代表天或天性。而對自然本性的擾亂、破壞,則是“人”或人為的,即“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莊子·秋水》)。郭象還進一步闡釋為:“自然而然,則謂之天然?以天有之所以明其自然也。”(《莊子注·齊物論注》)“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認為“人事”理應效法于“天道”;既然“天法自然”,則“人事”也應“自然”。
問題是,這樣做“天”、“人”就能“合一”嗎?莊子曰:“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莊子·大宗師》)莊子的闡述包含“天人相類”和“天人相通”兩層意思。但關于“一”,莊子突出整體性,“道通為一”(《齊物論》)、“天地一氣”(《大宗師》)、“萬物一齊”(《秋水》);而老子則強調動態性,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老子·四十二章》)老、莊的理想追求,都是通過客體與主體之間那種相類通、相感應、相適合、相諧和的特定關系,最終實現“天人合一”。
要實現“真”性,從而與“道”為一,與“天”為一,還要通過“心齋”、“坐忘”,拋棄仁義禮樂,超越是非利害,忘卻耳目心意。“心齋”是什么?即“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莊子·人世間》);“坐忘”,即“墮肢體,黜聰明,離行去知,同于大道。”(《莊子·大宗師》)“心齋”“坐忘”的過程即是忘卻假我、顯現真我的過程,就是與“道”為一、同于大道的過程;與“道”為一即是與“天”為一、與天地萬物合一。莊子是貴己的,他注重人的個體,注重人的內在精神世界和自由本質,崇尚的是超歷史、超道德、超政治的“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境界,突出的是個體自由生命的自在價值。道家特別看重內在的修為,一個人天生怎么樣,就該怎么樣,不要試圖去改變他,只要是天生的、自然的,便是美的。總之,要歸于生命的本然狀態,通過個體自身的和諧來最終實現社會的和諧。并從宗法的倫常形態出發,莊子強調要返回到生命大德的本然,讓生命退出歷史的宗法狀態,從否定宗法倫常到注重生命自然,這是一個否定的過程。
綜上所述,道家思想在塑造中國士大夫階層的審美心理結構和藝術審美理想方面顯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種思想,通過歷代知識分子的融合和相互補充、相互為用,從而為中國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哲學基礎,使得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形成鮮明的民族特色,使之成為人類文化遺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