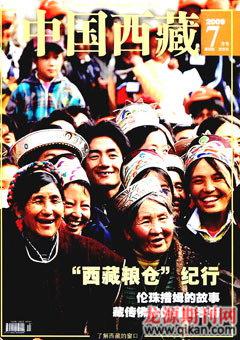大昭寺轉經廊壁畫的人物塑造
項江濤
藏傳佛教繪畫表達的是高原民族對宗教的信仰,是藝術家在繪畫修行中對慈悲清凈性格的流露。穩穩的構圖,靜靜的陳述,沒有藝術夸張的延宕起伏,在一種固定的程式中,體現出藝術與宗教的完美結合,其特有的民族氣質、風俗習慣、思想觀念所創造出的佛教藝術,在佛陀、菩薩、諸天護法、樂伎、天王,以及眷屬民眾形象塑造中均可以窺見其獨特的精神關懷。正如意大利著名藏學家杜齊所言:“西藏藝術真正想做的就是為我們展示神的世界,它的召喚是那樣的生動并使之變得輝煌燦爛。這種關于人類的藝術態度即是一種半透明的冥想或超凡真實的一個世俗復本,它表現了一種奇跡般虔誠的機敏和宗教神學上的復雜事物。”
大昭寺轉經廊壁畫的繪畫風格是17~18世紀的新勉唐風格的延續,一種成熟的藏傳佛教繪畫體系,早期尼泊爾繪畫風格影響已不多見,其主尊居中的棋格式布局已經發展為另一種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格式布局,壁畫的整體構圖更具有連貫性,在對佛本生故事圖組的表現中又顯示出創作者的靈活性,故事情節在畫面中以直線或曲線環形依次展開。以現實的自然景色為背景,融入了對于佛教故事創作的浪漫主義色彩。同時,壁畫的繪制也充分展示了創作者嫻熟的藝術表現技能和對裝飾藝術構圖法則熟練的應用,整體布局的連續性,局部形式間的秩序性,色彩搭配的對比與和諧,人物性格刻畫的神采生動、造型組織疏密、虛實相互襯托,層次分明而有節奏,構圖統一嚴謹,動靜結合、冷暖相宜,繁簡疏密、方圓曲直都在繪畫中有所體現。“化靜為動”、“寓時間于空間”,使壁畫同時具有了時間與空間的雙向延展性。
大昭寺轉經廊佛傳故事的人物刻畫同樣體現了近代寺院壁畫共同特點——
佛的造型特征
大昭寺轉經廊外側壁畫每段中間的主尊佛像都嚴格遵守《繪畫量度經》等繪畫經典,主尊佛像以橘色或金色暈染肌膚,圓臉造型,高髻,大耳不飾環,內著紅色僧裙、系綠色帛帶,外披紅色或橘紅色袈裟、飾以繁華精美的花紋,或露右臂、并于右肩部披袈裟的扇形一角,于身前翻露出袈裟的墨綠色、藍綠色或粉綠色等不同綠灰色調的里襯,結跏趺坐,以紅色暈染掌心,并于掌心內繪制金色法輪,手印有說法印、鎮地印、定心印、施愿定心印、三摩地印、說法定心印、施愿印等。關于主尊佛像類似的著裝特點,學者張亞莎在論述《扎塘寺壁畫的人物造型》一文中曾有這樣的論述:“釋迦牟尼內著寬袖衫,外罩紅色袈裟,左肩通肩而右肩僅披袈裟的一扇形角,使右臂與右邊胸部的內衫衣飾能夠從包著的袈裟中顯露出來,這種服飾和這種穿著習俗,無論是藏傳佛教,還是漢傳佛教的佛像傳統,都是很難見到的,這種服飾原本也并非釋迦牟尼所專有,它實際上是漢傳佛教中流行的一種僧人服飾,是高僧們平時的穿著打扮,不過穿在佛陀身上的這身僧服,質地更精良,服飾圖案更精美,衣裳的邊繡更為華麗而已。”故事情節中的佛祖造型特點與主尊造像著裝大體相同,披袈裟多袒露右肩,肌膚均施金色,坐像莊嚴,手結各式手印,有背光,立像則上有華蓋。
佛弟子(僧人)的造型特點
佛弟子(僧人)僧袍著裝樣式與佛祖相同,只是華麗不足,平頭,偶有佩戴紅色僧帽者,跣足。內外服飾以橘紅和絳紅區別,以金色繪制簡單的團形紋飾,并以紋樣的疏密、繁簡來區分內外層次。人體比例上雙臂大都有拉長的感覺。在僧人的裝束中以披紅色袈裟為主,在北壁集中于第五段有著黃色袈裟者。大昭寺轉經廊壁畫雖是關于佛本生的題材描繪,在壁畫中仍然有藏傳佛教不同教派弟子的形象描繪。
世俗人物裝各不同
故事中以王統身份出現的人物其重要的標志是均配有綠色的頭光(有的還有身光),居于室內,多坐像,并有裝點華麗的寶座,著裝上有著明顯的身份等級的區別,華麗的錦緞,或為吐蕃貴族服飾,又有波斯風尚。頭纏巾或戴花冠,耳飾大環,長袍系腰帶,長褲,著鉤尖革履,外罩廣袖長袍,項戴瓔珞,帛帶飄逸,有時亦用金色作為膚色:作為佛陀宿世中的普通人物形象以佩戴金色的寶冠為標示。
畫中婆羅門的服飾為白色披肩,袒露上身,頭發以環形盤于上方或上部束發散于腦后,面部多以長形或側面形象出現。
梵天、帝釋及各類天女的服飾類似于早期的“波羅”式服飾特征,束高髻,戴寶冠,耳飾大環,上身袒露,下著長裙,佩項圈瓔珞,肩披帛帶,臂戴華麗的釧、鐲。南壁“太子降生”的情節中摩耶夫人的造像也為此類裝束。
普通平民衣著質地有著明顯的不同,裝飾簡單,多身著短袍,系腰帶或短裙,下著長褲,多穿長靴,短發或系白色、青色頭巾,衣服顏色以棕色、綠色、藍色等色彩為主,袖口與衣襟的邊飾不用紅色或橘色,這源于藏族傳統中的紅色為尊的用色習慣。普通女性長發結辮,成“人”字形分搭于肩部,中間挽一頂髻,以漂亮的花飾點綴。
士兵服裝:士兵裝配長矛、腰刀等,頭盔上裝飾紅纓,其甲衣更似大昭寺主殿內的漢地將軍的塑像。
刻畫人物神態以強化主題
主尊造像面相圓潤飽滿,雙眼細長,薄唇微翹略帶笑容,神態安詳典雅,俯視蕓蕓眾生:在故事情節中的刻畫也是超凡脫俗,展示了佛祖的慈悲為懷。弟子僧人簇擁于佛陀身邊,或仰首傾聽,或低眉冥想,神態虔誠恭敬、專注認真。女眷刻畫嫻靜、典雅而高貴,其他人物刻畫也都各有不同。人物的性格通過面部五官細致入微的變化來體現,猙獰的惡道、心懷詭計者、爭強好勝者,在畫面中都有不同的體現,如眼睛:弓形、細長型、圓型、魚肚白等賦予了不同的性格特征,丹巴繞旦先生在《西藏美術》中曾解釋西藏繪畫藝術中對于眼睛的造型為“眾佛的眼睛似弓形,善怒皆非或憤怒,仙人的眼睛似海貝型或蓮花瓣,和善佛母之眼睛似魚腹,娼妓的眼睛似竹弓形,大怒的眼睛似長圓型等”,畫面中人物間的性格對比表現的生動而準確。
壁畫中更注重借助真實場景的描繪來表現主題,如“飼虎圖”,類似題材的表現,在其他寺院中多以諸天的降臨來烘托極樂世界的到達,而在大昭寺轉經廊壁畫中,畫面雖然是血腥場面的表現,幾只老虎略顯饑餓和急切,但畫中人物體態的飽滿、柔軟抬起的右臂、安靜的猶如熟睡的神態刻畫與之形成對比,更能體現出佛教宣揚的慈悲、因果報應的思想。其甘愿犧牲、毫無怨言的神態刻畫,正如于乃昌先生所言:“產生于宣傳佛教教義思想需要的古代藏族壁畫,從藝術的角度來看,作為審美的對象,一個顯著的特征,就是對富有人性的人物形象的精心刻畫,即使是描寫神佛形象的作品,也處處流露著現實的蕓蕓眾生的風采。”
總的來說,大昭寺轉經廊壁畫的人物造像形式有以下特征:
服飾紋樣的裝飾以中心佛像的服飾裝飾最為華麗,紋樣繁多而精細,如青蓮花、紫檀花、薩達花、菩提葉、金翅鳥蓮花、寶劍、金剛杵、吉祥結、壽字符、祥云等等,僧人等人物的衣飾多以簡單的團花、圓點、方格、短線代替,地位低下者服飾花紋尤為簡略。
不同時代的人物和諧的組合在同一畫面中,打破了時空的阻隔,并且完美糅合了漢、藏兩地的風俗特征,甚至還延續了早期的尼泊爾繪畫藝術的特點,畫面很大程度上展現了當時的現實社會風貌。
服飾是畫面人物等級區分的標志之一;在身相比例上也有明顯的差別:尊者的比例明顯的夸大,且多以正面形象出現。
在形象塑造上,以中央主尊造像更為精細,但是故事中的人物塑造更顯生動、靈活,這在一向以量度經為摹本的西藏繪畫中是極為難得的。
造型獨特的“飛僧”
“飛僧”的形象在轉經廊壁畫中的體現,只是作為畫面內容需要而出現的。或在藍色蒼穹的背景中,不設云彩作依托,簡單自然,只以身體形象的造型表示佛偕同梵天等眾仙的“從天而降”:或借鑒了“傳統飛天”的造型藝術特點,身體平展,伸開雙臂,手拈袈裟一角作飛翔。其區別于敦煌飛天的“輕歌曼舞”,在壁畫中的作用更多的是“內容大于形式的需要”。“飛動之美”是構成華夏藝術基本特征的元素之一,但在西藏繪畫中身著絳紅色的袈裟的“飛僧”形象出現,背景或是天地蒼穹或是遠山碧樹、澄湖閃爍,有著西藏藝術獨特的表現。正如王堯先生所言:“以藏族藝術中特有的民族氣質、風俗習慣、思想觀念來統馭或運載佛教,諸天護法、天王、伎樂及至眷屬都可發現藏族的民族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