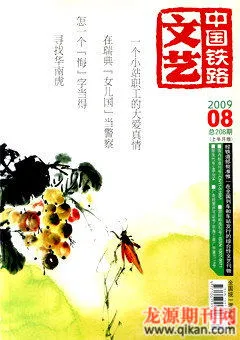母愛四題
金 翔
經過這些年來的努力拼搏,我雖算不上這座城市里先富起來的群體,但作為身為人父的我,該有的也就有了,也就沒有多少所謂的追求了;惟一的愿望就是將在鄉下為我勞累了大半輩子的母親接到身邊,好好地盡一盡做兒子的孝心。
這個愿望終于在今年春天實現了。然而,在鄉下愛說愛笑的母親進城之后就變了個人,一整天像尊泥菩薩一般坐著,沒有表情,沒有言語,還三天兩頭說要回家。每次我都像哄孩子一般把她留下來。最后一次母親說得很堅決,怎么也不肯在城里住下去了。母親在鄉下累了大半輩子,進城還沒享幾天福又要回老家,我心里很難受。我近乎哀求地問母親:“媽!城里哪點不好,你就給娃直說吧。”母親臉上勉強擠出一絲笑容:“娃。媽也沒覺出哪不好,可心里總是堵得慌,還是在鄉下種畝地養頭豬舒坦、自在。”于是我隨口道:“媽,只要你能留下來,我就買頭小豬讓你養!”“娃你要是滿足媽的這個愿望,媽就不走了!”母親的話著實把我嚇了一大跳:我這三室一廳的住房怎么養豬,怎么會是養豬的地方呢?!要知道,我之所以那樣說,無非是想讓母親明白我留她的一片苦心罷了。但是,當我看見母親進城后第一次笑得這樣開心,這樣真實,我那憋了半天的“不”字,最終沒有說出來。
豬娃買回來了,一頭純白的下洋豬,粉紅色的鼻子一翕一翕地抽動,一雙黑眼睛溜溜地閃著賊光,母親把它抱在懷里,笑了又看,看了又笑,同抱小時候的我一個模樣。于是小兒的房間給騰出來了,因為豬娃的入住,他以后只能“遷移”到我和妻子的床上過夜了;看著鳩占鵲巢的豬娃歡快地在自己的房間里上躥下跳,小兒抱著我的腿眼淚直流……面對這一切,惟一讓我欣慰的是:好在妻是嫻妻,諒解我的難處,否則后院非得起火不可!
母親每天步行七八里去郊外農民的田里割豬草。我們在看電視的時候,母親在廚房為她的豬娃煮豬食。一閑下來,母親總要喜滋滋地說上幾句她的豬娃如何地乖如何地肯吃肯長、愛干凈,也不管她的孫子嘴巴翹得有多高。將母親的這一切看在眼里,我心里酸酸的。
在西方。據說小豬是寵物,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并未愛上這頭可愛的小畜生,自小豬住進來、妻再沒有帶朋友回來,她怕;小兒對小豬的目光一直是狠狠的。不管我們怎么不喜歡,小豬在保姆般的母親調教下,還算不壞——只要吃飽了,決不胡亂哼哼;大小便也能在母親指定的地方如槽入坑,加上母親隔三差五地為它洗澡,家里也沒有一點飼養場的味道,以至這棟樓的人們一直不知道我家在養豬。
城市終究是不適宜養豬的,人獸間的平和還是被打破了。一夜,已成“二八少女”的小豬無法抗拒本能的驅使,嗷嗷地叫起來不肯停下,三天后才歸于平靜。除了母親,那些天一家人都是捂著耳朵過來的。而我和妻還要賠著笑臉應付因不堪攪擾而興師動眾上門的左鄰右舍。事情如此糟糕,我必須找母親談談。然而,我剛開口說出一個“豬”字,母親就興沖沖搶過去說:“是呀,豬娃可以配種了,年底又是一窩豬娃。娃,你忘了吧,你升學那年,正好咱們家一窩豬娃趕上了好價錢,要不,你的學費還真難住了我和你爸呢……”我不愿把母親傷害得很直接,只能由遠及近,由淺入深地講道理。一大堆話時隱時現地藏著一個母親最不愿接受的事實:家里那頭豬留不得了!母親的臉色漸漸的變得難看了,甚至有些凄然。末了,母親說:“娃呀,別說了,都怪媽不曉事,媽知道你孝順,你想讓媽來城里過幾天好日子,可是娃你哪里知道,媽種了一輩子地,養了一輩子豬,猛一到城里,娘看不到地看不到豬就好像沒了主心骨。”我流淚了。我知道我再也留不住母親了。
兩天后,我租了一輛車子,將那頭豬裝進一只透氣的口袋,把母親和她的那頭豬一起送走了;母親離開城市沒有一點難過的樣子,倒是顯得放松了許多。而我卻為自己難盡的所謂孝心,淚流滿面……
母親的電話
幫朋友忙完他母親的喪事,那晚我回到家后,禁不住地給在老家鄉下的母親打了一個電話,電話剛一撥通,手機里立即傳來了母親的聲音——這足以表明她老人家還未睡,至少說還未睡著。而其時已是凌晨一時多了!
其實,對母親的這種認識,可以追溯到我的童年時代——
最初的記憶——我想也是我們這代人幾乎都有的記憶,兒時的我每晚睡在被窩里,母親挑一盞油燈給我納鞋底、補衣服;時常是我一覺醒來,揉一揉惺忪的睡眼,看見母親還在微弱的燈光下做著,“媽,睡吧”我叫了一聲,母親走過來一邊輕輕地拍著我一邊說:睡吧,媽待一會兒就睡。于是我又進入了甜甜的夢鄉……現在想來,很是慚愧——我從不知道母親的“待一會兒”具體是多長的時間?!
記憶最深的是我上中學時,在那個沒有鐘表的年月里,為了掌握我上學的時間,母親用的是山村人計時的土辦法:每天公雞叫的第三遍,就是臨近天亮。因離校較遠,需要翻越幾道山梁才能抵達鄉里那所中學;每天公雞鳴叫第二遍到第三遍之間,便是我上學起床的時間。因此,每天雞叫過第二遍,已為我做好了早飯的母親,就開始掐算著叫醒我起床時刻——早了,她心疼兒子的瞌睡;晚了,又擔心兒子遲到挨批評。——什么是母愛?這就是母愛!又怕兒子睡,又想讓兒子睡。母親為我而未睡過安心覺!
后來參加了工作,投入到激烈而無情的競爭與應酬之中,從對母親隔三差五的書信問候,變成一月、兩月都提不起筆。再后來,從不對我提任何要求的母親卻讓我給家里安裝一部電話,她說她有時夜里睡不著很想聽一聽我的聲音。這時我才感知到自己忽略了母親對我的牽掛與思念。而電話裝好后。母親卻很少撥通兒子那為了業務連夜里都未關掉的手機,她說她怕打攪兒子的工作和休息。
前不久,我趁出差順道回去看望母親。到家時,六十多歲的母親高興極了,一如兒時過年的我——其時,我才真正體味到一位作家說過的一句話:兒女回家的日子,就是父母的節日!母親叫我去床上躺一躺,好好休息一下,自己忙著到廚房為我準備飯菜——母親把我倒視為了客人了!于是無聊的我坐在母親的床邊,隨意地翻看著儲存的內容——我給母親的電話開通了來電顯現;當我翻到“已撥欄”時,呆住了:因為我看到一連串未撥完的相同的號碼——我的手機號碼——有的甚至已撥得只差最后一個數字了——而撥打的時間大都是凌晨一兩時了!這樣的時候我在做什么呢?不是陪人泡在酒吧里,就是躺在床上酣然入夢。這時我才感知:我是一只從母親心里飛出的永遠長不大的鳥兒,愫愫情懷仍捏在她的心里:我飛得越高越遠,母親心里那根叫牽掛和思念的弦,就會繃得越緊越揪心,使她徹夜難眠!我的眼淚一下子流了出來……
母親是我的經紀人
寫下這個有點新潮意味的題目,我既不是歌星影星,也不是大款富商,但作為一個普通工人來說,卻毫無矯情、偽飾可言,因為,這是我內心真實而強烈的自然流露——切合我的心境;對母親的這種認識,可追溯到我的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