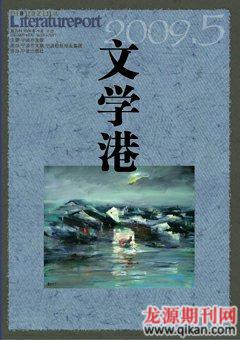折翼天使
劉 嬪
細雨漸漸打濕我的臉,我已分不清是淚水還是雨水。撫摸冰冷的墓碑,你在那里還好嗎?我回來了。
四年了,我依舊找不回那雙屬于我的翅膀。腦海中殘破不堪的記憶碎片一瞬間拼湊成了一幅完整的畫。
小米經常說,我們倆是折翼的天使,需要相互取暖,才會飛得更高。好多時候,我都不明白,為什么她會如此消極,但有時候,又不得不覺得她有我們這些同齡人所沒有的成熟。
小米的父母經常吵架,有一次甚至驚動了鄰居,當我躲在母親身后看熱鬧時,小米正躲在鞋柜旁,瑟瑟發抖,一雙空洞的眼睛望向窗外。從沒有見過這樣的小米,好陌生,不敢靠近,那年,小米十歲,我十歲。
父親迷上賭博,母親不能忍受家庭暴力,離家出走。從此,小米沒有了笑容,眼神迷離。有幾次,我看到小米的父親喝醉了酒,對小米一陣暴打,小米也不反抗,仿佛自己的身體和靈魂是分離的。我總覺得她在心中打算著什么,直到那一天,小米興沖沖地跑來告訴我:“水水,我要走了,我要去找我的媽媽。”那時的小米,笑得十分燦爛。那笑容像花一樣印在我的腦海中,一年又一年,她找到她的媽媽了嗎?
后來,我們搬了家,從同學和朋友的口中收取關于她的零碎信息。
她找到了媽媽,但是媽媽卻另嫁他人,還有了另一個小孩——她的弟弟。對于一個外來者,每個人都有心理防線,兩個小孩都在那時認為對方是剝奪自己幸福的罪魁禍首,于是互相看不順眼。有一次,弟弟摔倒了,冤枉小米推他,繼父不由分說,上來就是一拳,小米鼻子上又開出了一朵朵鮮紅的花朵。那年,小米十八歲,我十八歲。
2004年的時候,我拿到國外大學的通知書,星期天的早上,我從派出所出來,拿著手中的通知書和簽證,心想,明天就可以去美國了,開始新的學習生活。仿佛街上的行人都投來羨慕的眼光。這時,我發現不遠處的鐵門口,站著一個濃妝艷抹的女孩,旁邊的女警還在說著什么,可是,她十分的不厭煩。是小米!她也認出了我,先是一驚,但分明在她的眼中看出了喜悅。劣質的香水,夸張的耳飾,嘴里不斷咀嚼的檳榔,無一不與現在社會上的混混畫上等號。小米拉著我走出了大門,身后傳來女警的聲音,“下次別來了,進警察局像吃飯一樣。”
幾句陌生的客套話之后,小米拉著我走進一家酒吧,那是我第一次進酒吧!昏暗的燈光,奇形怪狀的人,嘈雜的聲音,與我顯得是那么格格不入,而小米卻熟門熟路地拉著我徑直走到吧臺,叫了一杯“藍色火焰”,點上一支煙,最后還是小米打破了沉默:“怎么,不習慣這里?”
我笑了笑:“還好,就是有點陌生。”
小米:“那是,你們這些好學生可是很排斥這里的。”
我沉默了,不知道如何回答,小米曾經是一個多么乖巧的小姑娘,而現在……
小米打破了沉默:“你怎么樣啊,去派出所干嘛?”
“哦,明天要去美國了,去派出所拿簽證。”
“挺好的,果然和我們不一樣啊!”小米再一次點上一根煙。
“你呢,怎么樣啊?”
小米喝了口啤酒,眼神暗了下來,“也就這樣吧,混日子,你也看到了,進局子像吃飯。”
我剛想說什么,卻被煙嗆到了,小米立馬掐掉煙。空氣里出現了一絲凝滯。
“你媽媽怎么樣了?”我想換個話題會好一點。
“不知道,很久沒有聯系了,都不記得長什么樣了。”
空氣再一次凝結,我想很快地結束這次十分沉重的談話,小米仿佛也感覺到了,于是,把我送出了酒吧,正在門口道別時,我看到一輛銀色轎車飛快地從巷子一端行駛過來,而另一端,則傳來女人的尖叫:“寶貝!危險!”尋聲望去,一個小孩正慢慢地往巷子中間走。
握著手中的簽證,我猶豫了,而小米則沖到了巷子中央,小孩得救了,而她被車子撞飛了,劃出一道美麗的弧線。路人越圍越多,我站在原地。忽然想起小米的那句話“我們倆都是折翼的天使。”
小米,找到了她的那只斷翅,而我卻永遠失去了飛翔的勇氣。那年,小米20歲,永遠停止的20歲。我也20歲。
第二天,坐在候機室里,一同去美國的朋友興奮地告訴我,“水水,我們上報了”,看到報紙上面醒目得寫著一行大字:我市5名畢業生,今日飛赴美國。而此時,我也注意到,報紙的右下角,很不顯眼的位置寫著:“昨天下午我市老實巷發生一起車禍,一女青年為了救小男孩,不幸喪身。”
這時,廣播傳來甜美的聲音:“搭乘T9089航班的乘客,請到2號登記口登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