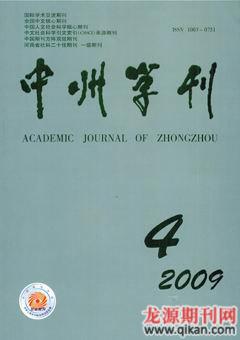略論清代北方鄉約行政組織化的消極影響
段自成
摘 要:清代北方鄉約行政組織化后,鄉約首事逐漸官役化,這不僅導致鄉約教化職能的弱化,而且使鄉約的鄉村自治地位開始動搖,鄉約逐漸淪為聽命于官府的基層行政組織。所有這些反映了清代北方鄉約性質的變化,也說明清代北方鄉約行政組織化并不能使清代的鄉村政治真正得到改善。
關鍵詞:清朝鄉約;行政組織化;鄉村自治
中圖分類號:K2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09)04—0171—04
清代北方鄉約行政組織化的影響問題是清代鄉約研究的重要課題,研究這一課題對于我們全面地評價清代北方鄉約的行政組織化,正確地認識清代鄉約的性質以及深入地了解清代北方的鄉村政治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然而,史學界迄今尚缺乏這方面的研究。有鑒于此,本文試圖通過研究清代北方鄉約行政組織化的消極影響,探討清代北方鄉約性質的變化與鄉約行政組織化的關系,以總結清代北方鄉約行政組織化的歷史教訓。
鄉約的行政組織化導致鄉約教化功能的嚴重削弱
順治年間,北方地區就設置鄉約,負責朔望講讀圣諭。鄉約教化曾是清代北方基層教化的重要形式,但隨著鄉約的行政組織化,鄉約的教化職能普遍削弱。其所以如此,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伴隨著鄉約行政組織化而出現的鄉約長官役化,使清代北方鄉約首事的素質難以保證,從而嚴重影響了鄉約教化的效果。鄉約首事本應由未出仕的士人或殷實而有學行者擔任,但鄉約長官役化后,任重役苦,受到鄙視,有身份的人不愿充當,鄉約首事的素質和地位普遍降低。比如,康熙年間的地方官于成龍曾說:“年高有德鄙為奴隸,殷實富家視為畏途,或情或賄,百計營脫,而寡廉喪恥之窮棍兜攬充役。”①乾隆年間,陜西巡撫張楷也說:鄉約長被“視為賤役,致老成、公正之人避不肯當,所選多不得人”②。由于鄉約首事的素質和地位下降,清代北方鄉約教化的效果大受影響。于成龍在《慎選鄉約論》中說“寡廉喪恥之窮棍兜攬充役”后,鄉約“錮習不可救藥,欲端風化、靖地方,不同癡人說夢乎”。清人張望在《鄉治》中說:鄉約長“亦窺上之以無恥待也,眾之所謂下流而居之,雖欲潔清不污不得也,遂盡從而棄之,上之人又孰從而信之?不惟上之人不信而已,即以己之不善而教人善,以己之惡而謂人惡,平居譊譊,其誰信而服之乎”③。晚清人黃璟也說:“向充鄉約、保正等輩,率皆視為賤役,只可供奔走勾攝詞訟人證,催征錢漕,不能期其正己以正人也。”④由此看來,清代北方鄉約首事素質的下降確實影響很大,它大大削弱了鄉約的教化功能。
第二,清代北方鄉約行政組織化后,鄉約長普遍陷于事務性工作而無力過問教化,也是導致清代鄉約教化衰落的重要原因。康熙年間的地方官于成龍曾描述了鄉約首事官役化后的真實情況,他說:鄉約內“一事未結,復興一事”,致使鄉約長“終朝候訊,遷延時日,無歸家之期。離縣近者,猶可朝來暮去。其遠在百里外者,即以點卯論,兩日到縣,一日點卯,再兩日歸家,是半月內在家不過十日。加以協拏人犯、清理區保,手忙足亂,無一寧晷……彼鄉約曾未家居,何由而勸人為善去惡”。⑤鄉約首事官役化后無力過問教化的情況在清朝絕對不是個別現象。清人李義卿談及清代鄉約的弊端時說:“人徒見吏胥、約保之奔馳,門牌、冊籍之更疊,出役應差之勞,什伍連坐之患,而曾不聞衛、養、教、利之政。”⑥道光《陽曲縣志》記載:“邇來六言不講,為鄉約者,僅効奔走供使令而已……訓諭之宣講無聞,在昔培風化俗之良法蕩然無存,非一朝一夕之故矣。”⑦民國《洛寧縣志》也記載:“今之所謂鄉之約者,又非有教化之任與夫鄉飲讀約之禮者也。”⑧由此可見,清代鄉約長忙于辦理公務,難以兼顧教化,使鄉約教化失去了至關重要的時間保證。
第三,清代北方鄉約行政組織化后,鄉約首事以外為講約服務的各種約職普遍被裁減,對鄉約教化的影響也很大。本來除了首事鄉約長外,鄉約內還設有約講、約史或直(值)月,甚至有的鄉約還設有約鐸、約贊等職。鄉約行政組織化后,以講讀圣諭為職責的約講、直(值)月,以記善記惡為職責的約史,以及以掌管講約司儀為職的約鐸、約贊,普遍不再設置,只設首事成為各地鄉約普遍的組織形式。北方內地不少地方雖然仍有鄉約朔望講讀圣諭之制,但講讀圣諭已由專業的宣講人員負責,鄉約內部并不另設講職和司儀。比如,史料記載:雍正二年,“頒發《圣諭廣訓》萬言,吏部行文各省督撫,令教授、教諭、訓導等官,遴選生員中有品行、文學者,句詮字解,闡發宣講……毋得以鄉約、耆老輩偶爾談說虛應故事”⑨。在東北地區,鄉約朔望普遍不講讀圣諭,設置講職和司儀的例子十分罕見。少數民族地區的鄉約也普遍只設首事。筆者迄今沒有見到有關新疆各少數民族鄉約、西北地區回族鄉約設置講職和司儀的例子。鄉約只設首事,說明鄉約行政組織化后其傳統的組織形式已發生明顯變化,鄉約朔望講讀圣諭之制已失去了組織保證。
鄉約行政組織化使清代北方鄉約的教化功能嚴重削弱,表明鄉約原本作為教化組織的性質正在改變,鄉約在基層社會組織中的傳統優勢已經喪失。
鄉約的行政組織化導致鄉約首事官役作風的出現
隨著清代北方鄉約的行政組織化,鄉約首事逐漸淪為在鄉官役,鄉約作為鄉村自治組織的地位發生動搖。清末東三省總督徐世昌就說:“今之鄉約,勒派地方之財,供應地方之官差,習慣上充地保者也,不得與自治團體同年而語。”⑩在鄉約的鄉村自治性質改變之后,鄉約首事在辦理鄉村自治事宜和基層行政管理事務時往往表現出官役作風,其對鄉村政治的危害也明顯暴露出來,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鄉約首事普遍借端科派的現象出現了。鄉約行政組織化后,由于鄉約長普遍沒有固定的津貼,遇事攤派不可避免。比如,在東北的安東縣,每牌各置鄉約、保正一名,“地方有事,或官府令行諸事,皆由鄉保集會招集首事諸人或各住戶定期開議。每次必費款若干,年終總計一歲之所費,皆由地畝攤派”(11)。《寧城縣志》記載:清代當地“每鄉置鄉約一名,總理全鄉事務……其所有費用,悉根據地畝,由地方攤斂之”(12)。民國《萊陽縣志》記載:“社、甲約輪差,各社、甲均有補助,或以粟米,或貼差地畝錢文,或其他收入。”(13)隨著鄉約長在官役化后素質的下降,鄉約在攤派支出時借端勒索的現象十分普遍。比如,臨江縣“每年由花戶納之于鄉約者……三倍于正供”(14)。《吉林行省賓州府政書》記載:“本廳鄉約于每年春秋兩季潑牌兩次,少者每坰抽錢四五百文,多者一吊有余。此就人人所知者而言,其他項勒索,尚不在此數……若輩人格太低,以侵蝕公款為長技,以調唆是非為得計,甚或構人興訟,抑且開場聚賭。但可分肥者,無所不為。”(15)雍正年間,河南巡撫田文鏡述及鄉約稽查賭博情況時說:“鄉約、地方,逐處抽取規例,規例到手,不但不查拿解究,抑且徇隱出結。”(16)這些例子說明,鄉約借端科派的現象在清代北方鄉約行政組織化后相當嚴重。
其次,鄉約長和吏役勾結害民的現象趨于普遍化。鄉約的行政組織化為鄉約長和吏役的勾結害民提供了機會。約長和吏役的勾結突出表現在利用訴訟勒索原告和被告方面。乾隆年間,監察御史王柯奏稱:鄉約長“在官則為蠹吏、滑胥之爪牙,在鄉則為訟徒、奸棍之羽翼……其弊有不可勝言者”(17)。在陜西洋縣,“凡遇詞訟,原差傳喚動輒六人,甚至九人、十二人,與鄉約串通舞弊,往往草鞋錢數串,口案錢數十串,官號錢多者甚至八九十串,少者亦不下三四十串……凡居鄉在山鄉約,遇差役持票叫人,必協同傳喚。一經傳到,先說草鞋錢,次講飯館酒肉,動稱口案錢若干,以少報多,鄉約均行分肥”(18)。鄉約長串通吏役勒索民眾,也是催科中的常見現象。左宗棠記載:北五省及關內外各州縣在賦稅和陋規征派中,“丁役取其一,而承差頭人、鄉約、里正又倍之。層累既多,中飽無厭”(19)。在編甲稽查事務中同樣存在鄉約與吏役勾結害民的情況。康熙年間的地方官于成龍說:“寡廉喪恥之窮棍兜攬充役,串通衙捕,魚肉煙民,以編甲漏造為生意,以投呈證佐為活計,惟恐地方之不生事也,居民之不興訟也,差役之不來照顧,官府之不來呼喚也。”(20)乾隆年間,大學士鄂爾泰曾說:編查保甲時,吏胥“需索多端……重則入室搜查,生端挾詐;輕則冊費、路費,坐索無休。至斂錢之鄉保人等就中分肥,皆勢所不免”(21)。由此可知,鄉約首事勾結吏役害民的情況已經滲透到州縣行政的方方面面,成為鄉約害民的重要方式之一。
最后,鄉約首事與官員勾結害民的現象也出現了。新疆鄉約首事與官吏勾結害民的情況最為典型。新疆巡撫袁大化曾說:“鄉約借通情事,往往假借官吏,魚肉其眾,此外別無所長。”(22)民國的吳藹宸也說:新疆“鄉約人多品雜,往往與貪官污吏朋比為奸,倚勢欺凌,民間無如之何”(23)。清代北方其他地方鄉約與官員勾結害民的情況雖然沒有新疆嚴重,但也時有發生。比如,《黑龍江將軍衙門檔》記載:巴彥蘇蘇“丈地委員與鄉約勾串,苛派奇出,索要毗連以及廚夫各項雜用錢文”(24)。在阿拉楚喀副都統衙門轄區,“田界官串通鄉約,按戶硬潑小租錢項”(25)。嘉慶年間,直隸承德府豐寧縣郭家屯巡檢李鴻光奉命派夫辦差,鄉約楊玉聲、馬遂等“向各牌頭斂錢到巡檢衙門打點減夫,冀圖得利分用”,“楊玉聲等許送規禮銀三十六兩”,李鴻光遂“將楊玉聲等請減緣由到縣面稟,代為請減”。(26)可見,鄉約與官員勾結,在一些地方也成為鄉約害民的重要方式。
清代北方鄉約行政組織化對鄉村政治的這些危害表明,官役化的鄉約長與里長、老人和保甲長一樣,已經成為害民之役,這反過來又進一步說明清代北方鄉約已經徹底改變了其傳統的鄉村自治性質。
鄉約的行政組織化使鄉約淪為聽命于官府的基層行政組織
清代北方鄉約的行政組織化,改變了鄉約組織的性質,勢必要打破鄉約與官府原有的權力分配結構,從而引起鄉約與官府關系的新變化。
鄉約行政組織化后,其行政管理職能明顯擴大,而清廷沒有及時對鄉約和官府的權力劃分做出統一規劃,從而形成北方一些鄉約把持鄉政的局面。比如,在陜西洋縣,鄉約“遇有形跡可疑之事,使人具售狀……動輒罰錢數串或數十串文。無錢者折給地畝,鄉約自行收租”(27)。在陜西澄城,“如有違反禁約,而又恃強不遵罰規,官中公制木棍兩條,鄉約、公直依法重懲”(28)。在邊疆地區,鄉約的權力更大。比如,新疆呼圖壁地區流傳著這樣的民謠:“文官宰相武官侯,戶兒家的鄉約大到天里頭。”(29)民國初年,新疆首任省長楊增新曾說:“南疆各屬鄉約,沿前清伯克余習,勢力最大,積弊最深,竟有充當鄉約終身或至二三十年之久者。即或因事被革,迨經換官,不難營謀復充,以故屢仆屢興。人民受其殘虐,無不忍氣吞聲,不敢與較。官吏之不敢肆于民者,鄉約乃敢肆之;官吏之不敢侮于民者,鄉約乃敢侮之。”(30)與新疆鄉約相比,東北鄉約把持鄉政的情況,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賓州鄉約舉辦團練,按坰收款,“其苛斂之巨,一坰地有攤派中錢二三百吊至四五百吊者。出錢稍遲,練勇即將攤戶鎖禁會房,私刑拷掠。故小民之畏練會,大甚官署……并擅受民詞,拿賭勒霸,兇暴如虎……其會房門亦懸虎頭牌,立軍棍焉”(31)。盡管清代北方各地鄉約權力的大小不盡相同,但在完成了鄉約行政組織化的地方,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著鄉約把持鄉政的情況。
鄉約把持鄉政,使北方一些地方鄉約權力和官府權力的矛盾激化,鄉約與官府公開對立的情況隨之出現。清末人傅疆在《查勘臨江報告書》中指出:東北鄉約行政組織化后,“黠悍無賴之徒,遂把持地面,與官分治”,“鄉約乃分東省數百年政治之席,直接臨民,置地方官于間接地位,為鄉約之傀儡”。(32)在東北奉化縣,“鄉約、地保之役,往往權傾縣令,擅作威福”,以致“鄉愚呼鄉約為老爺”,民間流傳著“些小事村三家,鄉約老爺威坐衙。聞得縣官來,老爺昨被拏”的民謠。(33)民國初年的新疆省長楊增新說:新疆的“地方官來去無常,鄉約則不常更換,是以百姓畏懼鄉約較官為甚。其尤者,地方實權一操其手,即地方官亦且莫可如何”(34)。《樊山判牘》記載:陜西某縣電陽里幾位生員商定:“凡里民因事結訟者,先須投明保約,不投保約而具控者,公同議罰。”而知縣樊增祥認為:“保約無非鄉里小民,小心畏事者必不肯充,既肯充亦不能了事;至小有才者,其居心未必公正,臨財無不茍得,若更假以聽訟之權,非徇情即謀利,非附勢即逞能,是非何自而明,剖斷安得得當?”因此他命令官“役迅將具稟之文武生員十人,一齊傳案……聽候訓責”。(35)這些例子生動地說明,在鄉約行政組織化后,清代北方鄉約與官府的矛盾確實存在,而且有些地方還相當嚴重。
為了緩和官府和鄉約的矛盾,清代北方一些地方官力圖限制膨脹的鄉約權力。比如,針對鄉約長把持詞訟,陜西洋縣一位知縣說:“刑罰操自官長,非小民所能自專……嗣后鄉約每人只準說事,不得動接售狀。竊案大者,隨時稟官;小者鄉間議罰,只準四五百錢文。如有過一串者,告發后以詐贓究辦。”(36)與此同時,清代各地官府還普遍采取了一些措施,以調整鄉約和官府的關系。一是北方內地不少地方要求鄉約首事朔望到官府應卯。比如,晚清地方官吳文镕說:“每月朔望,循例鄉約點卯。”(37)官府要求鄉約首事參加朔望點卯,有對鄉約長“稽勤惰、功過”(38)之意,目的是為了加強對鄉約的管理。二是官府普遍將鄉約的任免權掌握在自己手中。《鐵石齋記事》記載:河南浚縣選舉總約和各村鄉約時,須“公具保狀,來縣驗充”(39)。東北五常廳民間推舉鄉約長,須“稟請衙門準充”(40)。順天府寶坻縣民眾“若非蒙恩賞諭”,“不敢私行會同各莊紳民人等議舉”鄉約首事。(41)上述措施雖然有利于緩和官府和鄉約的矛盾,但卻同時進一步強化了官府對鄉約的監督和管理,使鄉約和官府的關系更加緊密,從而使鄉約這個昔日的民間自治組織進一步淪為聽命于官府的基層行政組織。
由以上可知,清代北方鄉約的行政組織化,導致了清代鄉約教化職能的削弱和鄉約自治地位的動搖,并引起鄉約和官府關系的變化,因而清代鄉約的行政組織化不僅是鄉約職能的調整,而且意味著鄉約性質的改變,標志著清代北方鄉約已經由民間自治組織發展為半官方的基層行政組織,鄉約首事已由鄉村自治的領袖演變為唯官府馬首是瞻的在鄉官役。清代北方鄉約行政組織化的消極影響說明,削弱甚至放棄鄉約傳統的教化和自治優勢而一味強化其行政管理職能的鄉約實踐是不成功的,鄉約行政組織化雖有利于加強官府對基層社會的控制,但并不能真正改善清代的鄉村政治,因而對清代北方鄉約的行政組織化不宜評價過高。
注釋
①⑤(20)賀長齡、魏源:《清經世文編》,中華書局,1992年,第1832頁。
②《硃批奏折》《內政類?保警》,乾隆四年五月二十一日張楷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
③賀長齡、魏源:《清經世文編》,中華書局,1992年,第1832、592頁。
④(39)黃璟:《鐵石齋記事》,光緒辛酉刊本,第39—40頁。
⑥陸耀、朗甫:《切問齋文鈔》卷二一,道光已酋刊本。
⑦《陽曲縣志》卷十《刑書》,道光二十三年葛英繁刻本。
⑧《洛寧縣志》卷六《藝文》,1917年鉛印本。
⑨《灤縣志》卷十八《故事?文獻徵存》,1917年鉛印本。
⑩(14)(32)徐世昌:《東三省政略》卷一,《中國邊疆叢書》,文海出版社,1965年,第1121、1122—1128、1123頁。
(11)《安東縣志》卷四《會費》,1931年鉛印本。
(12)吳殿珍主編《寧城縣志》卷一,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8頁。
(13)《萊陽縣志》卷二《政治志二?財政》,1935年鉛印本。
(15)李澍恩:《吉林行省賓州府政書》乙編《公牘輯要?民政》,宣統二年鉛印本。
(16)田文鏡:《撫豫宣化錄》,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32頁。
(17)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乾隆年間整飭書吏史料》,《歷史檔案》2000年第2期。
(18)(27)(36)陳顯遠:《漢中碑石》,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302、303、302—303頁。
(19)左宗棠:《左宗棠全集?札件》,岳麓書社,1986年,第415頁。
(21)《硃批奏折》《內政類?保警》,乾隆五年十二月二十日鄂爾泰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
(22)袁大化修,王樹相纂《新疆圖志》卷一〇六,《中國邊疆叢書》,文海出版社,1965年,第3915頁。
(23)吳藹宸:《新疆紀游》上篇,《中國西北文獻叢書》,蘭州古籍書店,1990年,第392頁。
(2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部、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清代黑龍江歷史檔案選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7頁。
(25)《阿拉楚喀副都統衙門全宗檔案》縮微膠卷第1卷,第15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
(26)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嘉慶年間直隸書役辦差勒索案》,《歷史檔案》2002年第1期。
(28)王西平主編,張進忠編著《澄城碑石》,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162頁。
(29)呼圖壁縣志編纂委員會:《呼圖壁縣志》,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24頁。
(30)楊增新:《補過齋文牘》辛集三,《中國邊疆叢書》,文海出版社,1965年,第2741—2743頁。
(31)李澍恩:《吉林行省賓州府政書》丙編《風土調查》第13章,宣統二年鉛印本。
(33)光緒《奉化縣志》卷四、卷十二,《中國方志叢書》,成文出版社,1974年。
(34)楊增新:《補過齋文牘》辛集一,《中國邊疆叢書》,第2502—2507頁。
(35)樊增祥:《樊山判牘》卷四,《批吳訪蓮等稟詞》,民國年間法政講習所印行。
(37)吳養原編《吳文節公(文镕)遺集》卷五二,《近代中國史料叢刊》,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1396頁。
(38)《洋縣志》卷六《文告》,光緒二十四年青門寓廬刻本。
(40)曹廷杰:《曹廷杰集》下冊,中華書局,1985年,第478頁。
(41)《順天府檔案》卷91,第155號,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館藏檔案。
責任編輯:王 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