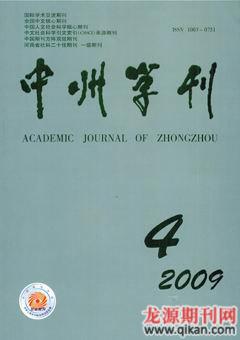論房琯對中唐初期士風與文風的影響
胡永杰
摘 要:房琯是中唐初期的著名文士之一。他自身道德、才學兼美,同時也繼承了前輩文儒所開創的優良傳統,樂于提攜、培養有才華有操守的士人。開元末期至肅宗時期,房琯一直和文士群體保持著密切的關系。在當時艱險的政治環境中,他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會聲望,盡其可能地幫助、支持、激勵包括大批文人在內的正直之士。房琯對當時文士既憤激、抑郁卻又堅貞、向上的思想心態和精神品質以及慷慨、沉郁的文學風格的形成有著不可忽視的貢獻。
關鍵詞:房琯;中唐初期;士風;文風;影響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09)04—0207—04
大唐開元時期,以張說、張九齡為首的一批文儒之士在政治上占據著主導地位。他們重視文學,尊重文士,培養、提攜了大批道德、文章兼美的文儒之士,也培養了文人們自信、勁健、積極進取、奮發向上的心態和精神面貌。房琯是張說等人所培養起來的重要文士之一。他自身繼承了前輩文儒的優良傳統,樂于提攜、激勵有才學、有操守的士人。特別是唐玄宗開元后期至肅宗時期,李林甫、楊國忠、李輔國等奸佞之輩相繼把持朝政,大肆打擊、排斥正直之士。在當時艱難的政治環境中,房琯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會聲望,盡其可能地幫助、支持、激勵著包括大批文人在內的正直之士,對當時的士風、文風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一
房琯(697—763),河南(今河南洛陽)人,年少時曾在洛陽附近的陸渾伊陽山中讀書十余年。史稱他“少好學,風儀沉整”。開元十二年(724),玄宗將封禪東岳泰山,房琯獻《封禪書》及箋啟。①當時張說任中書令,主持封禪之事,看到房琯的獻書,“奇其才,奏授秘書省校書郎,調補同州馮翊尉”。之后他歷任盧氏令、監察御史、睦州司戶、建德令、慈溪令、宋城令、濟源令。天寶元年(742)拜主客員外郎,三年遷主客郎中,五年任給事中;同年坐與李適之、韋堅善貶宜春太守,又歷任瑯玡、鄴郡、扶風三郡太守;十四年征拜左庶子,同年遷憲部侍郎。“安史之亂”爆發,房琯追隨玄宗入蜀,拜文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德元年(756)八月和韋見素、崔渙等人共同奉使至靈武冊立肅宗,深得肅宗的倚重。同年請兵討賊,加拜持節、招討西京兼防御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十月戰敗于陳濤斜。至德二年五月罷相,為太子少師;乾元元年(758)六月貶為邠州刺史;二年征拜太子賓客,上元元年(760)改任禮部尚書;尋又出為晉州刺史,改漢州刺史;寶應二年(763)四月拜特進、刑部侍郎。代宗廣德元年(763)八月,在回京途中卒于閬州僧舍。
房琯自身以才學受知于張說,深受張說等文儒之士的影響;而他自己也和張說等人一樣,是一位尊重文士,樂于提攜、幫助他們的賢明儒士。開元時期,房琯已開始和文士們進行交往。例如,他在為布衣時就和少年的杜甫相善;開元末期和著名詩人王維、孟浩然、高適、陶翰都有著密切的交往。王維詩集中今存《贈房盧氏琯》一詩。房琯任盧氏令是在開元二十二年之前不久,王維詩中云“達人無不可,忘己愛蒼生”,稱贊了房琯任盧氏令勤政愛民的政績;詩中還表達了想到盧氏隱居的愿望,以此可以看出兩人關系的友善。孟浩然詩集中今有《峴山餞房琯、崔宗之》一詩,也可看出他們交往的密切。陶翰有《贈房侍御》一詩,題下自注云“時房公在新安”,當是開元二十二年前后房琯由監察御史貶為睦州司戶時之作,“新安”當指和睦州相鄰的歙州新安郡。詩中對房琯“與道周旋”、“雄義特立”、“犯顏豈圖全”的節操都給予了高度贊揚。高適在宋州時有《同房侍御山園新亭與邢判官同游》一詩,是房琯由監察御史出為睦州司戶、再為宋城令時之作。詩中云:“夤緣事登臨,忝游芝蘭室。”由此看來,當時高適經常出入于房琯之所,和他一道登臨游賞,詩歌往還。
天寶時期,房琯也同樣和文儒之士們保持著親密的關系,而和李林甫等奸佞之輩處于對立的關系。天寶五年,李林甫謀害李適之、王琚、李邕、裴敦復、裴寬等文儒之士,房琯也坐與李適之、韋堅等善,貶宜春太守。但是,在艱險的政治環境中,房琯和當時不少著名詩人依舊保持著密切的交往。李頎有《聽董大彈胡笳聲兼寄語弄房給事》一詩,是寫給房琯的,詩里的“董大”當是董庭蘭。據《舊唐書?房琯傳》記載,“(房琯)則聽董庭蘭彈琴,大招集琴客筵宴”;又云“琯好賓客,喜談論”。這里記載的主要是肅宗至德年間的事情,但是可以看出房琯和琴工董庭蘭的密切關系以及他經常聚集賓客宴飲、談論、聽琴的喜好。房琯曾于天寶五年任給事中,李頎詩稱房琯為“給事”,當是作于此時,可見當時李頎也是經常到房琯處宴飲、談論、聽琴的。李頎還有《送綦毋三謁房給事》一詩,是送綦毋潛拜謁房琯之作,也寫于天寶五年。綦毋潛于天寶初年棄官還鄉,詩中云“高道時坎坷,故交愿吹噓”,“此行儻不遂,歸食蘆洲魚”。陳鐵民先生曾推測:“細玩《送綦毋三謁房給事》‘高道二句及‘此行二句之意,潛謁房給事,蓋為謀求再次出仕之門路。潛后果復出仕,任右拾遺。”而從“故交”、“吹噓”等語也可以看出,李頎、綦毋潛都是和房琯交往已久、情意頗深的老交情,而房琯也是一位在政治之路上樂于幫助他們的人。天寶年間,詩人儲光羲也和房琯保持著良好的交往關系。儲光羲有《同房憲部應旋》一詩。房琯于天寶十四年任憲部侍郎,當時儲光羲在朝中任監察御史,詩應是作于此時。詩中云:“憲卿文昌歸,愉悅來晤語。”可見當時兩人同在朝中,經常往來,而且在一塊談論得很投機。房琯天寶年間還推薦過文士李翰(李華的宗子)。史載:“天寶末,房琯、韋陟俱薦(李翰)為史官,宰相不肯擬。”另外還需提及的是,房琯和元德秀的關系也很密切。據《新唐書?元德秀傳》記載:“房琯每見德秀,嘆息曰:‘見紫芝(元德秀字)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元德秀是開元后期及天寶時期一位極富道德操守的名士,《新唐書》本傳稱“德秀善文辭,作《蹇士賦》以自況”,蕭穎士、李華、賈至等著名文士都深受他的影響。
當然,開元后期及天寶時期幫助、支持、激勵著文人們的文儒之士不止房琯一人,而是一批人,諸如李邕、韋述、韋陟、張均、張垍兄弟、張鎬、顏真卿、蕭穎士、元德秀等,都是其中的重要人物。
二
房琯對文士們更大的影響則是產生在稍后的肅宗時期。“安史之亂”爆發后,房琯受玄宗派遣,與韋見素、崔渙等往靈武冊立肅宗,“(肅宗)以琯素有重名,傾意待之,琯亦自負其才,以天下為己任”。房琯一執掌大政,便大刀闊斧地提拔文儒之士,諸如嚴武、賈至、劉秩、杜甫等都在這時得到了他的推薦和任用。嚴武、賈至等人總體上都是既有正直品性又有文學才華的士人。嚴武是開元著名文儒嚴挺之之子,他也曾追隨玄宗入蜀,后來趕赴肅宗行在所,房琯“以其名臣子,薦為給事中”。劉秩是開元時期名儒劉知幾之子,房琯一直都對他極為稱賞。開元末,劉秩采經史百家之言,撰成《政典》三十五卷,房琯以為才過劉更生(西漢人劉向)。房琯對劉秩之弟劉迅也極為看重,史載“(劉迅)常寢疾,房琯聞,憂不寐,曰:‘捷卿(劉迅字)有不諱,天理欺矣”。而劉迅也是一位極具道德操守和才學的人,李華曾把他和元德秀、蕭穎士并稱為“三賢”。賈至則是開元時期著名文儒之士賈曾之子,至德元年十月,房琯請命討賊,肅宗允許他自選參佐,結果房琯“乃以兵部尚書王思禮、御史中丞鄧景山為副,戶部侍郎李揖為行軍司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誥賈至、右司郎中魏少游為判官,給事中劉秩為參謀”,并十分自信地說:“彼曳落河雖多,能當我劉秩乎?”房琯這話雖不乏書生意氣,但卻可清楚地看出他對文儒之士的倚重。杜甫至德二年從安史亂軍中脫身,奔赴肅宗行在所在的鳳翔,被授以左拾遺之職。杜甫這次被授官,也受到了房琯的推薦。杜甫在他《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韻》詩中曾說過“昔承推獎分,愧匪挺生材”,仇兆鰲注云:“推獎,謂房琯引薦。”而岑參這時也在杜甫等人的推薦下,擔任了右補闕。當時還有一位名為張偁的詩人也曾慕名而至,謁見房琯。②高適也在這時得到了重用。至德元年十一月,永王璘起兵江陵,肅宗聞高適論諫有素,詔而謀之,高適陳江東利害,且言璘必敗。十二月,以高適兼御史大夫、揚州大督都府長史、淮南節度使,并與淮西節度使來瑱、江東節度使韋陟共討永王李璘。除上述諸人之外,當時王維、顏真卿、韋陟、張鎬等人也都在朝中。
以房琯為首,包括杜甫、岑參、王維、賈至等文人在內的這批士人,是一個正直、向上而又團結、親密的群體。杜甫在《寄岳州賈司馬六丈、巴州嚴八使君兩閣老五十韻》詩中,記述了當時他和嚴武、賈至等人交往的情形:“恩榮同拜手,出入最隨肩。晚著華堂醉,寒重繡被眠。轡齊兼秉燭,書枉滿懷箋。”仇注云:“拜手隨肩,并為近臣;晚醉寒眠,與共晨夕;轡齊書枉,往來交密也。”可見當時他們之間情同手足、密切無間的關系。岑參當時也有《宿岐州北郭嚴給事別業》一詩,嚴給事即是嚴武;詩中描述了他和眾同僚共同到嚴武的別業游賞,晚上就住宿在那里,一直談論到半夜還意猶未盡的情形,可以佐證杜甫“晚著華堂醉,寒重繡被眠”等語。房琯被貶時,詔書中說他與劉秩、嚴武等“潛為結交,輕肆言談”,有“朋黨不公之名”,這雖是肅宗等人排斥他們的托辭③,卻可以讓我們從中見得他們志合情契的情形。當時,朝廷中還出現了久違了的詩歌唱和之事。例如,有一次賈至寫了一首《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詩,王維、杜甫、岑參都有詩相和。杜甫詩集中還有不少作于當時的其他應和、贈答之作,都可看出當時他們之間詩酒唱和、關系親密的情況。
如果回顧一下歷史,從開元二十五年張九齡罷相,李林甫、楊國忠先后獨攬大權、大肆排斥文儒之士以來,這種籠罩在文人心頭令人壓抑的社會政治局面已近二十年。正是房琯的執掌大政,讓包括文人們在內的正直之士頓有揚眉吐氣的感覺。一時間,朝廷中頗有一些文士匯聚的彬彬盛況。
三
從唐玄宗開元末期直至肅宗朝,是李林甫、楊國忠、李輔國等奸佞之輩相繼專權,社會政治環境頗為險惡的一個時期。從上文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看出,房琯等文儒之士則是當時社會正義之風的代表者和維持者。房琯作為政治地位較高的文士之一,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社會聲望,盡可能地激勵、幫助、引薦富有才學和節操的文士,當時很多著名文人都深深受到了他們的影響。當然,房琯等文儒之士對當時文人的影響是極為廣泛的,本文此處只就李頎、綦毋潛、儲光羲、杜甫、岑參、高適等直接受其影響者的情況略作論述,以窺斑知豹,觀其大概。
房琯等文儒之士對文人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文人心態和精神品質之上,而這種心態和品質無疑又會對他們的詩歌風格產生影響。綜觀開元末期、天寶時期、肅宗時期著名文士的經歷,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他們普遍仕途偃蹇、人生困頓;但是在艱難的人生境遇中,他們卻絲毫也沒有墮落,而是堅強地保持著傲岸、耿介、高潔的品性,這應該說有房琯等文儒之士對他們支持、激勵的原因。
李頎、儲光羲、綦毋潛在開元末期至肅宗時期都曾有過棄官的經歷。④他們的辭官并不是因為其社會責任感和報國經世之志淡薄之故,而恰恰是由于他們的人生理想遠大而又純粹的原因。如李頎《不調歸東川別業》詩云:“寸祿言可取,托身將見遺。慚無匹夫志,悔與名山辭。……且復樂生事,前賢為我師。清歌聊鼓楫,永日望佳期。”對于辭官歸隱之事,詩中所表達出的滿是無奈和憤激的情緒,可見他的辭官絕非主動之舉,而是出于理想無法施展的憤懣和傲視權奸、鄙薄利祿的品性。類似的思想情緒在李頎《送綦毋三謁房給事》、綦毋潛《早發上東門》、儲光羲《游茅山五首》、高適《封丘作》等詩中都可以看得到。當然,李頎等詩人的棄官之舉并非當時文人的普遍行為;我們談論他們的棄官,意在以之為視角窺視文人們的思想心態、志節操守以及精神品質。其實,當時多數文人無論仕宦還是退隱,大都始終保持著堅貞、高潔、耿直的品性,有著悲慨、郁憤的心態。儲光羲《田家雜興八首》其五云:“平生養情性,不復計憂樂。……忽見梁將軍,乘車出宛洛。意氣軼道路,光輝滿墟落。安知負薪者,咥咥笑輕薄。”詩中表現出對驕縱、輕薄之輩的鄙視。《采菱詞》云:“濁水菱葉肥,清水菱葉鮮。義不游濁水,志士多苦言。”則表現出堅守高潔品性的節操。李頎《行路難》、岑參《送張秘書充劉相公通汴河判官,便赴江外覲省》等詩,也表達了對趨炎附勢的浮薄世俗的厭惡和抨擊。總之,高潔、耿直、憤激是開元末期至肅宗時期文人們普遍的品性和心態,這種品性與心態和房琯等文儒之士們是恰相一致的。
和李頎等詩人開元末年及天寶時期慨然棄官之舉相對,房琯于肅宗時期為相時,杜甫等人則表現出對政治極為積極、投入的態度。這兩種行事表面雖然相反,但其內在忠貞正直的品性、操守卻是一致的。兩種舉動只不過是文人們的操守、品性在不同的政治環境中的不同表現而已,兩者結合恰恰可以讓我們更為全面地看到當時文人所受房琯等文儒之士的影響。
受房琯影響最大的文士當屬杜甫。杜甫一生在仕途的時間不多。肅宗至德、乾元時期他奔赴肅宗行在,任左拾遺;疏救房琯被下三司推問并最終和房琯等人一同被貶,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政治行事。在這次事件中,杜甫把其文儒的精神品質展現得淋漓盡致,他的忠貞、耿直的節操極為時人敬佩。他在后來所寫的《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中追述這次事件說:“唐始受命,群公間出。君臣和同,德教充溢。魏杜行之,夫何畫一。婁宋繼之,不墜故實。百余年間,見有輔弼。及公入相,紀綱已失。……公實匡救,忘餐奮發。累抗直詞,空聞泣血。……拾遺補闕,視君所履。公初罷印,人實切齒。甫也備位此官,蓋薄劣耳。見時危急,敢愛生死。”這表明杜甫是因為房琯繼承了貞觀、開元儒臣所形成的正直、骨鯁、進取的士風,具有淳儒之精神的賢臣,所以才傾心歸向、奮力疏救的。杜甫對自己疏救房琯而被下三司推問及被貶一事終生都沒有悔意,反而常常為當時沒有再耿直一點而有遺憾之感。他后來所寫的《建都十二韻》、《壯游》、《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韻》等詩中都曾提及此事,可以看出他對于這次事件是終生惦記,而且每一念及都情懷激烈,可謂是赤心不改。房琯去世后,杜甫還寫了多篇詩文祭吊、追念。這些足可看出杜甫對房琯情義之深,受其影響之大。
岑參于至德二年六月由杜甫等五人推薦擔任右補闕,乾元二年三月改為起居舍人,四月出為虢州長史。雖然岑參詩文沒有直接提及他和房琯的關系的材料,但在朝期間他和杜甫、嚴武、賈至、王維等人關系極為密切,也像其他文儒之士一樣,一直保持著忠貞正直的品性。岑參在《佐郡思舊游》一詩中曾評價自己在朝中的行事說:“史筆眾推直,諫書人莫窺。”這表明他任右補闕時上疏論事是直言敢諫,做起居舍人時寫史是秉筆直書。杜確《岑嘉州詩集序》也說他“入為右補闕,頻上封章,指述權佞,改為起居郎,尋出虢州長史”。房琯諸人乾元元年被貶,岑參則于乾元二年三月由右補闕改任起居舍人,四月貶為虢州長史。岑參被貶是否與房琯諸人有關,史料所限,不得而知;但是他由于品性正直得罪權佞而遭到排斥,這和房琯等人是一樣的。
岑參至德二年六月入朝任右補闕,乾元二年四月出為虢州長史。岑參在朝中的時間雖然不長,但是他對這段時光卻極為懷念,后來經常在詩中提及。如他在虢州時所作《初至西虢官舍南池呈左右省及南宮諸故人》詩云:“數公不可見,一別盡相忘”;任嘉州刺史時所作《西蜀旅舍春嘆寄朝中故人呈狄評事》詩中說:“起草思南宮,寄言憶西掖。時危任舒卷,身退知損益”;同時還有《客舍悲秋有懷兩省舊游呈幕中諸公》一詩,依然表現出對當年朝中生活及當時舊友的深深懷念。這些詩句之中所透出的對諸省同僚及往日生活濃郁的懷念之情,應該說主要是出于當時他們志同道合、關系和諧、協力為國的氛圍。岑參被貶后,除了濃郁的失落之感和對舊友、往事的強烈懷戀之情外,還有一份困頓之中不改赤子忠誠的堅貞之心。如他被貶虢州長史時所作的《題虢州西樓》詩所云:“明主雖然棄,丹心亦未休。愁來無去處,只在郡西樓。”意即雖處困頓,雖深感失落,但是對國家黎庶的忠貞之心卻始終不改,并沒有頹唐、衰颯之氣。他于代宗廣德二年所作的《送嚴黃門拜御史大夫再鎮蜀川兼覲省》詩云:“許國分憂日,榮親色養時。蒼生望已久,來去不應遲。”詩中諄諄勸勉嚴武為國分憂,勿負蒼生之望。可見岑參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有失落,有憂憤,但是卻一直不失對國家、百姓的系念和忠貞之心。這正是以房琯為首包括岑參、杜甫在內的這批正直之士的共有品格。誠如前文提及過的杜甫《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中稱贊房琯所云:“貶官厭路,讒口到骨。致君之誠,在困彌切。”
上文我們已經論及,房琯為相時,高適也得到了肅宗的重用。高適被肅宗召見是否受到房琯等人的推薦不得而知,但是從他早年和房琯友善的關系以及當時房琯大力提攜文儒之士的情況推測,也是極有可能的。乾元元年六月前后賈至、房琯、嚴武、劉秩、杜甫、張鎬、韋陟等人相繼被貶黜,而在這一年高適也被貶官為太子少詹事。高適被貶是否和房琯諸人有關,也不得而知;不過據《舊唐書?高適傳》所載,“李輔國惡適敢言,短于上前,乃左授太子少詹事”,可知高適和房琯等人一樣,具有耿直、忠貞的品性,都是作為正直之士受到李輔國等奸佞之輩的讒害而被貶官的。
當時,另一位著名文士李華也和房琯關系極為密切。他曾有《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銘》一文,文中講述了房琯在玄宗后期及肅宗朝忠貞為國的赤膽忠心,以及他受到奸人排擠,致使大志未酬、天下人凄凄的內情。李華之文不僅表明了他對房琯的高度敬仰之情,也可佐證我們前文所論房琯被貶時所被羅列的罪狀多是構陷、羅織之詞的史實。而從李華對房琯道德風操的贊美之中我們也不難想象,他自己的道德風操和精神品性必然也會受到房琯的影響。
當然,和開元時期的張說、張九齡等相比,房琯的文學成就并不突出;他自身的的主要興趣似乎也不在詩文之上,所以他對當時文士的影響主要是在心態和精神品性之上。但是,這種影響對于當時文學的重要意義并不可小視。如果對中唐初期文壇作一些總結的話,我們可以這樣說,是當時混亂險惡的政治環境的壓制之力和房琯等文儒之士所代表的正直士風的支持和激勵之力,兩者共同造就了杜甫、岑參等文人既憤激、抑郁卻又堅貞、向上的思想心態和精神品性。而這種思想心態、精神品性發之于詩文,便形成了當時勁健、沉郁的文學風貌。因此我們說,對于中唐初期文學風貌的形成,房琯是有推動之功的。當然,這份功績不是由房琯一個人創造的,而是由以他為代表的一大批文儒之士共同創造的。
注釋
①房琯的《上張燕公書》今存,見《全唐文》卷三三二。
②《全唐詩》卷二五八今存其《辭房相公》詩一首。
③《舊唐書?房琯傳》中所記載房琯主持陳濤斜之戰失敗,以及和劉秩、嚴武諸人“潛為結交,輕肆言談”,有“朋黨不公之名”等史事頗有失實、不公之處,很大程度上是當時奸佞之輩排斥正直之士的結果,他們被貶的罪名大部分都是誣陷、羅織之詞。此問題鄧小軍先生曾做過詳盡的考辨,可參看其《杜甫疏救房琯案與墨制放歸鄜州》一文(載于其《詩史釋證》,中華書局,2004年)。《新唐書?房琯傳》評論云:“原琯以忠誼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之下,為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使琯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為名宰。”此段評論不失為較公正之言。
④具體情況可分別參看傅璇琮主編《唐才子傳校箋》卷一《李頎》、卷二《儲光羲》、卷二《綦毋潛》,中華書局,1987年。
責任編輯:行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