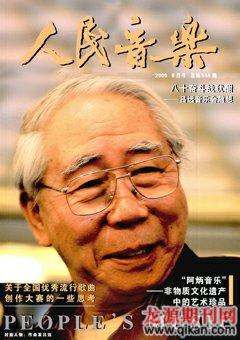中國古代聲樂文獻中的“字”與“腔”
始見于先秦的中國古代聲樂理論,在元代前并不成熟,不見唱論專著,只有少量散見于各類音樂文獻中的有關歌唱的論述,這些論述雖只言片語,但卻言簡意賅地道出了聲樂審美的精要。元代燕南芝庵《唱論》的出現,并伴隨著聲樂實踐的發展,有關聲樂的論述便更加詳細而系統。在這些聲樂理論中反映出許多問題,如,聲樂藝術的審美規律、聲樂技巧、聲樂道德、聲樂教學法、字與腔、聲與情的關系等等。其中字與腔是聲樂演唱理論中最具普遍性的問題,古人亦很早就注意到了。故本文將著眼于字與腔以及辯證關系進行論述,以便厘清它們之間的本質聯系。
一、中國古代聲樂文獻中的“字”
“字”,在《簡明古漢語字典》中作如下解釋:許慎《說文解字敘》:“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①《現代漢語字典》中提到“字”也可解釋為“文字的讀音”。②歌唱藝術是“用人聲唱出的帶有語言的音樂”,是語言化的音樂藝術,也是音樂化的語言藝術,因此它是音樂與語言有機結合、完美統一來傳情達意的一種綜合性藝術形式。字音不正,則字義不清,唱起來使人不知所云,欣賞者難以受到曲情的感染,更難與演唱進行交流,致使他們不為聲樂所動也就理所當然了。因而在歌唱中要做到咬字吐字清晰準確、字正腔圓、字清意明,即古人常說的“以情唱字、以字帶聲、以字行腔、字正腔圓”的道理。在我國近古,李漁就在《閑情偶寄》③中指出“字忌模糊”、“學唱之人,勿論巧拙,只看有口無口。聽曲之人,慢講精粗,先問有字無字。字從口出,有字即有口,如出口分明,字若無字,是說話有口,唱曲無口,與啞人何異哉!”“常有唱完一曲,聽者只聞其聲,辨不出一字者,令人悶煞。”、“然于開口學曲之初,先能靜其齒頰,使出口之際,字字分明,然后使工腔板,此回天大力,無異點鐵成金。”王德暉、徐沅徵在《顧誤錄》④中提到“最忌方板,更忌乜斜,大都字為主,腔為賓。字宜重,腔宜輕。字宜剛,腔宜柔。反之,則喧客奪主矣。”陳元靚在研究宋代唱賺這種歌唱藝術時也指出它的吐字上的美學原則:“夫唱賺一家,古謂之道賺,腔必真,字必正,欲有墩元掣拽之珠,字有唇喉齒舌之異,抑分輕清重濁之聲,必別合口半合口之字。”⑤徐大椿在《樂府傳聲》⑥中指出:“字若不真,曲調雖和,而動人不易”、“凡演唱自然應以清朗為最重要,欲令人人之所唱之為何曲,必須字字響亮。”從以上這些論述聲樂理論中“字”的觀點,充分反映出“字”在中國古代聲樂文獻、聲樂理論、聲樂演唱中的重要性。
二、中國古代聲樂文獻中的“腔”
在中國古代唱論中,對聲樂藝術審美規律、審美準則的認識,多集中于發聲行腔本身及其整體效果的要求上。古人對歌者聲腔的要求,從《樂記》中“累累乎端如貫珠”說,到“遏云響谷”、“余音繞梁”等對歌唱效果的描繪,均可見對聲腔清純、宏亮、圓潤、貫通之美的重視。到宋代,沈括在“如貫珠”說的基礎上,提出“善過度”說。他的《夢溪筆談》⑦在論及歌唱時指出:“古之善歌者有語……當使字字舉本皆輕圓,悉融入聲中,令轉換處無磊磈,此謂‘聲中無字,古人謂之‘如貫珠,今謂之‘善過度是也。”它要求“聲中無字”,強調聲腔貫通之美,是對“累累乎端如貫珠”說的具體繼承與發展。其后,元代的燕南芝庵在《唱論》⑧中提到“有字多聲少,有聲多字少,所謂一串驪珠也。”清代的劉熙載在《藝概》⑨中曰:“累累乎端如貫珠,歌法以之,蓋取分明而聯絡也。”以上各家,皆從“如貫珠”說出發,并各有發展,分別提出了“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夢溪筆談》),“聲要圓熟,腔要徹滿”(《唱論》),“生曲貴虛心玩味,如長腔要圓活流動,不可太長;短腔要簡徑找絕,不可太短。至如過腔接字,乃關鎖之地,有遲速不同,要穩重嚴肅,如見大賓之狀。”⑩(魏良輔《曲律》)的主張等。這里顯示出古人對聲腔審美除“宏亮、清純”的一般觀念外,又將聲腔連貫、過腔圓熟、接字無磊磈以及長短、強弱得宜等視為具體的審美準則。明清時期,在聲樂審美中,開始更縝密地注意到聲腔的藝術處理問題。徐大椿《樂府傳聲?頓挫》篇曰:“唱曲之妙,全在頓挫,必一唱而形神畢出,隔垣聽之,其人之裝束形容,顏色氣象,及舉止瞻顧,宛然如見,方是曲之盡境。此其訣全在頓挫。頓挫得款,則其中神理自出……此曲情之所最重也。”這里所謂“頓挫”,即指根據曲情要求而聲腔上所做的抑揚起伏、剛柔相間、跌宕多變的藝術處理,使人能聞其聲而如見其人(指歌中“角色”),并能盡合曲情,形神畢出。將頓挫之法視為“唱曲之妙”,可見其對歌曲藝術處理的重視。
三、中國古代聲樂文獻中的“字”與“腔”辨證
在我國古代,歷來就有關于“字”與“腔”的爭論,這也是聲樂美學討論的焦點之一,既有強調聲腔之美者,也有強調字的音韻之美的,以前者居多。宋代的沈括在《夢溪筆談》中曾說:“古之善歌者有語,謂當使‘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縷耳,字則有喉、唇、齒、舌等音不同。……如宮聲字而曲合用商聲,則能轉宮為商歌之,此‘字中有聲也,善歌者謂之‘內里聲。不善歌者,聲無抑揚,謂之‘念曲;聲無含韞,謂之‘叫曲。”上文表明沈括想在聲的基礎上,求得字與聲的有機結合,并服從于樂。這段關于“聲中無字、字中有聲”的論述闡述了字與聲的辯證關系。這是古代唱論中關于字聲問題的早期論述,指出了聲樂演唱由于自身的特殊藝術規律,必然存在著字與聲之間的對立統一矛盾,如何恰當地處理好這一對矛盾,便成了能否成為“善歌者”的關鍵。“聲中無字”從歌唱整體角度提出了要求,即演唱的連貫、婉轉,追求整體表現的旋律意境;“字中有聲”,則從局部之變化、豐富表現之需要,提出具體要求,即字字都要有飽滿悅耳的聲音支持,追求“字真、曲和”的理想境界,實現了語言與聲音的完美結合。字本身的音、聲、義、節奏與聲的音色、音量、旋律、節奏之間的不同,就預示著兩者之間是一種對立統一的關系。歌唱藝術正是在語言與聲音之間尋找兩者結合的契合點。宋代張炎在其《謳曲旨要》{11}中又在沈括所論的基礎上引申道:“字少聲多難過去,助以余音始繞梁。……舉本清圓無磊磈,清濁高下縈縷比,若無含韻強抑揚,即為叫曲念曲矣。”張炎還在他所著的《詞源》{12}一書中說:“腔平字測莫參商,先須道字后還腔。”這里的“參”和“商”都是指天空中星座的名字,也就是指“參星座”和“商星座”,這兩個星座在天空的運行中,是從不相遇的,每當參星座升起的時候,商星座便降落下去,反之也一樣。所以“參商”在這里就是表示分離的意思。也就是說他認為歌唱的聲音和歌唱的咬字吐字的關系是不能分離的,但二者之間,應在咬清字的基礎上,求得唱好聲音。王德暉、徐沅徵在《顧誤錄》中也提出相同的見解。明代魏良輔的《曲律》中詳解了字的音韻與行腔的關系,強調字音在歌唱中的支配地位,曰“五音以四聲為主,四聲不得宜,則五音廢矣。平上去入,逐一考究,務得中正,如或茍且舛誤,聲調自乖,雖具繞梁,終不足取。”
從以上闡釋表明,無論是同一時期的爭論還是不同時代的爭吵;無論是偏重于字還是偏重于腔,各家都有充足的理論根據和妙處。但在這方面,魏良輔卻有著獨到的見解。他在《曲律》一書中這樣寫道:“曲有三絕:字清為一絕;腔純為二絕;板正為三絕。”“初學先從引發其聲響,次辨別其字面,又次理正其腔調,不可混雜強記,以亂規格。”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字音、字聲、字義、旋律、節奏,在歌唱中雖有聯系,但卻又有著不同的概念,再加之字調“陰陽上去”四聲,使得歌唱語言既不能脫離歌唱的技能,又必須包含豐富的語言表達機能。由于語調的高低、快慢、長短、輕重以及音色明暗、音量大小的不同,故繪聲繪色的旋律又蘊含著字與聲的辯證關系。不論忽視哪一方面,都不能使歌唱進入一個完美的境界。
“字”與“聲”的有機結合,是要處理好兩者之間的辯證關系。前面已經談到的“聲中無字,字中有聲”就是“字”已融入腔內,“字”與“聲”形成了和諧的統一體。“字中有聲”是字已經達到了音樂化的目的。因此,僅有“聲”無“字”不行,而僅有“字”無“聲”也不行。這是因為歌曲演唱過程中要以“字”表情達意,要以“聲”美化字音。因此,我們在演唱歌曲時要注意“字”與“聲”的結合特點,因為如果字輕聲重,字為聲所包,聽起來便會有聲無字,聲不達意;而字柔聲剛,則不能控制抑揚頓挫,聽起來必是“叫曲”。因此重與輕、剛與柔在這里是對立的統一。正如《顧誤錄》所談及的“字宜重,腔宜輕。字宜剛,腔宜柔”。《樂府傳聲》指出的:“輕者,松放其喉,聲在喉之上一面,吐字清圓飄逸之謂。重者,按捺其喉,聲在喉之下一面,吐字平實沉著之謂。”
在我國傳統聲樂藝術理論中,聲韻對于字音、字義的表達具有十分重要的美學意義。我們知道,京劇的聲腔是在湖北語音基礎上加以美化夸張而產生的。京劇的旋律音調也是以湖北語音的四聲抑揚為基本準則,在聲韻上也是一樣,這就導致了京劇在字音字韻上必然產生強烈的變韻易轍現象,從而形成了它在音韻上獨特的美學構成。{13}這些對于字韻的審美要求,如果從地方語音的自然規律來看,并不復雜,這是它以能為北方人聽懂作為客觀基礎而形成的規律。合乎這些規律,字則正,音則美;反之,京劇的聲韻轍口以至其聲樂美,就會首先從這一環上遭到破壞。這種音韻間的轉化現象說明了語音對于聲樂的權威性制約作用,說明了語音美是如何通過吐字達到聲樂美的普遍規律,很富有實際意義。在音韻規律制約下的復韻母字的慢吐藝術,在中國唱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以出聲、行音、收聲歸韻,把一個個字的頭、腹、尾完整地溶化在旋律音調中;不論這個旋律短得只有一兩拍、一個樂匯,還是長至十幾拍、甚至幾十拍的大樂句,都“當使字字舉本皆輕圓,悉融入聲中”,以清晰有力的噴口出聲,自然流暢地行腔,而又輕晰準確地收聲歸韻,使動人心魄的音調旋律處處滲透著圓滿、醇厚、雋永、耐人尋味的音韻美,從而使語義美和語音美整合為一個有機的整體。
字與腔的關系體現了“字正腔圓”的歌唱審美要求。我們不難看出其間蘊含著中國傳統美學中的“尚和”思想,追求“聲與字和,腔與句和”,不論是字音與聲,還是腔與語句之間,論者都強調并努力在理論上將這些矛盾雙方的對峙關系轉化為一體內在的和諧,從而達到一種聲音的和諧,演唱自身的和諧,演員與觀眾之間的和諧,集中地體現了中國古代哲學所倡導的中庸和諧之道。
①《簡明古漢語字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70—971頁。
②《現代漢語字典》,成都天地出版社1999年第781頁。
③李漁撰,堵軍編《閑情偶寄》,延邊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④王德暉、徐沅徵《顧誤錄》,《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版。
⑤[宋]陳元靚《事林廣記》,中華書局1999年版。
⑥[清]徐大椿《樂府傳聲》,《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中國戲劇出版社1980年版。
⑦[宋]沈括《夢溪筆談》(音樂部分),人民音樂出版社1983年版。
⑧[宋]燕南芝庵《唱論》,修海林編《中國古代音樂史料集》,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版。
⑨[清]劉熙載《藝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⑩[清]魏良輔《曲律》,修海林編《中國古代音樂史料集》,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版。
{11}[宋]張炎《謳曲旨要》,文化部文學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編《中國古代樂論選輯》,人民音樂出版社1983年版。
{12}[宋]張炎《詞源》,修海林編《中國古代音樂史料集》,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0年版。
{13}陳幼韓《戲曲表演美學探索》,中國戲劇出版社1985年版,第58—60頁。
彭丹雄浙江師范大學音樂學院副院長、副教授,文學碩士
(責任編輯張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