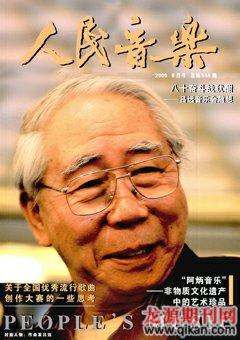“情境邏輯”:聲樂表演藝術理論研究
程 軍
在以往有關聲樂藝術表演的文獻之中,“情感性”和“炫技性”始終是作為表演的核心要義,高居于評判標尺之上。似乎歌唱的最終目的,終將只是指向對聆聽者“情感”的引發。此般理論,在中西樂事中比比皆是,不一而足。譬如以歌劇為例,西方自十八世紀初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中的“美歌”時代(Bel canto),閹人歌手們為了能夠毫不費力地演唱無比輝煌的華彩樂段,而進行種種精心訓練,但這種對音色感觀的極端追求,其結果卻只是導致華麗之后的情感真空;而在浪漫主義時代,聲樂體裁本身似乎便是為了擔負“情感陳述”的職責,情感便是一切,常常自顧脫離歌劇文本的語境前提,最終因毫無節制的情感濫用而破壞了歌劇藝術綜合美的有機性。歌劇史歷經格魯克、蒙特威爾第、莫扎特及至先鋒派貝爾格、布里頓等大師的種種革新,其最終的目的,也正是為解答一個謎題:音樂和戲劇,究竟誰才是歌劇的邏輯。對優美音色和靈敏技巧的渴望、對充沛的情感渲染力的追求,在聲樂藝術表演中,固然極為重要。但作為一門藝術,表演家們還應該有著更為清醒的主體意識。本文要旨,正是意在嘗試提出一個聲樂表演的理論概念,即:將“情境邏輯”作為聲樂表演——尤其是歌劇表演藝術的依據之一。文中觀點當屬個人一孔之見,偏頗遺漏在所難免,敬請各位方家指正。
一、“情境邏輯”之學理界定
所謂“情境邏輯”,乃是英國美術史大師E.H.貢布里希于其煌煌巨著《理想與偶像》中,分析藝術發展動因時所提出的一個學理概念。他認為,“社會科學中有一種客觀的方法,也許可以稱為客觀理解的方法或情境邏輯。一門客觀理解的社會科學可以不依賴任何主觀的或心理學的思想而獨立發展。這就在于,詳盡地分析行動的人們的情境,以便從情境中解釋行動,而不必借助心理學。客觀的‘理解就是,我們認為行為客觀上符合情境。換句話說,盡可能廣泛地分析情境,使那些最初像是心理學因素的東西,如愿望、動機、回憶、聯想等,都變成為情境因素。把一個有這樣或那樣愿望的人變為一個處于追求這樣或那樣目標的情境的人。把一個有這樣或那樣回憶或者聯想的人,變為一個處于用這種或那種理論或者這樣或那樣的信息裝備起來的情境的人”①。
可見,“情境”二字絕非等同于“情節”、“主題”、“歌劇腳本”或者“舞臺背景”、“作品風格”諸般概念。在歌劇的實踐美學中,它意味著一個更為綜合的理念,要求表演者對角色做更綜合層面上的揣摩和把握。所以,“情境邏輯”作為一種分析視角,強調的是從客觀的角度出發,從而避免空洞的抒情和盲目的炫技。對于現實表演而言,“情境邏輯”已經化為一種“語境”,我們可以從歌劇中角色的形體語言以及歌唱兩方面,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首先,“形體語言”與“情境邏輯”之間的關聯。歌劇中的動作行為,其比重雖不如話劇,但仍然擔負著不可取代的戲劇使命。優秀的歌劇表演家除了能夠發出自如優美的聲音之外,還須妥帖地依從劇作情境,設計動作樣式。這里的“情境”被理解為制約角色行為選擇的“客觀環境”,據此引發人物的行為選擇。絲絲入扣于“情境邏輯”的形體語言,能夠更好地推動戲劇情節的“起承轉合”,使人物的形象刻畫更為傳神深刻。格魯克在著名的《阿爾切斯特》前言(Preface to Alceste)這篇經典文獻中對“動作必須貼和情境”的問題洞之若燭,他說道:“用音樂表達感情,遵循劇情的發展,不用無價值的浮夸裝飾去打斷動作或抑制動作。”②正確、真實的動作才能夠和歌唱的內在激情相互配合、相互促進。《茶花女》第二幕中薇奧萊塔和阿芒的交鋒便能深刻地說明這一點。劇中薇奧萊塔面對阿芒突如其來的造訪,首先表現出一種優雅的敬意,因為他是愛人的父親,但當阿芒粗暴無禮地要求薇奧萊塔離開他兒子,并譴責薇奧萊塔貪慕虛華引誘其兒子時,薇奧萊塔在形體語言上經歷了從“凜然對抗”、“斷然拒絕”到“痛苦掙扎”的動作形態。當阿芒終于知曉事實的全部真象,對薇奧萊塔報以同情之時,薇奧萊塔卻又表現出一種“原諒”的神情。這種種形體語言,無不深深刻畫出她雖為風塵女子但卻無比高貴的內心,從而使觀眾對茶花女的悲劇報以更深刻的同情和憐憫。
世界著名的歌劇表演家們,除了擁有令人嘆服的嗓音技術之外,也多能夠從劇作本身的情境邏輯出發,去進行形體語言的塑造。比如《唐?卡洛》中因飾演伊麗莎貝塔而聞名的女高音格蕾?布魯文斯蒂恩(Gre Brouwenstijin);男中音布林恩?特菲爾等等。傳奇女高音瓊?薩瑟蘭女爵曾對年輕演員語重心長地告誡道,“有些年輕歌唱演員一上來就唱《安娜?波列娜》的終場,對我來說,這段不是入門者唱的,因為你得經由整部歌劇才能導向這個最終的場景”③。在這里,“整部歌劇”作為一種“情境邏輯”,制約著角色人物行動的發出,以及情緒的變化。薩瑟蘭爵士隱約道出了歌劇藝術表演的一個真諦。 需要強調的是,注重臺本的揣摩,雖然幾乎可算是所有表演家耳熟能詳之語,但對于真正把握“情境邏輯”而言卻絕非僅此而已。正如美國著名音樂學家保羅?羅賓遜(Paul Robinson)所言,“文辭和故事僅僅是個開始。如果只是談論文辭和故事,或許我們會總結出許多啟發性的聯系,但這些結論最終缺乏解釋的力度,因為這種結論沒能與音樂——區分歌劇與戲劇的主要因素——發生關聯。歌劇首先是一個音樂現象,它的歌劇性妥協不會使我們脫離音樂的上下文”④。在歌劇中,音樂其實負載著更多的它真正想要表達的思想——無論是作曲家還是劇本情節本身的。這要求表演藝術家們,除了認真揣摩腳本角色和對生活經驗的點滴積累之外,核心之處在于要能夠把握住歌劇的觀念所在。這其實也就是我們所一直在談論的“情境邏輯”。譬如,要想真正把握住瓦格納的《飛行的荷蘭人》中角色的漂泊、彷徨之感,表演家們最好能夠知曉這出歌劇和海涅作品之間的思想關聯。
其次,情感的流露與“情境邏輯”之間的關聯。“以情帶聲”已經是聲樂藝術的權威信條,無人能夠反駁。事實的確如此。問題在于,“情感的流露”是在“情境邏輯”的制約之下,即,只有依據“情境邏輯”,才能獲得“真實的情感流露”,否則便是矯情,觀眾也很難理解這些情感的內涵。世界一流男低音馬爾蒂?塔爾韋曾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當聲音一進入良好的狀態,音色立即呈現出來,而你在想的是唱的內容。聲音是歌唱者的仆人,很多時候我有目的地唱一個重聲音,因為聲音只是仆人,而我們必須告訴我們意圖表達的內容。一個歌手不能只是一口空擺著的鐘。必須有鐘聲傳達訊息”。可見,情感的釋放必須具有一種“意圖性”,它有自己的“情境邏輯”,而不是漫無來由的“濫情主義”。一位優秀的歌劇表演藝術家,將能始終保持著一種主體克制意識,小心謹慎地處理自己的主觀情感和音樂本體之間的關聯,絕不會過度沉溺于一種危險的狹小個人情緒之內。否則,對于作品的詮釋,經不起審美的細致推敲和聽覺考驗,令人聽而生厭,興味全無。
二、“情境邏輯”的組成要素:以《費加羅的婚禮》為例
筆者認為,在歌劇表演藝術中,“情境邏輯”主要應該涵括下列兩個部分:“戲劇本體”的“情境邏輯”、“音樂本體”的“情境邏輯”。前者具體而言,包括情節展開、人物關系和矛盾沖突、戲劇觀念;后者則主要旨涉音樂主題、情感內涵、表現手段(音樂語言和技法)。“從美學層面上看,戲劇的本性主要在于它的空間性、造型性或曰再現性,而音樂的本性則在于它的時間性、抒情性或曰表現性。當這兩者作為構成元素同時進入歌劇綜合體之中時,一種神奇的對比互滲效應也就隨之發生,于是便產生出一種新質,一種任何單一藝術所不可能具有的綜合美感,于是便造就了歌劇藝術在美學品格上空間性與時間性的統一、造型性與抒情性的統一、再現性與表現性的統一、造型性與抒情性的統一、再現性與表現性的統一。”⑤這意味著,當使用“情境邏輯”去分析歌劇角色和內涵時,演唱者應當在保持清醒的主體意識之下,根據戲劇所提供的人物、情節、動作、沖突等等,去進行一種空間性和視覺性的描繪和構思,這體現為演員的形體語言、面部表情、臺步的走法等等;而音樂作為一種主情的要素,將擔負著以直入心靈的方式去揭示歌劇人物內心世界最微妙、最精細、最隱秘的情感活動和心路歷程,總之,戲劇所未能言及之處,音樂皆能補充,二者唇齒相依、不可偏廢。只有充分理解上述情境,表演者才能恰如其分地詮釋出歌劇的觀念和意圖所在,在舞臺上展現出無與倫比的風采和吸引力。筆者在此試圖以莫扎特的四幕歌劇《費加羅的婚禮》中的“費加羅”形象為例,簡要概述“情境邏輯”分析法對于歌劇表演的重要性。
首先,從“戲劇本體”的情境邏輯而言,關于該劇的性質、情節、觀念,業界已經達成共識:這是一部社會喜劇,足智多謀的費加羅巧妙地懲罰了放蕩不羈的伯爵,使其不能行使貴族陋習中領主特有的初夜權,體現了18世紀啟蒙運動關于“理性”的思想潮流。這是一部人物眾多、人際關系異常復雜的歌劇,所以,人物間的“沖突關聯”是詮釋角色時所要考慮的“情境邏輯”之一。比如費加羅和伯爵的沖突在于,荒誕放蕩的伯爵意欲對未婚妻蘇珊娜行使初夜權;伯爵和羅西娜的沖突則在于愛與背叛;費加羅和蘇珊娜的沖突則在于忠誠與誤解;伯爵與凱魯比諾的沖突則在于愛與嫉妒。如此多的沖突,卻在終場都達成和解,伯爵夫人的寬恕,使事件導向于“大團圓”式的結局。所以,我們可以將整部戲劇的思想觀念具體分析為,莫扎特創造了一種真相與愛情的音樂論證,對人性的惡與社會的不公抱之以深切的人文關懷。于是,這里所謂的啟蒙運動的理性精神,在劇中情境,變具體化為“一個關于公正社會的幻想:每個社會成員既能實現自己的渴望,又不至于摧毀他人的夢想”⑥。
根據上述情境,費加羅這一人物的形象特征便將清晰起來。他是一個足智多謀、風趣詼諧的角色,否則也不可能幫助伯爵得到羅西娜,又如愿以償地解脫蘇珊娜的困境;他是一個傲慢自負的男人,否則他也不會誤解蘇珊娜真的和伯爵有染;他還是一個狂放不羈、情感強烈、自信無比的人物,否則他也不會常常用一種甜蜜而冷淡的語氣,輕蔑地稱呼“Signor Contino”(我親愛的伯爵),給人一種顛覆既定階級關系、仆人控制了主人的情感效應。如此種種,成為歌劇演員塑造“費加羅”這一形象時,所必要了解的“情境邏輯”,據此來揣摩、選擇人物的動作、表情等等行為語言。
而“戲劇本體”中所未能揭示的種種人類間的微妙情感,則交由“音樂情境”來完成。筆者在此,主要擬選取重唱段落為例,剖析“音樂情境”和“戲劇情境”相互促進的效應。莫扎特天才般的音樂筆觸,用重唱這一方式,絕妙地描繪出人物間錯綜復雜的關聯、揭示了沖突下各個人物復雜的心緒和情感、推動著角色動作的進展和發出。比如,第三幕中的第十八分曲中的“Sull mandre”(他的母親)“六重唱”,它是由發現費加羅是瑪爾切利娜與巴爾托洛之子這一事件引起。“正如科爾曼所言,六重唱雖然是個玩笑,同時也是個和解的時刻:兒子和父母團聚,一個曾經受到奚落的未來兒媳也得到未婚夫的認可。”在六重唱戲劇沖突巔峰的時刻,即費加羅和其母親擁抱,蘇珊娜進來,在不明就里之下打了費加羅一耳光的時間,音樂的主題突然滑到下屬小調,弦樂出現了不安的抖弓,幫助點明了此處的緊張情緒,“六人此時同時唱出不同心態——費加羅、瑪爾切利娜和巴爾托洛表示理解蘇珊娜的憤慨是出于愛情,伯爵和庫爾喬仍是滿腹氣惱,但多少有點幸災樂禍;蘇珊娜當然是怒不可遏。他們六人重唱的豐滿織體將音樂推至高點,并將音樂穩定收束在屬調性C大調上——至此呈示部結束。”⑦敏銳的歌劇演員,在此處必定能夠感受到音樂情境和戲劇邏輯的內在一致性,以此來調節自己的動作發出和轉換,在情感的揭示上,也將采用一種真實自然的抒發和流露。因為,從來沒有無緣無故的情感,演員必須首先學會為情感的來由找到正確的通途。
結語:將“情境邏輯”作為聲樂藝術
表演的語境
綜上所述,“情境邏輯”對于歌劇藝術表演來說,具有重大的意義。它在“戲劇本體”上,是詮釋人物行為動作、思想觀念的“情境依據”,又是“音樂本體”上進行情感塑造和表露的“客觀尺度”。它具有一種“語境”力量,成為表演家們平衡情感抒發和理性控制二者關系的“調節器”。事實上,將“情境邏輯”作為聲樂藝術表演理論概念提出,正是為了提醒人們注意到這樣一個問題:演唱雖然是一門主情的藝術,但是“情感”不可脫離于“音樂和戲劇”的“情境邏輯”。事實上,歌劇的“情境邏輯”研究還有很多有待深入探討的問題,比如:在面對聲樂單曲時,“情境邏輯”的解析方式如何執行?有沒有可能提出更為全面和具體的“情境邏輯”分析方式?總之,歌劇是一門如此深奧的藝術,一位成熟的歌劇演唱者,只有不斷地開掘戲劇之情境邏輯的各項要義和內涵,才能夠在舞臺上大放異彩、塑造出各種令人難以忘懷的經典角色。
①[英]E?H?貢布里希《理想與偶像——價值在歷史和藝術中的地位》,范景中、曹意強譯,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7年版,第94-95頁。
②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London:Macmillan Publisher limited, Vol.7,1989, p467.
③朱墨青《年屆八十的神奇女高音》,《人民音樂?留聲機》2006年第12期。
④[美]保羅?羅賓遜《歌劇與觀念:從莫扎特到施特勞斯》,周彬彬譯,上海音樂學院2006級碩士論文。
⑤居其宏《歌劇美學論綱》,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頁。
⑥[德]沃爾夫岡?維拉切克《50部經典歌劇》,黃冰源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頁。
⑦楊燕迪《莫扎特歌劇重唱中音樂與動作的關系(續)》,《音樂藝術》1992年第3期,第65頁。
程軍 西安音樂學院音樂教育系副教授
(責任編輯 張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