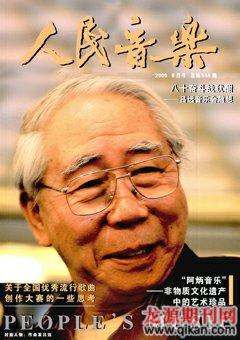沒有樹木 哪有森林
一
近讀劉靖之先生發表在《人民音樂》2007年第2期上的文章,從標題《音樂作品樂派之本——有關“新世紀中華樂派”之歷史思考》,到“隱隱約約地覺得‘中華樂派這個名詞是音樂史和音樂學者在研究、分析、歸納了音樂作品之后所總結出來的,是一個時期作品的風格和內容所形成,而不是可以憑人們的主觀愿望所能夠建立起來的”①,到“研究這個課題應以音樂作品分析為本②,從理論到理論,從文本到文本,夸夸其談是無法解決問題的”③等等論述,都深得我心。
但是,該文的“結語”卻指出:“……作品的數量不算少,可惜評論和分析、歸納的文字著作則難以配合。有些評論‘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我的意思是說大部分的文章,只作個別樂曲的分析和評論,缺乏宏觀的比較研究,而且傾向于文本論述,不重視音樂研究。音樂理論研究,應以音樂作品為本。”④本人實不敢茍同。這里且不說這段論述自身矛盾,并與該文前述矛盾⑤,而且將文章正確、鮮明的主旨“音樂作品樂派之本”幾乎“游離”成“作品分析樂派之本”了⑥!只就“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這一看法⑦,談談我個人的看法,并請教于劉靖之先生和各位同仁。
本文認為:個案文本分析從來就是音樂分析學的半壁江山,而目前并不太多、事實相當缺少、實需多多益善的針對中國現代音樂創作妥帖而完備的個案文本分析,則是中國現代音樂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基礎乃至不可回避的前提。
二
之所以說個案文本分析是音樂分析學的半壁江山,是因為音樂分析學主要包括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兩大部分:音樂分析理論與音樂分析實踐。理論需要實踐的檢驗,實踐促進理論的完善。相形之下,音樂分析理論形成和發展的周期,要遠遠緩慢于音樂分析實踐的頻率。老方法還可以不斷啟示出新視角的實踐——這甚至是更寶貴的——新理論則更需要大量實踐的證明。因此,在音樂分析學領域,音樂分析實踐遠比音樂分析方法活躍。而音樂分析學領域的分析實踐,恰恰又通常以個案文本分析為主流。
以音樂分析學領域享有世界聲譽的期刊《音樂分析》(Music analysis)所發表的成果為例,僅從該刊2005年10月號的目錄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個案文本分析在其中所占的地位,就已經不僅僅是半壁江山了!
作為20世紀新興的學科,音樂分析學在中國則幾乎是改革開放以來才真正起步并逐漸發展起來的。彭志敏、姚恒璐、賈達群、楊燕迪、張惠玲等教授為該學科在中國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實事求是地說,音樂分析學在中國目前仍然處于引入、介紹理論方法和運用、實踐西方已有理論的操作性階段,中國音樂分析學界還沒有對該學科做出成體系的理論構建方面的貢獻。當然,這也是一個學科從建立到發展再到成熟所不可回避的階段。
另一方面,中國音樂理論界理論研究服務于創作實踐、理論研究與音樂實踐相結合的理想與訴求從來強烈,這既有“立竿見影”的好處,也有影響學科獨立自在發展的不足。比如《曲式學》演變成《曲式與作品分析》乃至《作品分析與音樂創作》等等,都是這一思想的具體表現之一種。但不管怎么說,在音樂分析學領域,中國學者運用新興的音樂分析法對出色的中國現代音樂作品進行個案文本分析,不但有利于音樂分析學自身在中國的發展,對于中國現當代音樂創作實踐也會起到有力的促進作用。
音樂分析學本身從來不以追求獨特乃至僅僅是別人沒有分析過的對象為目的——這種情況在國內音樂學界恰恰比較普遍:在結論創新乃至視角創新難以實現的情況下,不少年輕的學者們往往更多地選擇最容易的“對象創新”,這,也許才是劉靖之先生文中所應該批評的那些個案文本分析——它更多追求的是理論方法的系統化與分析實踐的個性化。老課題深開挖、新開挖甚至是音樂分析學領域分析實踐的常態。雖然我不完全贊同“音樂學分析”⑧這個概念或名詞,但孟文濤教授在80年代發表的《一首五臟俱全的奏鳴曲式——剖解貝多芬〈月光奏鳴曲〉第一樂章,兼評魏納的分析》與于潤洋教授在90年代發表的《歌劇〈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前奏曲與終曲的音樂學分析》仍然是我國新時期以來音樂分析領域這一思路的典范之作。
三
另一方面,個案文本分析,對于中國現代音樂史研究,確實具有基礎性地位。無論是風格歸納還是歷史概括,對象越靠近,判斷則越困難。正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應該說,國內學界對當代專業音樂創作的評論、分析,在數量上還是較多的。音樂類學報,特別是作為音樂評論類的專門刊物《人民音樂》月刊,每年都刊發了大量相關文獻,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這些文章中的絕大多數,常常是就一部作品的首演或出版等情況,進行較為及時、較為粗略的報道、描述與評論,而真正意義上深入、細致的個案文本分析,在我國當代音樂創作研究領域,嚴格說來,其實才剛剛起步!而“音樂評論”與“文本分析”又各有不同的品質和使命,根本不能相互替代。
我曾在《關于中國現代音樂“文本分析”的幾個問題》一文中,粗略地討論過“音樂分析”、“文本分析”以及“歷史評價”之間的區別與聯系。認為:“文本分析,則一般介于音樂評論與歷史評價之間。它不可能非常及時,也不一定需要很長的歷史距離。文本分析主要屬于音樂分析學的范疇,以忠實地體現、表達、展示、突顯‘樂譜的‘客觀存在為主要目的。而這個‘客觀存在則主要指作曲技術理論含量特別是‘結構完型方式”⑨。
必須承認,相對而言,音樂評論比較感性,文本分析比較理性,而歷史評價特別是現當代音樂歷史研究,則應該更依賴于對大量文本分析所積累信息的比較和篩選。不僅中國現當代音樂歷史研究需要這樣,即使相對成熟、相當完備的西方音樂歷史研究,仍然需要對經典音樂作品——或者相反,可能被歷史“誤會”為比較一般的作品——進行個案文本分析,從而或豐富或深化或改變歷史,并發展與開拓史學研究。當然,在進行個案文本分析的過程中,主次清晰、有機關聯、力能所及、適度而為地觸類旁通是值得鼓勵的——前面提及的《音樂分析》2005年10月號也正有這樣的傾向。
最后需要再次、特別強調的是,無論是作為音樂分析的實踐,特別是作為中國現代音樂歷史研究的前提與基礎,對中國現代音樂創作進行個案文本分析,在對象的選擇上,確實是至關重要的一步:
“從嚴格意義上講,對象的價值決定了分析報告的價值。盡管文本分析基本上回避‘貶褒層面上的評論,但從根本上而言,分析者‘選取了某個作品作為文本分析的對象,已經在最大程度上‘認定了‘當下這個‘對象的相當重要、相當獨特的‘價值。也因此,如果說音樂評論的對象相對廣泛,尺度也可以相對寬松——畢竟是相當‘及時的——文本分析則對對象的選擇提出了相對苛刻的學術要求。”⑩
2005年以來,我曾經在武漢音樂學院策劃、發起并主辦的第一、第二屆中國現代音樂創作研究年會,其最深沉的目的,就是在目前還難對中國現當代音樂進行宏觀概括、完備論述的史學研究的情況下,能夠相對及時地從作曲技術理論的角度對現當代音樂創作進行分析與研究。事實上,來自全國各地的老中青三代學者向年會提交了一大批有分量、有價值、有爭議的學術論文,這確實是令人高興的事情。但所提交的論文中仍然存在著明顯的不足:比如,分析對象選擇的隨意性;比如,分析方法與作品實際之間的不相適應等等,都是值得學界注意與調整的。確實,對象選擇的妥帖與否,確實不僅僅關乎一篇音樂分析論文的價值高低;確實,狹義上的中國現代音樂創作歷史還比較短,我們面對的對象都是幾年前甚至幾個月前創作的作品;怎樣、如何能夠選擇一部“有價值”的作品作為研究的對象,本身就已經是一個艱難的挑戰。這需要我們的學者特別是充滿活力和創造力的年輕一代具有深邃的目光、敏銳的耳朵、完備的技術、平靜的心態和深沉的使命感。高為杰教授在2008中國交響樂論壇上呼吁“音樂評論要做音樂創作的好伯樂”,而對中國現當代音樂創作的個案文本分析,則要做中國現代音樂史研究的排頭兵!
四
沒有樹木,哪來森林?中國音樂分析學的發展與豐富,中國現代音樂史研究的開展與深入,都呼喚著豐富而多樣、妥帖而完備的個案文本分析。
即使有了森林,仍然需要新樹。宏大的歷史敘事,仍然需要不斷涌現的鮮活而新穎的個案文本分析來論證;日常的專業作曲技術音樂理論與音樂學理論的教學與研究的開展,也需要不斷更新、日益豐富的個案文本分析來支撐。
特別是針對中國現代音樂創作的個案文本分析,更是一個值得高度重視、長期關注,并且大有可為、具有可持續發展的領域。
何況,我們連樹木——特別是有可能茁壯成長的樹木——還都很少呢?!
①劉靖之《音樂作品樂派之本——有關“新世紀中華樂派”之歷史思考》,《人民音樂》2007年第2期,第18頁。
②這句話前面如果再加一句話:“新世紀中國樂派,應以大量、優秀的音樂創作為前提”,是否更完善?
③同①,第20頁。
④同①,第20頁。
⑤“文本論述”不是“音樂研究”?通常所指的音樂作品的“文本”,當是樂譜、音像制品等載體。而“樂譜”應該是最“音樂”的。
⑥我們的作品確實不少,但樂派的形成,不僅僅是以作品的數量為根本。也不是說有了很多作品,并有了很多分析,就一定能形成樂派。還是劉靖之先生的文章標題貼切——音樂作品,樂派之本!“好”的音樂作品,乃樂派形成之根本!
⑦最近在網絡上看到某音樂學院編輯紀念文集,也提出了“文章內容原則上不應針對某個具體作品,入選的文章應在學科內具備宏觀指導性”等要求。
⑧相對于西方的音樂分析學概念界定與論述體系,中國幾乎還沒有“純正”意義上的音樂分析實踐。學界所發表的論文幾乎都是“音樂學分析”——盡管側重略有不同。“純正”的音樂分析實踐絕大多數是研究生教育層面的練習與訓練。
⑨⑩錢仁平《關于中國現代音樂“文本分析”的幾個問題》,《音樂藝術》2005年第2期。
錢仁平 上海音樂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 于慶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