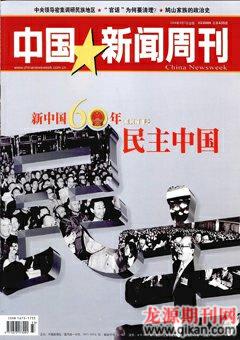新中國修憲風云
韓 永
編者按:
邏輯上,民主是憲政的前提,憲政是民主通過憲法而實現現代國家最理想形式,無民主即無憲政,憲政的本意在于主權在民。正如此,憲政法律秩序必然追求民主,民主是憲政法律秩序的首要因素。
憲法是固態的憲政,憲政是動態的憲法。所以我們回到起點,還原新中國歷史上歷次修憲的細節與故事,以期更深入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民主精髓。修憲也是一個舞臺,每位參與者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各不相同。
憲法每一個條文的修改,并非輕而易舉。過程中充滿了激烈的博弈。妥協有時候也在所難免。
李步云在1982年憲法修改時搞了一點“小動作”。
1980年7月份,李步云從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借調到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報到的第二天,他就領了一份特殊的任務:為葉劍英委員長寫一個發言稿,用在憲法修改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為1982年憲法的修改定調。
在與另外一個人合寫的這份發言稿里,李步云承認加入了一點個人的觀點——他往這個發言稿里塞了兩樣東西,一是立法民主,另一是“司法獨立”。
文稿沒有大的變動。李步云說1982年憲法修改有三點值得銘記,一是在結構上將“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移至“國家機構”之前;二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外一個,就是有關公民的定義。
誰是公民
“由于公民定義模糊不清,很多人就給全國人大寫信,問我到底是不是公民,全國人大也沒法答復,只是含糊其辭。”李步云說。
“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公民,罪犯也是公民”,源于李步云1979年10月30日《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論我國罪犯的法律地位》,這一文章的思想源泉,可以追溯到他在1978年12月6日發表在該報上的另外一篇文章:《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此文已被公認為中國法律界在“文革”后思想解放的開山之作。美聯社的“中國通”約翰?羅德里克評其為“政治法律領域一個重要轉折的標志”。
而當時,在公民問題上有兩種看法,一種認為只要有中國國籍就是,另一個認為人民和公民是一個概念,敵對分子不是公民。敵對分子包括地富反壞右,后來又擴大到一些被判刑的人。
《罪犯》一文發表后,引起了軒然大波。一些囚犯拿著刊有此文的《人民日報》,跟監獄管理人員叫板,討要權利。監獄不尊重犯人權利的現象也逐漸浮出水面。陷入被動的監獄管理方對該文滿腹意見。一位地方勞改局的副局長說:“講罪犯的這個權利那個權利,為什么就不能多給我們一些權力呢?”一次高規格的檢察長會議也對此文提出公開批評。
李步云的導師、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張友漁在關鍵時刻保了他一把。他在一些重要的場合明確表態,說這篇文章沒有問題。“如果說有問題,最多是說早了點。”
到了中央書記處后,李步云找到了一個為自己“翻案”的絕好機會。按照憲法修改的程序,先由憲法修改委員會秘書處擬定草案,提交委員會討論,修改后再提交中央領導審核。領導審核前,中央書記處要先把第一道關。作為其中為數不多的法律專家,李步云得以對憲法修改稿先睹為快,并就其中的爭議問題,選擇恰當的時機發出自己的聲音。

1981年底,他再次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在罪犯的法律地位問題上強勁發力:“如果這些人不是公民,那他們是什么?是人?是國民?他們在法律上是什么地位?憲法上說的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他不是公民,憲法就不能對他適用。那他既不能享受權利,也不用承擔義務。”“那這些人的行為用什么來調整呢?專門為他們制定一部憲法嗎?”
后來,憲法修改委員會秘書處的一位同事告訴李步云,他的這一番言論,已經說服了很多人,最終在該委員會的一次討論中被吸納。秘書處是憲法修改委員會的寫作班子,當時的秘書長是胡喬木,李步云的導師張友漁是副秘書長。胡喬木后來生病住院,起草工作事實上由張友漁主持。曾經參與過1954憲法制定的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許崇德,也是秘書處的成員之一。
公民定義的顛覆,其影響非同小可。媒體在報道此事時不吝贊美,說其“改變了幾千萬人的法律地位”。
人權人憲
此時,人權在國內還是一個忌諱的字眼。李步云之前發表的幾篇文章,也沒有敢用人權這一稱謂,只是說要保障公民的權利。1983年,李步云和法學所老所長王叔文去中南海開了一個會,領回來一個任務:清除精神污染。當時,學界的精神污染典型有兩個:一個是無罪推定,另一個就是人權,他的那篇《論我國罪犯的法律地位》就是一個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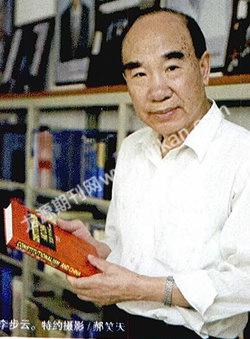
法學所所長王家福找到李步云,希望他參加批判人權的寫作小組。李步云提出一個條件:不能說人權是資產階級的口號,社會主義也要講人權。我們可以畫幾個杠杠,說明我們的人權和他們的人權是有區別的。王家福說:好。后來由于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正在興頭上,大家的注意力全轉移到那兒,這事也就不了了之。
到了1991年,國際形勢發生巨變,蘇聯東歐解體。這件事給中共高層震動很大,出了19個題讓有關部門去調查,社科院領了其中的大部分。這些調查試圖弄明白一件事:蘇聯東歐為什么突然間倒下?
社科院兩個調查組帶回來兩個完全不同的結論:一說蘇聯的解體,是因為戈爾巴喬夫的叛變和帝國主義的顛覆,另一個結論則是這些國家的制度有問題。后一個調查結果呈交上來時,社科院一位副院長不高興了,說我讓你們去調查,你竟然給我拿出這么個結論?調查組成員也不示弱,說你不是讓我去調查嘛,我查出來的就是這么個結論。
李步云后來給高層領導講課時,也強調這么個邏輯:如果蘇聯制度沒有問題的話,誰想搞垮它也搞不了。
正是從此時起,中國領導人的提法開始發生轉變。“不再說人權是資產階級的口號了,改口說社會主義也有人權。”但此時中國所提的人權,只談人權的特殊性,不承認人權的普遍性,與西方世界的爭論也一直僵持不下。
1992年下半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要社科院寫本書,描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什么,一共22章,李步云負責“人權”這一章。寫完后,李步云就接到電話讓他少講人權的普遍性。
李步云說人權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統一,不同意修改。后來,在李步云去美國訪問時,這條被刪除。
但半年后,情況發生變化。1993年6月25日,中國經過反復研究,同意了第二次世界人權大會起草的《維也納宣言及行動綱領》,這個文件有四處講了人權的普遍性。
此后,在中國的政治話語體系里,人權不再是一個忌諱的字眼。1997年,在中共十五大報告里,也正式寫入了“尊重和保障人權”。
但人權人憲并非是一個順理成章的事情。1999年修憲,被邀參與座談的李步云在中共中央提供的總共6條修憲方案里,并沒有看到他渴望的人權的字眼。他為此精心準備的發言,也完
全沒有派上用場。
不過,在6條憲法修改建議中,他如愿看到了“依法治國”的字眼。自從他1979年10月發表《論以法治國》一文并引發經久不息的討論以來,李步云也見證了“依法治國”人憲的整個旅程。在他看來,最具有轉折意義的是1996年2月8日中央高層的一次講座。
當時,司法部圈定了兩個題,最終確定為“關于實行依法制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這個題。主講人本來定的是李步云,但在試講過后,司法部決定臨陣換將,由社科院法學所所長王家福主講。
在這次講座后,江澤民發表了一個講話,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國”這一概念。1999年的憲法修改,原來的提法本來是“依法制國”,李步云聯合王家福、劉海年,給中央寫了一封信,建議將“依法制國”改為“依法治國”,并將江澤民的這一講話附在后面,最終高層拍板,“依法治國”走完了人憲的最后旅程。
而人權人憲,最終被推遲了5年。2004年修憲,李步云再次被邀參與由吳邦國主持的專家座談會。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沒有提供中共中央的修憲方案。李步云第一個發言,他提出的第一個建議,就是人權人憲。在現場的總共5位憲法專家中,還至少有兩位準備了這樣的建議,一位是徐顯明,另一位是許崇德。
激辯“專政”

2004年修憲,像這樣的專家座談會還有5場。江平和吳敬璉被邀請參與了其中的一場。與其他人不同的是,他們事先就此開了一個研討會。
中國政法大學副院長江平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開研討會的目的在于集思廣益。“我們有一個考慮,既然憲法修改,多征求意見不是更好嗎?”在1999年修憲時,吳敬璉也曾經接到邀請,但由于時間緊促,基本上沒有提出什么像樣的建議。
此前,江平和吳敬璉合作,在上海科協名下注冊了一個民間組織——上海法律與經濟研究所。他們在研究所發了通知,希望所里能先就憲法的修改發表意見。
研討會匯聚了20多位國內頂尖的法學、政治學、經濟學等領域的學者,這些學者的部分建議,被江平帶到了由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主持的修憲研討會上。
江平被安排在第4個發言,由于總共只有8位專家,每個人發言的時間都比較充裕。他總共提出了5點個人建議,除了主張私有財產保護人憲和人權人憲外,他還提到了幾個比較敏感的話題:一是憲法修改的指導原則問題。他說,現在似乎形成了一個規律,就是一屆新的黨代表大會開完就要修改憲法,而憲法修改是個嚴肅的問題,必須是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發生重大變化或是更強調對公民權益保護時,修改方有意義。“否則,僅把黨綱黨章修改的精神用之于憲法的修改,是不嚴肅的。”
此外,江平認為“三個代表”在序言中寫進去未嘗不可,“但不能非常生硬,更不能不倫不類。”“應當把‘三個代表的精神考慮進去,而不是光寫這四個字。”“而且我當時還說,我們過去有一種理解,就是憲法里面不能夠用縮寫的詞,‘三個代表如何翻譯成英文呢?”
許崇德建議寫進“三個代表”,但一定要加上引號。“有人反對,說法律沒有帶引號的,我查了外國的憲法,法國憲法序言里說:法國人民都擁護人權公約,那個人權公約是加引號的。還有蘇聯憲法中也有‘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表述。我就給有關部門打電話,說國外有這樣的先例。”
有關憲法修改的程序問題,江平說,憲法修改由執政黨在廣泛征求意見的基礎上提出憲法修改的草案不是不可以,但他認為最好的方式是執政黨向全國人大提出憲法修改的建議,由全國人大的修憲機構在征求各方意見后提出修改稿。“這樣做的好處在于樹立憲法在全國人民中的地位,更表明憲法的修改也應是全國人民的事情。”
江平還談到憲法監督機制的問題。“大家都認為憲法實施中最大的問題,不在于憲法規定內容應該擴大多少,而是在于現有的權利受到侵犯后,違憲的問題無法得到糾正。”他提及孫志剛案和“三博士上書”,“我們沒有一個專門審查和監督違憲機構。這個問題已經是迫在眉睫的問題了。”“當前至少應在全國人大內設立憲法委員會,在將來條件具備時,從議會的監督改為法院的監督,即設立憲法法院。”
江平結束講話后,吳敬璉發言。“他講的主要問題是憲法要公開。應該公告,通知到每一個人,每個人都可以提意見。”
“當時應該說還是在一個很隨便的氣氛中討論的。沒有反對我的聲音,都是個人發表個人的意見。”江平說。
博弈與妥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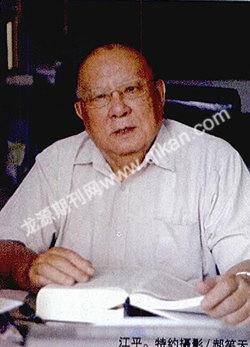
憲法每一個條文的修改,并非輕而易舉,過程中充滿了激烈的博弈,妥協有時候也在所難免。作為1982年憲法修改秘書處成員的許崇德,對憲法修改中的有些場景至今難忘。
這種討論的氛圍讓許崇德心旌蕩漾,他想起自己參加1978年憲法修改座談會上的一幕場景:當時,他主張將國家主席重新寫入憲法,被某鋼鐵廠的一位團委書記當場喝止,理由是“毛主席反對”。
1978年憲法修改發生在當年的3月份,此時距離代表著思想解放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還有9個月的時間。而1982年憲法修改的真正主帥彭真,此時尚未出山。
從1978年開始的真理標準大討論,給這次憲法的修改鋪上了濃重的民主底色。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前身)副院長江平在校內開了一門《西方民商法》,校內反響熱烈,校外也相安無事。
彭真在“文革”中被整的經歷,給1982年憲法修改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比如,許崇德說,彭真非常重視“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這一章,不僅把其位置提至國家機構之前,還把人格尊嚴和人身保護都寫進了憲法。“人身保護過去也有,但沒有這么強調。他自己親身經歷了‘文革受迫害的遭遇,有切身體驗。”
憲法還有一個條文,就是公民對國家工作人員有揭發、檢舉和控告的權利。“彭真在稿子上特別加了不能捏造或者歪曲事實進行誣告陷害這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