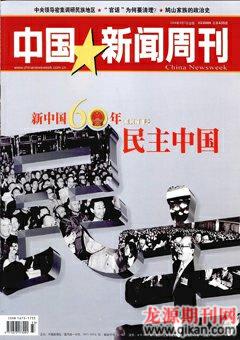雨城:海選“逼”出黨內民主
王維博
編者按:
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將中共黨內民主分為三個階段:1949年至1956年,中共堅持了民主集中制,同時也在不斷地完善通過民眾和民主黨派對執政黨進行有力監督的有關嘗試;1957年至1978年,自“廬山會議”始,中共黨內民主遭到個別高層人士的輕視,自此以后,階級斗爭擴大化,這個時期的黨內民主被嚴重地破壞和踐踏:1978年至今,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黨內民主制度也在不斷健全發展,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恢復行使職權、領導干部終身制取消等等,都是三十年來黨內民主與監督的重要舉措。
特別是中共十六大以來,形成了“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的新理念,相應的重大舉措已經出臺,如制定條例保障黨員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實行基層支部直選制度并逐步擴大差額選舉制度,減少副書記職數,加強對一把手的民主監督……
由公推村支書,到直選鄉黨委書記,再到區黨代表常任制。四川雨城的民主試驗,勾勒出基層黨內民主的現實與路徑。
300多名黨員開始在兩排用課桌搭起的“秘密劃票間”投票,課桌兩邊釘著木板,后面掛一個小簾子,每個競選人的照片就貼在簾子上。
馮學富參加的會議“級別”越來越高。2009年7月3日,作為基層黨代表,他被邀請參加四川省雅安市干部推薦大會,投票推薦3名“廳級”干部。
參加會議的有100多人,幾十名“黨代表”以外,其余均是正處級以上官員。廳級名額有一個,副廳有兩個,按規定每個職級可以投兩至三人。馮學富說,他的票和區委書記的票具有同等“分量”。
2002年,雨城區開始嘗試黨代表直選,魏家村支部書記馮學富被選為區級黨代表,不僅多次參加區、市兩級干部推薦大會,還每年參加兩次區黨代會。2000年,馮學富所在的村便開展了村支書的公推直選。
在雅安,雨城被稱作黨內民主的試驗田。從公推村支書,到直選鄉黨委書記,再到區黨代表常任制,黨內民主改革路徑漸次顯露。
操場上的“直選”
2006年4月8日一早,雨城區合江鄉魏家村黨支書馮學富趕到了合江中學的操場上,當天,全鄉將首次公推直選鄉黨委書記。
正是采春茶的季節,操場上有些燥熱,臨時搭起的主席臺上拉著橫幅。9點鐘,伍文利等十幾個候選人開始輪流演講。
“合江要大力發展茶葉,要搞一個茶葉交易市場,掌握市場主動權。”伍文利承諾,要用一年的時間發動全鄉村民成立一個交易市場。
有黨員提問,什么時候能實現。錢從哪里來,伍文利——答疑。
馮學富站在臺下,手里捏著兩張選票,一張鄉人大代表的選票,一張是鄉鎮黨委書記候選人的推薦票,“每一個競選者有一頁宣傳紙,照片和競選演講稿都印在上面。”馮學富說。
演講過后,300多名黨員開始在兩排用課桌搭起的“秘密劃票間”投票,課桌兩邊釘著木板,后面掛一個小簾子,每個競選人的照片就貼在簾子上。
至少給村民一個了解的機會,馮學富說,往常鄉黨委書記都換了幾任了,有的村民還不知道。他最后填了伍文利的名字,原因是伍“為人平和,競選承諾也講得實在”。
雙河村原村支書王國良也投了伍文利一票,71歲的老人有些激動,“茶葉市場的事以前也提過,但沒人拍板。”
最后票選結果出來,伍文利得票第一,當選為合江鄉首位“直選”黨委書記。
直選之前的一個月,合江鄉還進行了兩輪“公推”:由全鄉村民對報名參加的鄉黨委書記候選人投推薦票,將得票相對集中的前8位候選人上報區委組織部,通過審核后,由區全委會票決出2位候選人,最后交由合江鄉全鄉黨員大會最后選出一位黨委書記。
作為雅安市鄉黨委書記公推直選試點,區委組織部為這場選舉傲了“精心準備”。雨城區黨代表聯絡辦公室主任李德軍說。
選舉之前,區委組織部舉辦過一期選舉培訓班,除競選人外,還召集了部分黨員和村民代表參加。“主要告訴他們如何競選,村民如何‘公推,黨員如何投票等。”
正式選舉前,合江鄉還專門召集全鄉的黨員召開了一次動員大會。馮學富也參加了動員大會,“當天下大雨,大家都披著雨衣,300多個黨員坐在壩壩里,人人都戴一個草帽。”
直選的最大變化是黨員直接表決“書記”,馮學富說,書記說了不算,下次就通不過了。
這樣的公推直選此前已有試點。據四川省委組織部資料,2004年,包括雅安在內的10個市州30個縣(市、區)開始試點鄉鎮黨委書記“公推直選”,直接選舉出45名鄉鎮黨委書記。2001年底,四川省委還曾在全省三分之一以上的鄉鎮推行過一次“公推公選”,公選鄉鎮領導干部5447名,其中鄉鎮黨委書記787名。
鮮為人知的是,1998年,四川省青神縣南城鄉就進行了一次黨委書記直選,從零星試點到更大范圍的推行,四川經歷了6年多時間。
“海選”倒遇“公推”
“兩委”的制度性矛盾成為基層黨內民主的推動力量。
2000年,馮學富的前任,原村支書張玉祥被“逼”參加了村支書的“公推直選”。經過個人報名、演講和村民投票,張玉祥被公推為村支書候選人,最后由全村黨員投票,當選為村支書。
1998年底,魏家村村委會“海選”后的一天,魏家村黨支部一屋子的燜煙,煙灰缸里堆滿了煙蒂,支部會議開得很沉悶。一位支部委員望著村支書說:“張書記,以后財務都由村委會來管,村主任還能聽話?”
張玉祥看了看大家,半天沒吱聲。
魏家村轄4個生產合作社,278戶、920人。黨支部書記一直都是上級領導提名,考察后任命。村委會海選之后,按照《村委會組織法》的規定,村主任接管了村集體的財權,一直由村支書掌管的行政公章也移交給村委會。
盡管村支書的職責仍然是“抓大事”,但張玉祥總覺得少了經濟大權,其他權力就被架空了。
想了一夜,第二天,張玉祥去了鄉里。
“村主任可以搞海選,村支書能不能也搞一個選舉,”張玉祥說。
“村支書是黨員選舉的事,怎么能讓村民選?”時任鄉黨委書記的倪宏偉皺了皺眉頭。
“不能直選書記,就讓村民公推候選人。”
2000年11月底,魏家村在選舉村委會時,每個村民手上多了一張村支書候選人“推薦票”。
經過演講和村民投票,張玉祥和魏建文被公推為村支書候選人,在最后一輪黨員投票中,張玉祥當選為村支書。雖然競爭讓張玉祥很不適應,當選后張玉祥松了一口氣,“有了群眾基礎,工作更有底氣了。”
“要是放在以前,這(公推)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同村的馮學陽說,“上世紀70年代,黨支部管理生產隊的一切事務,修路、分田等具體事務,一律先由支部開會研究,然后召集黨員大會和隊干部會,宣布并實施。”
今年58歲的馮學陽是魏家村老黨支部書記,
15歲加入中國共產黨后一直擔任魏家村的黨支部書記到1978年卸任。
“如果黨員有意見,可以在會后提出,”馮學陽說,支部書記會逐個“思想教育”,直到說服為止。
1984年,馮學陽開始擔任魏家村主任,從這一年開始,村里的事情開始先由村委會討論,最后報給黨支部。“即使是支部內部開會,也開始少數服從多數了。”
“解放初期,村支部經常表決。”曾擔任過雙合大隊隊長的王國良說,“五個支部委員至少3人點頭才算通過”。
1969年以后,村支部開會少了,基本上書記一人說了算。王國良說,1974年,村里要辦一個茶廠,需將村里的荒山、荒坡和耕田重新調整,哪塊地種茶,哪些種田,全是支部書記一句話。
“書記有絕對的權威,不聽話的黨員先是被訓話,嚴重的發動群眾‘批斗。”王國良說,身為大隊長的他,也經常被揪到鄉大禮堂里挨批。
這樣的情況直到文革結束。
具體事務增加成為推動村支部公推的另一原因。中共四川省委組織部組織一處處長黃林在接受采訪時說,改革開放以后,村支部決策的具體事務越來越多,沒有村民的支持,工作根本沒法搞。“只有通過公開推薦,擴大村支部的民意基礎,才能保障村支部在村級事務中的決策中心地位。”
組織意圖與民意
村支書的“直選”很快推進到鄉一級。2001年開始,雅安開始在鄉鎮試行“公推公選”。
雅安市委常委、組織部長劉華軍認為:村和鎮的黨內民主是一種聯動關系,“當村支書都公推直選之后,自然會推著鄉鎮黨委進行改革,否則鄉鎮黨委的工作就沒有民意基礎。”
2001年,雅安市安排合江鄉進行鄉鎮黨委班子“公推公選”試點。由全鄉村民公推出兩鄉黨委候選人,再由全體黨代表投票選舉鄉黨委領導班子。
2006年合江鄉黨委書記由公推公選改為“公推直選”。公推出來的候選人由全體黨員直接差額選舉。
2006年2月底,伍文利從街道辦事處調到合江鄉擔任臨時黨委書記,組織上給她的任務是,組織合江的黨委換屆選舉工作,同時參與競選下一任合江鄉黨委書記。
按規定,另一位落選者還可參選副書記、委員等職務。“這樣可以使區縣的選舉盡量不影響組織確定的書記人選。”伍文利說。但她還是不放心,奉調之前她已經知道自己是區委組織部考察的重要人選,但也有選不上的可能。
接下來的一個月,伍文利以合江鄉黨委代理書記的身份,將全鄉10個村“過”了一遍。每到一個村,會先找村干部、黨員代表、村民代表等幾十人開座談會。會上,初來合江的伍文利會介紹自己當選后的發展思路,了解民眾有什么樣的需求,最后將這些需求結合實際加到她最后的競選演講中。
這樣的推銷顯然頗具效果,民意顯示,她的支持率直線上升。要做的承諾也要以書面的形式先呈報給換屆選舉委員會,征得區委領導的同意和支持。伍文利說。
剛開始直選,區委還有些擔心,不敢一下子全部放手。李德軍說。選舉之前,區委組織部門舉辦過一期選舉培訓班,組織參選者反復演練,還通過調動,讓部分競選者提前提任代理書記、副書記,提前了解村情,研究競選策略。
在區委組織部的大力推動下,伍文利成功當選鄉黨委書記,一年后,伍被調入區委組織部任副部長。而另外和她同臺競爭的9個人,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升遷。
這樣做是為了鼓勵基層干部參與競爭,通過公推直選也可以發現人才。在李德軍看來,合江鄉的公推直選很成功,“組織意圖與民意都照顧到了”。
來自另一個公推直選試點鄉鎮的觀化鄉黨委書記楊義認為,黨員的參與權、選擇權要保障,但上級黨委還應加強引導,通過培訓,將組織的意圖向黨員傳達,“畢竟組織部門對干部的能力比較了解,提出來可以供黨員參考,最終決定權還在黨員手中。”
由公推直選到黨代會常任制
公推直選到常代會常任制,基層民主由民主選舉轉向選舉與監督互為呼應的新階段。2002年8月,曾在四川遂寧設計并主持步云鄉長直選的張錦明調任中共雅安市委常委、組織部長。張上任不久,直選黨代表和常代會常任制試點開始在雨城區和滎經縣同時推開。2002年12月,雨城區首次在全區范圍內分選區直選縣級黨代表,馮學富和時任區委副書記的蒲忠都參加了直選。
打破身份界限、平等參與直選,被奉為雅安黨代表選舉的一大特色。
雨城區的82個選區,上至區委書記,下到普通黨員,都必須主動到所在支部報名,接受黨員的選擇。而且,在推薦初步候選人、正式候選人和選舉代表的過程中,均以姓氏筆畫為序,由黨員無記名投票推薦和選舉。這一變化,讓選舉者和被選舉者都備感壓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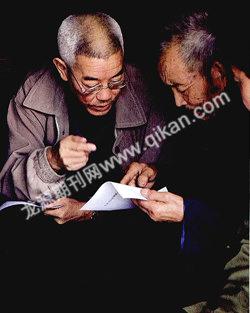
“當時區委書記看我初來乍到,擔心選不上,善意地提醒:要不要做些工作?我拒絕了,如果我連黨代表都選不上,我以后怎么工作。”現任雨城區委書記蒲忠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說。
事實上,在那一次選舉中,包括糧食局局長、計生局長和供銷社主任在內的3名科級干部在競爭中落選黨代表。“這在以往不可能發生!”直選結果讓很多黨員震驚。
2006年,馮學富再次當選為雨城區黨代表,同年又當選雅安市黨代表。
“參加會議的‘級別越來越高。”身為村官的馮學富笑著說,他不僅每年參加市區兩級黨代會,還經常與市委書記,區委書記“面對面”討論問題。
只有當民主選舉制度和民主監督制度互為呼應,民主政治才是完整的。只有當民主政治是完整的,權力才沒有失控的可乘之機。雅安市委常委、組織部長劉華軍說。
在劉華軍看來,始于2000年的“公推直選”“公推公選”等基層選舉改革為直選黨代表奠定了基礎。2002年,十六大提出“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基層黨內民主改革出現了前所未有的開闊操作空間。
“通過黨代表直選,明確了黨代會、全委會和常委會之間的授權與監督關系,使基層民主由民主選舉轉向選舉與和監督互為呼應的新階段。”劉華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