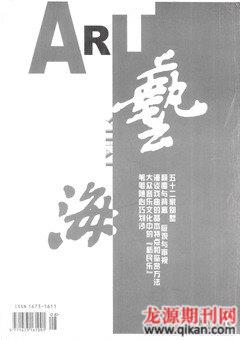中國(guó)寫意畫教學(xué)淺論
陸懿妮
中國(guó)寫意畫是一種將詩(shī)、書、畫、印融為一體的美術(shù)創(chuàng)作,是畫者之意、筆墨之意、物象之意的藝術(shù)統(tǒng)一。而所謂“寫意”,也不能被簡(jiǎn)單理解為用涂抹的方式、似是而非的形體、以及含糊不清的意圖來描繪其大概。“意”是畫家對(duì)宇宙、人生、時(shí)代、民族、社會(huì)、自然等一切的深邃體察之總和。是寫意觀使中國(guó)畫具有了極大的包容量,中國(guó)畫家把所見、所知、所想,經(jīng)過思維加工,綜合成一種宏觀意識(shí),力求充分完整的揭示自然的本相和畫家的心理世界。
中國(guó)傳統(tǒng)繪畫,扎根于中華民族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經(jīng)過數(shù)千年的發(fā)展形成了中華民族獨(dú)特的審美意識(shí),思維方式和哲學(xué)觀念的完整的藝術(shù)體系。縱觀中國(guó)繪畫的發(fā)展,可以看到由于老莊的“天人合一”、“陰陽(yáng)相克相生”的哲學(xué)觀的影響,中國(guó)的藝術(shù)家們很早便認(rèn)識(shí)到藝術(shù)的創(chuàng)作是一個(gè)主觀與客觀相統(tǒng)一的過程,中國(guó)畫不特別看重視覺的真實(shí),即是超越具體物象的摹擬再現(xiàn)而強(qiáng)調(diào)作者主觀情感的流露。中國(guó)畫中的借物抒情、托物言志的特點(diǎn)不是強(qiáng)加在作品上的,而是要善于抓住動(dòng)植物與人們的生活遭遇,思想感情的某種聯(lián)系,而給以藝術(shù)的夸張、強(qiáng)調(diào)。
“寫意”一詞作為文學(xué)詞匯轉(zhuǎn)借過來討論美術(shù)現(xiàn)象已有很多年歷史。“意象”、“意境”、“格調(diào)”、“情趣”、“神韻”等等,這些互為滲透、彼此聯(lián)系的民族美學(xué)范疇的繪畫基礎(chǔ)理論,在長(zhǎng)期的藝術(shù)實(shí)踐中形成了中國(guó)藝術(shù)家特有的認(rèn)識(shí)方法、思維方式、審美情趣和造型觀念。比如中國(guó)畫家在畫面中非常重視“意境”的創(chuàng)造。中國(guó)畫家認(rèn)為:在對(duì)客觀事物的觀察、認(rèn)識(shí)、感知中,產(chǎn)生與之相通的思想感情,通過特殊的藝術(shù)構(gòu)思和想象塑造,把這種情景交融的感情充分體現(xiàn)出來,使畫面產(chǎn)生一種動(dòng)人的效果,這就是“意境”的創(chuàng)造。由于創(chuàng)造過程不拘泥于對(duì)自然物象和簡(jiǎn)單模擬和再現(xiàn),而強(qiáng)調(diào)主觀的意思,因此就更加注重想象力的發(fā)揮。巧妙的運(yùn)用比、擬等藝術(shù)手法表現(xiàn)自然、社會(huì)和人類感情關(guān)系的推移,從而增強(qiáng)了抒情寫意的力量。一幅有“意境”的畫,往往給人“畫中有畫、無中生有”,給觀眾留下想象的余地,這樣個(gè)畫作貴在含蓄,意在筆先。
那么,在國(guó)畫教學(xué)中又怎樣讓學(xué)生體會(huì)到“寫意”之境呢?首先還是要理論分析中國(guó)畫的寫意觀。早在一千多年前,中國(guó)畫的寫意觀就已基本形成,并不斷豐富和發(fā)展。“天人合一”、“緣物寄情”、“不似之似的神似”等等,都是中國(guó)畫寫意理論的精華。
“天人合一”
縱觀中國(guó)畫的發(fā)展史,可以看出,由于受老子、莊子所總結(jié)的中國(guó)哲學(xué)觀念的影響,中國(guó)藝術(shù)家們很早便意識(shí)到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不僅僅是一個(gè)再現(xiàn)客觀的過程,而是一個(gè)主觀與客觀相統(tǒng)一的過程。在一千多年前,東晉著名的人物畫家顧愷之便提出了繪畫“遷想妙得”的主張,指出藝術(shù)家在體察、認(rèn)識(shí)、表現(xiàn)外部世界的時(shí)候,必須要經(jīng)過自己頭腦思維的遷移、想象、升華、頓悟,才能有所妙得。顧愷之“畫形”的角度論述了對(duì)“傳神”的要求。這顯示了那個(gè)時(shí)期玄學(xué)思想對(duì)繪畫藝術(shù)的影響,一方面也顯示了當(dāng)時(shí)的畫論思想是建立在關(guān)注畫面之形與對(duì)象之形的聯(lián)系上。到了唐代,畫家張?jiān)锇堰@一思想具體化為“外師造化,中得心源”的創(chuàng)作原則。“造化”在這指藝術(shù)家的主觀世界,包括觀察、體驗(yàn)、提煉、加工以及思想感情的介入和表達(dá)。這就說明了中國(guó)藝術(shù)家即承認(rèn)藝術(shù)創(chuàng)造來源于客觀世界,離不開客觀世界,同時(shí)又十分重視藝術(shù)家主觀心源作用。把作為描繪對(duì)象的客觀世界的“物”與藝術(shù)家主觀世界的“我”,也就是“天”和“人”,有機(jī)的統(tǒng)一起來,力求完美結(jié)合,形成密不可分、不可或缺的整體。從而達(dá)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清代山水畫家石濤曾在題畫詩(shī)中云:“我寫此紙時(shí),心入春江水。江花隨我開,江水隨我起。”他將這自然生命滲化于萬物的節(jié)律中,并隨之起伏,豈不妙哉?
“緣物寄情”
中國(guó)藝術(shù)家常常是“俯仰天地間”、“一俯一仰之際,幾與為通”。天地間壯麗的自然景物強(qiáng)烈的吸引了藝術(shù)家的目光,深深的打動(dòng)了藝術(shù)家的情懷。面對(duì)良辰美景,藝術(shù)家觀物觀我,在自然中找到了自我感情的寄托,有感而發(fā)、緣物寄情,便成為順理成章的歸宿。見秋葉落而嘆人生之短暫,與落花同悲人生之不平,看勞燕分飛而惜人生佳偶,聽白頭啾鳴感幸福之不易。在我國(guó)繪畫史中,隨便翻開一頁(yè),借助物象寄情抒志已是普遍想象。像中國(guó)藝術(shù)家喜歡描繪的梅、蘭、竹、菊四種花卉,將它們稱為“四君子”,這倒不是因?yàn)樗鼈兊男螒B(tài)比其他花木更美,而是將它們作為藝術(shù)家人品的象征物出現(xiàn)在繪畫中,用它們作為載體來寄托藝術(shù)家的高尚情懷。人們樂于欣賞它們,也不僅僅是出于審美的需要,更大程度上考慮的是道德,是用梅、蘭、竹、菊來體現(xiàn)正人君子的情操。如沈周的題菊詩(shī):“老我愛種菊。自然宜靜心。秋風(fēng)吹破屋。貧亦有黃金。”題竹詩(shī)中又有:“石山有芳姿,此君無俗氣。其中佳趣多,容我自來去。”畫家們通過題畫詩(shī),明確的表達(dá)了自己的觀點(diǎn)。
“不似之似的神似”
根據(jù)“天人合一”、“緣物寄情”的藝術(shù)觀,中國(guó)繪畫認(rèn)為再現(xiàn)自然不是藝術(shù)家的最高追求,中國(guó)畫也并不是以模擬一時(shí)的真實(shí)作為衡量畫作的標(biāo)準(zhǔn),而是在繪畫造型上追求“不似的神秘”。那么繪畫究竟應(yīng)該是畫像還是不像?怎樣才算畫像?對(duì)此,中國(guó)藝術(shù)家一直有自己的觀點(diǎn),那就是:既不能太像,又不是全像,既不能太寫實(shí),又不能全不寫實(shí)。早在五代時(shí),山水畫家荊浩在《筆法記》中就提出了“似”與“真”的問題。荊浩認(rèn)為,“真”與“似”是有區(qū)別的,書中問“何以為似?何以為真?”答曰:“似者,得其行,遺其氣;真者,氣、質(zhì)俱盛。”清代畫家查禮也在《畫梅題跋》中說:“畫梅不要像,像則失之刻,要不到,要?jiǎng)t失之描。不像之像有神,不到之到有意。”在這里,他直接的提出了繪畫不要太像自然的物象,太像了就失之刻板。筆意要不到,要意到筆不到,全到了就失之描摹,并著重指出,不像之像才能有神,不到之到方才有意趣。
縱橫中國(guó)歷代名畫,中國(guó)畫家已系統(tǒng)的指出“意境”、“神韻”、“神形兼?zhèn)洹敝f。也總結(jié)了“五色”,“六彩”之說,墨色的“濃、淡、干、濕”,運(yùn)墨的“潑、破、積”等方法,結(jié)合恰到好處的運(yùn)用“新墨”、“陳墨”,通過統(tǒng)一不同的墨色變化和墨意效果,充分表達(dá)了“寫意”之美。
我們?cè)诮虒W(xué)過程中,不僅要讓學(xué)生掌握用筆的技法,更要落腳于讓學(xué)生理解并創(chuàng)造自己的風(fēng)格,突出表達(dá)自己的用墨情意,學(xué)會(huì)抒發(fā)自己的感情,塑造藝術(shù)形象。像現(xiàn)代杰出畫家徐悲鴻所畫的馬,歌頌了民族的奮起精神,給人以向上的感染力量,而李可染的牛贊美了民族的負(fù)重精神……畫家通過創(chuàng)作藝術(shù)作品,讓我們感受他們表達(dá)的意境,甚至聯(lián)想起一個(gè)民族的精神。他們并不是用直接的說教,也不是用逼真的刻畫,而是憑著藝術(shù)作品的感染力,使人們?cè)谛蕾p的過程中得以啟迪而進(jìn)入到美的精神境界。正是這種情和理的交融,才會(huì)表現(xiàn)畫家的人生觀與藝術(shù)觀。
(作者單位:湖南科技職業(yè)學(xué)院藝術(shù)設(shè)計(jì)學(xué)院)
責(zé)任編輯:文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