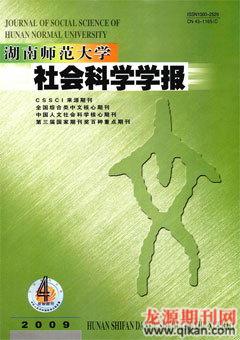西方還是本土:中國詩學研究的世紀性命題
李 怡
摘要:中國現代詩學發生的背景,以及發展過程,一直都是在“西方”與“本土”之間游走選擇,這也構成了中國詩學研究的世紀性命題,因此,《本土語境與西方資源》的學術貢獻在于重新辨析歷史材料,重新梳理和界定豐富復雜的中國現代詩學現象,重新探究和還原具體生動的中國詩學研究中的“中外詩學關系”,這是在新的學術語境中對一個重大命題的拓展和深化。
關鍵詞:中國現代詩學;西方;本土
中圖分類號: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2529(2009)04-0096-03
中國之有“現代”的詩學之所以會呈現出有別于中國古代的形態,與外來文化及外來詩學的引進輸入有莫大的關系。從最早“不學詩,無以言”、“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的儒家的功利主義詩論,到梁代鐘嶸的《詩品》對詩歌作品展開的思想藝術的品評,中國古代的詩論并不以探究詩歌本身的創造過程為目的,而是將主要力量集中于詩歌的社會作用與詩歌作品介紹、鑒賞等問題,中國古代詩論的這種實用性與鑒賞性的追求與西方自古希臘以來的詩歌批評傳統大相徑庭。從古希臘上古的詩的神性論到亞里士多德將詩視作“個別反映一般”的“技巧”,一直到文藝復興、浪漫主義、20世紀以來的一些詩論,詩歌創作者的感受始終是西方詩論所表述的中心,在西方,發展起來的是一整套關于詩歌創作實際體驗的“詩學”。亞里士多德的《詩學》討論的是詩人如何進行成功的“摹仿”,華茲華斯的《(抒情歌謠集)再版前言》述說如何“使日常的東西在不平常的狀態下呈現在心靈面前”,柯爾律治大談“想象力”、“天才”和詞語的使用,托·斯·艾略特研究“傳統”與詩人個人才能的關系,海德格爾追問“詩人何為?”這正如有學者已經指出的那樣:西方“無論是技藝學視野中的古典主義詩學還是美學視野中的浪漫主義詩學,都是立足于寫作過程并在對作者心性機能的假定中確立起來的。換句話說,它們都是從作者的心理機制出發來思考詩(藝術)的本質的。”值得注意的在于,恰恰是在進入“現代”之后,中國的詩歌理論與詩歌批評才大量出現了對詩歌創造過程與創造諸問題的關注,為了有效地解決這些創造的難題,中國現代詩論最重要的篇幅不再是“鑒賞”而是探討“怎么辦”,例如胡適闡發如何“用具體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做法”,俞平伯提出“增加詩的重量”、“不可放進舊靈魂”等方面的系列建議,宗白華探討“訓練詩藝底途徑”、“詩人人格養成的方法”,穆木天論及“詩的思維術”、“詩的思想方法”,梁宗岱論述“象征”如何創造等等。
超越古代詩論的鑒賞傳統、轉而關注和探究詩歌的創造主體問題與其他心理學問題,而且這樣的探討也一改固有的感悟、閑談的樣式,開始尋找著一種更具有思辨性和嚴密性的理論表述。“很難說中國現代詩人對哪一種哲學思潮特別感興趣,也很難分辨某一個詩人主要是汲取了某一種哲學思潮的養料,但是可以證實的是,中國現代詩學的建立無疑是在這樣一種有點混亂但確實體現了當時世界文化中最前沿的思想的基礎上開始的。”正是在這個背景上,我們可以說,對“中西詩學關系”的考察、梳理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我們研究中國現代詩學發生發展的最重要的背景,如何在“西方”與“本土”之間游走選擇,牽動著中國詩歌創作、詩歌理論與詩歌批評近百年的歷史進程,也構成了我們詩學研究的世紀性命題。譚桂林先生的新著以“本土語境與西方資源”為正題,以“現代中西詩學關系研究”為副題,可謂是準確地抓住了這一命題的核心。
作為現代中國詩學的“世紀性”命題,無論是“西方,本土”的框架,還是“中西關系”的視角,應當說都不是第一次出現了,然而,我覺得譚桂林先生出版于2008年的這一著作的話題依然有它特殊的學術意義。
任何一個具有長遠學術意義的命題都不會是被一次性呈現的,在漫漫的歷史當中,其意義的釋放往往具有多次性與起伏性,它的起伏所折射出的是歷史復雜的流變,不同的時段所呈現的就是這一段歷史的特殊含義,而對歷史發展的不斷的回應又從整體上深化和拓展了一個學術命題的內涵。立足于“西方/本土”選擇的“中西關系”的認知在中國現代新詩創作與詩歌批評的發展演化過程不斷釋放新的意義。在“五四”,這樣的認知引導中國詩人與詩論家從日益偏狹的古典詩境中掙脫出來,在異樣的景致與異樣的思維中重新探詢藝術陌生化的可能;在20世紀80年代,也是這樣的認知突破了僵化的政治封閉,在“走向世界”的寬闊視野中重構了現代中國詩學的基本闡釋模式。不過,在進入90年代以后,“走向世界”的理想卻遭遇到了一系列的學術質疑,隨之而來的更是對五四新文化的所謂“西化”傾向的批判和反省。這一新的學術動向實際上嚴厲地批判了通過引進西方文化尋求中國詩學發展的思路,至此,西方/本土的文化互動被扭轉為對“本土經驗”的格外倚重,中國現代的詩學建設在更多地被強調為一種本土的傳統的資源的繼承過程,“民族性”在這個時候更多地指向業已存在的傳統形態,而“本土性”常常被假設為一種穩定不變的區別于其他國別文化的東西。
我曾經指出過,1990年代對1980年代“走向世界”的質疑有它自身的根據:當“走向世界”的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了如何“才能世界”,而相對忽略了中國作家作為創造主體的一些具體遭遇之時,這便為后起者的反對留下了空間,甚至在一些人眼中,“走向世界”根本就是“西方文化霸權”的產物。不過,在批判1980年代、質疑“西化”10年后的今天,我們已經可以清晰地看到,對于一個早已經步入了世界現代化進程的民族而言,其實無法真正將其他民族的文化資源隔絕在自己之外,而現代中國詩學的發展也同現代中國文化的發展一樣,已經不可能由傳統文化獨立支撐了,那種試圖通過召喚古典傳統抵抗外來文化以保存文化“純潔性”與“獨立性”的努力不僅在理論上充滿內在的背謬,而且從來也沒有為我們的實踐所證明。相反,為我們質疑和批評的“西化”的時代同樣促進了中國文化一系列重大的發展,而所謂臣服于“西方文化霸權”的1980年代也繼續奠定著中國現代詩學的堅實體系。未來中國詩學的發展將繼續走在面向世界、中西對話的道路之上,西方與本土的持續不斷的互動依然是我們生生不息的資源性力量。
在這個時候,譚桂林先生《本土語境與西方資源》重新探討中國現代詩學如何在開放的“中西詩學關系”中發展壯大,不能不說具有一種特殊的學術意義:一個舊題的新作不是學術的重復,而是在新的學術語境中對一個重大命題的新的拓展和深化,它的論述將啟示我們認真檢討近百年的中外詩學關系史,尤其是在“西化還是本土化”間反復折騰的我們曲曲折折的學術史。
《本土語境與西方資源》的學術拓展以對歷史材料的重新辨析入手,試圖通過對現代詩學現象的獨到梳理來把握“中外詩學關系”及現代詩學形態的復雜細節。到目前為止,可能是受制于一般文學思潮既定分類的影響,我們的現代詩學研究,常常局限在“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象征主
義”(“現代主義”)這樣的闡釋框架之中,這固然是更利于發掘中國詩學與西方詩學的若干相似之處,但卻并不利于呈現中外文化相互糾纏又分歧的歷史細節,多年的研究也使得相關領域的學術信息幾乎有被打撈干凈的危險。譚桂林先生另辟蹊徑,努力從中國現代詩學本身的歷史進程中提煉和總結現代詩學的“形態”,這樣,出現在我們面前的中國詩學現象,可謂是相當的豐富,除了在過去研究中一些基本形成共識的詩學現象——如象征詩學、左翼詩學、女性主義詩學之外,引起論者興趣并被重新定位的還有“生命詩學”、“神秘主義詩學”、“反諷詩學”、“漂泊詩學”等等全新的現象,其中有的命題所指涉的對象(如“反諷詩學”、“漂泊詩學”)顯然同時具有更為廣闊的文化意義,可以為我們重新探討整個中國現代文化的歷史問題提供新的思路,而論者對一些固有詩學現象的新的處理方式也耐人尋味,如象征詩學與意象主義詩學在過去的研究中常常被結合在一起,譚桂林先生卻分而置之,我想這樣的處理更利于展示中國詩學發展的獨特形態,也就是說,歷史的事實在于,盡管有西方詩學的輸入和引進,但輸入和引進的西方詩學從來都不是以它們各自的完整形態在中國展示和發展的,中國詩學的發展依憑的是多種文化交織對話的邏輯,這就是“西方/本土”交相互動的真實景觀。例如首開風氣的胡適從意象主義(龐德)的六項原則中獲得了靈感,但他借鑒這些原則而提出的“八不主義”卻既不屬于意象主義,也不屬于象征主義。譚桂林先生將現代中國的意象主義詩學從象征主義的空洞框架中解脫出來,轉而納入“現代都市詩”的范疇中加以討論,應該說是獨具慧眼的。當然,本書對的一些詩學的命名,特別是它們彼此問的聯系和區別尚可以作更為清晰的辨析,以利中國現代詩學的研究,可以從中獲得新的概念的基礎。
是西方還是本土?中國與西方究竟如何完成彼此的結合?在經過了中國學術的種種曲折坎坷之后,中國詩學的這一世紀命題繼續釋放著自身的魅力,在我看來,譚桂林先生的這一新的展開,將有效地喚起我們對問題的新的探求欲望,而且,我們分明已經可以感知到可能存在的新的闡釋空間。例如,我們不僅可以總結中國詩家如何糾纏于西方詩學概念與本土情結之間的矛盾,也同樣可以仔細分析他們如何透過這些概念的糾纏而努力表達自己樸素意念的思路。因為,嚴格說來,在現代的中國詩學發生發展的時候,其實首先并不是這些詩論家必須對古代或者西方的詩論加以繼承或者排斥的問題,而應當是這些關注詩歌、思考詩歌的人們究竟如何看待、如何解釋正在變化著的詩歌創作狀況的問題,最早的中國現代詩論都如同胡適的《談新詩》一樣,關注和解釋的是“八年來一件大事”,因為“這兩年來的成績,國語的散文是已經過了辯論的時期,到了多數人實行的時候了。只有國語的韻文一所謂‘新詩——還脫不了許多人的懷疑。”是豐富的文學的事實激發起了理論家的思考的興趣、解釋的沖動和新的理論建構的欲望。中國現代的詩論家首先是為了說明和探討關于詩歌本身的新話題而不是為了成為或古典或西方的某種詩歌學說的簡單的輸入者,在這些新的文學事實的感受中,在這些新的理性構架的架設中,我們的理論家同樣是“完全自由”的,我們同樣不能漠視他們的這種自由性。胡適之所以將“文的形式”作為“談新詩”的主要內容,首先并不是因為他掌握了西方的意象派詩歌理論,而是因為他感到必須讓走進死胡同的中國詩歌突破“雅言”的束縛,實現“詩體大解放”,我們完全可以發現胡適詩論與影響過他的西方意象派詩論的若干背離之處,但恰恰正是這樣的背離才顯示了胡適作為中國詩論家的“完全自由”。胡適的詩歌主張遭到了穆木天等人的激烈批評,在把胡適斥責為“中國新詩最大的罪人”之后,穆木天、王獨清等從法國引進了“純詩”的概念,他們這樣做的根本原因還在于“中國人現在作詩,非常粗糙,這也是我痛恨的一點。”“中國人近來做詩,也同中國人作社會事業一樣,都不肯認真去做,都不肯下最苦的工夫,所以產生出來的詩篇,只就technique上說,先是些不倫不類的劣品。”正是這種明確的“中國意識”使得穆木天、王獨清等人的“純詩”充滿了他們所“主張的民族彩色”,而與“純詩”在西方詩學中的本來意義頗有距離。從某種意義上說,胡適的“自由”、“口語”與“詩體解放”代表了中國現代詩論的重要的一極,而自穆木天、王獨清開始的對于胡適式主張的質疑、批評,進而力主“為藝術而藝術”的“純詩”理想,這又代表了中國現代詩論的另外一極,但無論是那一極,其詩歌理論的出發點都是中國現代新詩發展的基本現實,這些理論家是按照各自的實際感受來建構他們的詩歌主張,來攝取、剔除甚至“誤讀”著西方的一系列詩學概念。同樣,在袁可嘉那里,“新詩現代化”理論也體現了最自覺的“現代性”追求。而這樣的追求的目標,也是被我們的理論家放在解決“當前新詩的問題”中作了相當富有現實意義的表述。
在這個意義上,我以為要繼續展開中國現代詩學的世紀命題,新的思考就應該是:現代的詩歌環境究竟給詩論家提供了什么?中國現代的詩論家是怎樣感受和解釋這樣的環境?他們因此而產生了怎樣的理論設計?或者說,在中國既有的詩論體系之外,現代的他們又發現了什么樣的詩學的趣味、詩學的話題?在表達他們各自的這些看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怎樣的一種新的理論話語模式?
要回答這些問題,就需要如譚桂林先生《本土語境與西方資源》一書所已經著手的工作那樣,在對歷史過程的新的歸納與命名當中(而不是在固有概念的簡單借用和認同當中),重新檢討和梳理我們曾經走過的道路。
參考文獻:
[1]余虹,中國文論與西方詩學[M],北京:三聯書店,
1999,
[2]譚桂林,本土語境與西方資源——現代中西詩學關系
研究[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
[3]李怡:“走向世界”、“現代性”與“全球化”[J]南京大
學學報,2004,(3):112,
[4]胡適,談新詩——八年來一件大事[A],楊匡漢,劉福春
編,中國現代詩論:上冊[c],廣州:花城出版社,1985,
[5]穆木天譚詩——寄沫若的一封信[A],楊匡漢,劉福春
編,中國現代詩論:上冊[c],廣州:花城出版社,1985,
[6]王獨清,再譚詩——寄木天、伯奇[A],楊匡漢,劉福春
編,中國現代詩論:上冊[c],廣州:花城出版社,1985,
[7]穆木天,譚詩——寄沫若的一封信[A],楊匡漢,劉福春
編,中國現代詩論:上冊[c],廣州:花城出版社,1985,
[8]袁可嘉,新詩戲劇化[A],楊匡漢,劉福春編,中國現代詩
論:上冊[c],廣州:花城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