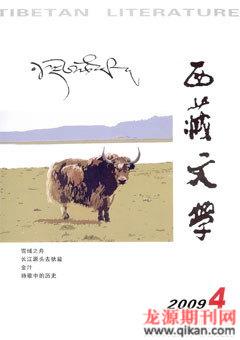牧人的愛情
梅 爾
牧人的愛情樸實而堅韌,在浮躁又多夢的都市人眼里,他們的愛情總是散發著一股淡淡的青草味和濃濃的奶香。
牧人在空曠的草原上放牧著牛羊,也放牧著自己的愛情,于是草原上便有了一個個古老而年輕的愛情傳說。
一
強巴常常坐在冬日的陽光中回憶,回憶年輕時候在牧場上與姑娘們追逐嬉戲的情景,那時候的強巴英俊健壯,驕傲中透露著霸道的自信。他正在追求草原上最迷人的姑娘——楊木措。楊木措不僅有著花朵一樣的面容,還有著百靈鳥一樣的歌喉。草原上的每一次盛會都有她們年輕而矯健的身影,她們唱歌、她們跳舞,她們甩著響鞭打馬在草原上飛奔,釋放著年輕而古老的熱情……。
往事如煙,如今的她們都已經走進了垂暮之年,楊木措一疊連聲的咳嗽早已掩蓋了她年輕時候那迷人的歌聲和優美的舞姿。滿臉的皺紋寫滿了幾十年的艱難和滄桑。強巴一邊拍打著女人的背一邊扭頭朝門外望,正巧護士小李端著藥盤從門口走過,她下意識地瞅了一眼病房,發現楊木措又在陣咳,無奈地搖了下頭朝里面的病房走去。
護士又換班了,值夜班的人已經接班了,她們接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發藥,同時也進行夜班查房。強巴已經摸索出了他們交接班的規律,并且也摸索出了幾個護士上班的次序,在值夜班的幾個護士中,他最喜歡的還是小李這個丫頭,整天樂呵呵地沒一點憂愁,不像有些護士整天吊著一張臉,好像誰欠了她的一樣。
強巴的女人又在咳嗽,一聲緊跟一聲,好像后面被人追趕著一樣。強巴不輕不重地拍打著他老婆的后背,很無奈地聽著這一聲聲的咳嗽,沒有一絲驚慌。幾十年來強巴一直用這種方式安慰和緩解著老婆的咳嗽。
女人得了個難纏的病,經常不停地咳嗽,咳出一團團的濃痰后方才舒服那么一點點,當痰咳不出來時,她的嗓子里就會發生像雞鳴一樣的聲音,“咯——咯——”的。每當這時強巴的心就像是被人撕裂著一樣有一種說不出的疼痛和難受,他甚至能聽到被撕裂的那種疼痛的聲音,于是就忍不住想起那個古老的刑法——千刀萬剮,他覺得他早已被千刀萬剮了幾百遍,并且以后還將繼續被千刀萬剮。
他們是這個醫院的老病號了,科里的大夫護士都非常熟悉他們,在辦住院手續時,護士只問了他們兩三項內容就把楊木措的資料填好了,然后很熟練又很習慣地將他們安頓在了這個并不寬敞但很安靜的小病房里。他們知道,這是為了照顧他們的生活習俗。
女人咳了一陣后停了下來,看著強巴喘著粗氣,強巴明白女人的意思忙打開床頭柜撕了塊紙遞給女人,女人將痰吐出后把紙扔進了床底下的痰盂里,然后長長地舒了口氣,臉上出現了少有的輕松和舒暢。強巴急忙扶女人依被子躺了下來,然后將一杯半溫的水遞給她。
女人叫楊木措,是強巴服侍了幾十年的老伴。此時的她并不急著喝水,而是雙手端著水很感激地看了一眼強巴,然后才慢慢抿了一口。幾十年了,強巴已經能完全讀懂女人的眼神了,并且根據她的眼神能正確無誤地判斷出她的需求。他習慣于老婆的咳嗽和咳嗽后的需求,并對這個習慣總是持著無怨無悔的態度。
冬日的暮靄匆匆來臨,頃刻間便籠罩了楊木措半躺的那張病床,也籠罩了整個病房。病區里昏黃的燈光此時不得不陸陸續續亮起。照顧完女人咳嗽后的強巴提起暖瓶去水房打水,這是這個冬天里他每日必做的事情。三十年了,足足有三十年了,對于強巴來說,好多個冬日的傍晚都是這樣度過的:拍著老婆的背聽著她的咳嗽聲,看著年輕而美麗的護士從門口走過。有一天他忽然感覺到厭倦了這樣的生活,他想他應該換個冬天的生活方式了,可換個什么樣的生活方式?怎么換?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中。
護士走進來,將藥片放在床頭柜上,簡單詢問了一下楊木措的病情后扭著腰肢走了,他看了看那些藥片后提暖瓶倒水。他的女人楊木措看著那滿滿一小盒的藥片搖了搖頭,很習慣地露出了非常為難的表情。吃藥是楊木措每天必做的功課,而期盼藥物盡快發揮作用卻成了強巴每天最強烈的愿望。
這是第幾次住進醫院的內科病房了?在高原草叢中放牧了幾十年牛羊的強巴已經記不清了,只記得這里的好幾個護士曾經還是小姑娘,現在卻一個個變成了小媳婦。
這是坐落在高原草地上的一家企業醫院,來這個醫院就診的病人并不多,自從強巴帶著他的女人住進這個醫院,這個并不寬敞的小病房就似乎成了他們的專用病房,接診護士每次都會把他們安置在這個病床上。
強巴很熟練地伺候著自己的女人服下藥物后有點沮喪地看了看逐漸落下去的晚霞。在強巴看來,這樣的晚霞已經不美了,它只發給他一個信息,那就是一天又過去了,女人的病還是沒有起色,生活的煩惱依然沒有改變。于是強巴開始厭惡冬日的黃昏和黃昏中嫵媚妖嬈的晚霞。
二
強巴和他的女人是十多年前走進這個醫院的,而在這之前強巴一直帶著他的女人到省城去治病。在強巴看來,他女人得的這個病是個很難纏的病,方圓幾十里的牧場上還沒有人得這個病。牧場附近那個三代單傳的小醫生對這個病簡直可以說是無從下手,認為只有省城那樣的太醫院才能治療這種病。就介紹他們到省城醫院去治病。強巴理解醫生的難處,就毫不猶豫地帶著女人去了省城。從那時候起他的生活軌跡似乎被固定了下來:每年秋天,他總要挑選一大批膘肥體壯的牛羊賣掉,然后趕著剩下的那些老弱病殘或者懷孕的母羊返回他們的冬窩子,過一個漫長而寒冷的冬天。而這時候楊木措嗓子里那個“咯——咯”的雞鳴聲就會開始響起,臉色也由原來的紫紅色變得鐵青。好像那只小雞知道強巴的口袋鼓起來了一樣。看自己的女人那么難受,強巴不得不帶著她到省城去治病。強巴懷疑楊木措的嗓子里真的養了那么一只冬醒夏眠的小雞,而這只小雞似乎是專門來吃他這一年心血的。
牧場綠了又黃,黃了又綠,牛羊也養成了好幾茬,可強巴的日子卻似乎沒有多大改變。每個冬天強巴唯一的選擇就是帶著楊木措去省城治病,而把那個一貧如洗的家撂給那一對逐漸長大的兒女和親戚朋友。他不想他的女人早死,也不想西北風夾雜著女人的“咯——咯——”聲響徹他的整個冬天。好在強巴的懷里揣著賣羊得來的幾千元錢。而在這之前他早已經計劃好了這幾千元錢的用處:冬窩子的房子得翻新,牛羊的簡易草棚得翻新,得買個新式的大烤箱,還想準備點煤炭,據說煤炭取暖比牛羊糞取暖要省事的多。可這一切在楊木措“咯——咯——”的喘息聲中統統化為了泡影,他不得不像往年一樣過這個冬天。
求醫的路很漫長,在省城的那些冬天過得就更漫長。他常常想起那些日子,想起那一個個漫長而寒冷的冬天。在強巴看來,省城的什么都好,就是錢太不經花。那可是賣掉了三十只肥羊才籌起來的血汗錢,自己整整一個夏天的勞動成果,現在卻換成一瓶瓶的藥水流進了楊木措的身體里,去處理楊木措嗓子里那只“咯——咯——”叫喚的小雞去了。強巴一想到這些就想喝酒,可大夫不容許他喝
酒,說這是在醫院里,一個牧人喝得醉醺醺的像什么?你以為這是在你們草原上?大夫是個小青年,估計年齡跟他的兒子一般大,說話斯斯文文的,一看就是個有文化的人,不像自己的兒子,只上了個小學五年級就跟著他去放牧了。其實兒子當時還可以上的,可他自己主動提出不上了,說什么去中學的路太遠,一個月只能回來一趟,他擔心冬天父母親去看病時家里沒人照顧,自己是老大,就應該有個老大的樣子,幫父親挑起這個家。兒子的話讓強巴著實吃了一驚,也感動了很久。他沒想到兒子這么快就長大了,并且有了一個男人所具有的責任心,這讓他欣慰,也讓他難過。因為長大的兒子要娶妻生子,可他拿什么給兒子娶妻生子?如果兒子當初繼續讀書,也能像這個小大夫一樣大學畢業成為公家的人就好了,那他就根本用不著愁娶妻生子的錢,也用不著每年跑這么遠來給老伴治病,他們可以讓兒子回家去給老伴作治療。當然,那樣的話他們也不用整天跟在小大夫后面說好話,而是坐在沙發上看著電視告訴兒子病情就行了。強巴一想到這些就更后悔沒有堅持讓兒子上學,于是就越發地想喝酒。
記得在省城的一個冬天,有一天強巴轉了好幾個商店才找到他愛喝的那種青稞酒,然后便獨自坐在馬路邊的一家小飯館里喝了起來,他沒有像在草原上那樣握著瓶子灌,而是學城里人的樣子要了一盤花生米,并要了一個玻璃杯,將酒倒到杯子里一口一口地抿了起來。在他看來,這個動作是很斯文,但同時也很虛偽,遠沒有那種拿起瓶子往嘴里灌的動作豪爽和過癮。于是抿了幾口后他就有點耐不住性子了,可又不好意思拿起瓶子灌,只好端起杯子一口接一口地喝。
店很小,卻很適合喝悶酒,除了他店里還有一個人也在喝悶酒,是個年輕的小伙子。不知道他遇到了什么煩心的事?是不是和他一樣有一個常年生病的女人,是不是也在為女人的病和醫藥費發愁?不,也許他還沒結婚呢?如果那樣他一定是因為得不到自己喜愛姑娘的青睞而喝悶酒。強巴這樣想著,嘴角露出了一絲久違的笑容。強巴郁悶的心情豁然開朗,于是就拿起杯子猛猛地喝了幾口,這時候的他忽然有了在草原上喝酒的感覺。
一夜未歸,到底醉臥在哪里了他自己也說不清楚,卻挨了大夫狠狠地一頓訓,小護士歪著腦袋瞪著眼睛警告他:如果再喝酒就立刻出院,醫院可負不起這個責任。強巴被小護士的厲害著實嚇了一跳,不敢作任何反駁,只是一個勁兒地點著頭沖護士說:“呀!呀!呀!”
好幾年里強巴的日子就是這么周而復始地度過的。每個夏天的放牧和每個秋天的收獲似乎都圍繞著冬天的這次出行而忙碌。在大家看來他們全家人的勞動都體現在這次出行上,只有這次出行的成功與否才能體現他們全家人的勞動價值。每一次出行前他們都希望這是最后一次,楊木措喉嚨里的那聲雞鳴聲從此消失,而她百靈一樣的歌聲又響起在他們那塊美麗的草場上,至少應該響起在他們那頂已經陳舊的帳篷里,那時候強巴一定騎在馬上甩著響鞭也唱上那么幾句。可每一次的希望很快就會被醫生那搖動的腦袋否定掉,醫生會用無奈的語氣告訴他病情比去年又重了點,治療一陣子可能會得到緩解。可能會?這是多么含糊的話,難道就沒有治愈的可能了?強巴的心有點麻木,麻木的不知道怎么打理眼前的生活,只好聽從醫生的安排。
一整套的檢查,沒完沒了的拍片、超聲、心電圖等,然后就開始漫長的抗炎支持療法。直到將強巴口袋里的錢折騰光時,大夫才會告訴他楊木措該出院了。楊木措喉嚨里的雞鳴聲已經消失了。
強巴的幾個冬天過得都是這么麻木而無奈,強巴真不知道該找誰去訴說心中的無奈。
三
上醫學院的侄子畢業后被分配到了這一家企業醫院。侄子告訴他這家醫院是對外的,離他們家只有三十公里,快馬加鞭也就一個上午的功夫。更讓他高興的是侄子說這家醫院完全能治療楊木措的這個病,并告訴他這個病并不是什么大病,只是呼吸系統的一個慢性病而已,由于拖的時間太長,所以才顯得這么難纏。
這個冬天強巴破例沒有遠行,而是帶著楊木措來到了侄子上班的這家企業醫院。
強巴覺得這個冬天要比以往的幾個冬天簡單和輕松些,至少少了對家里的那一份牽掛,大概半個月左右他就可以到家里去走上一趟,看看家里的孩子,給楊木措帶點風干的牛羊肉和酥油等。
這樣的日子對他們來說已經很滋潤了,早晨他們完全可以按照他們的飲食習慣沖一碗酥油茶喝,周末他們自然會改善一下伙食吃一些牛羊肉,平時又不間斷地吃一些肉干。這樣的冬天對強巴來說要比以往的冬天幸福得多,也輕松得多,強巴的臉上有了一絲淡淡的久違的笑容。
強巴在這個醫院度過了十幾個這樣簡單而輕松的冬天,這十幾個冬天里強巴除了少了一份牽掛依舊很憂傷也很無奈。當這個冬天來臨時,楊木措喉嚨里的雞鳴聲又叫了起來,他又一次走進了侄子工作的這家醫院。
四
他信這個醫院,從走進醫院的那一刻起,他就對這個醫院產生了一種莫名其妙的信任感。大夫和護士們那整天微笑著的臉讓他看著舒服,那和藹親切的話讓他聽著順耳,雖然好多衍他同樣聽不懂,但他能理解他們的意思,并且可以稱得上是完全的理解。這讓他和他的女人有一種說不上來的踏實感,感覺就像是到自己家帳篷里了一樣。
楊木措時常懶洋洋地躺在床上看著窗外的陽光對他說:“今年冬天的陽光這么好,我的病也一定好得比往年快,等過了這個冬天,我就可以跟你去放牧了。我們又可以像年輕時一樣騎著馬追著太陽跑了。”“呀!”看著楊木措充滿向往的眼神,他也會忍不住向往起寒冷過后的那個春天,春天多美啊,綠草成蔭、野花朵朵,牛羊悠閑而自在地逗留在草地上,牧民們甩著響鞭放聲唱著沒有什么曲調的歌,同樣過著悠閑而自在的生活。許多城里人說那簡直就是神仙的日子,無憂無慮,與世無爭,浪漫而悠閑。可現在楊木措的病似乎消耗掉了他心中最后的那一絲浪漫,他不得不無奈地期盼清晨,迎候夕陽。每天他看著最后一絲夕陽落下去時他就會發出一聲長長的嘆息,沒有人知道他是在嘆息落日還是在嘆息他女人的病,但大家卻能聽出他那聲嘆息中的無奈和憂傷。
楊木措的怒火就是從這一聲聲的嘆息中蓄積起來的,她恨自己,恨自己不爭氣的身體,患上這么個半死不活的病,拖累得全家人都沒過上好日子。可她聽到強巴的那一聲聲嘆息時還是忍不住怒從心起,她認為強巴已經厭煩她了,并且早就開始厭煩她了,從這一聲聲的嘆息中就能聽出來。她不怪強巴,一點兒也不怪強巴,強巴是只鷹,是一只能翱翔天空的雄鷹,是她把他拖成了一只瘟雞,幾十年來只能在原地打轉轉。想想連自己都感到害怕,從剛過三十歲開始到已經走進六十歲,整整三十年,三十年來他們的每一個冬天都是這么過來的:挑二三十只放牧了整整一個夏天和一個秋天的綿羊趕到自由市場出售,然后數著錢回家開始準備去醫院的所有物品:酥油、奶茶、糌粑以及風干的肉。起先這些東
西裝在羊毛紡織的褡褳里,過了幾年后褡褳換成了大大的尿素提兜,又過了幾年后尿素提兜換成了人造革的漂亮大提包,現在卻開始用上了新式的雙肩背包。時間過的可真快,光包都換了四茬,人自然老得都能在水杯中看清白發和皺紋了。楊木措的怒火不能不說摻雜著病中的壞脾氣,不僅很不講理,還無端地發脾氣,摔東西,弄得強巴不知所措。
強巴常常獨自坐在冬日的陽光中遐想,想他們年輕時候的美好時光,想他們遺落在草原上的那一幕幕浪漫,想那些流傳在草原上的愛情故事,還有故事中那些年輕而勇敢的主人公。往事如煙,曾經冬天里的那一個個夢想越來越遙遠,遙遠的讓他不得不回到現實中來。他的女人楊木措老了,他自己也老了,老的已經步履蹣跚,思維遲鈍了。老的已經懶得搭理身邊發生的任何事情了。
強巴其實挺郁悶的,尤其是跟楊木措生完氣后就更郁悶。就常常獨自來到醫院院子里閑坐,一坐就是大半天。他好想找個人說說話,說說他心中的郁悶,說說他的苦惱。可周圍沒有人聽他講他的苦惱和郁悶。閑坐的他感覺又回到了自己那空曠的牧場上,于是就忍不住自言自語起來:“年輕時你也是百里挑一的,我也算是草原上的一只雄鷹,可沒想到我們的好日子像射出的箭一樣短暫,還沒到三十歲你就得上了這種病,整天里咳嗽吐痰,吐痰咳嗽,可沒少折騰我。夏天放牧,秋天賣羊,冬天帶你住院看病,從三十出頭,這種日子就從沒改變過。我總想著有一天能把你的病治好,然后有錢給兒子娶房媳婦,要娶一個健康的媳婦,再讓他們生倆個娃,一家人過著幸福的生活,直到我們老去。可這個夢想現在已經破滅了,完全地破滅了。兒子已經過了娶媳婦的年齡,你的病卻越來越重了。現在物價漲的這么快,賣羊的錢越來越不夠你的醫藥費了。我老了,真的是老了,許多的事情已經力不從心了,我真擔心有一天我支撐不住了也倒在床上。那時候我們的兒子怎么辦?他到哪里去借錢給我們治病?我一想到這個問題心里就難過的很。我甚至想有一天我們能一覺睡過去,永遠再不要醒過來。你已經拖累了我幾十年,我不希望你再拖累兒子。他要娶媳婦,修房子,現在草原上也流行修房子,在自己的牧場里修幾間漂亮的磚房,再做個大火炕,冬天把煙筒放進火炕里,將爐子燒得旺旺的,一家人坐在火炕上聊天唱歌喝奶茶,那是多么幸福的日子。可要是你的病不好,我明年還得湊錢來給你治病,那么這樣的話,這一切的想法都是空的,我們的冬天會越來越凄惶,越來越寒冷。說到這里強巴的眼圈紅了,眼淚也忍不住流了下來。強巴真想放聲大哭一場,把自己對生活的怨恨都哭出來,全部地哭出來。他怨恨老天給他安排的這種日子,他不知道他錯在哪了,只是感覺到老天對他太不公平。對兒子也太不公平。跟兒子同歲的人都結婚了,都有了自己的女人和孩子,有了自己幸福的生活,唯獨兒子依然跟他們一起過著凄風苦雨的日子。可強巴終究沒有哭出來,而是忽然擦干眼淚站起身朝病房走去。
吃藥的時間到了,他還得伺候楊木措吃藥。
五
楊木措沒有熬過這個冬天,她那折騰了強巴幾十年的肺心病終于在這個隆冬的午后加重了,并且出現了心力衰竭和昏迷。
強巴傻傻地站在走廊里看著急匆匆在病房里進進出出的護士們,自言自語地叫著楊木措的名字,叫她趕快醒過來。他們還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要等過了這個冬天后去給兒子看媳婦,要一起到夏窩子里去扎帳篷,要去區里趕集……。
楊木措終究沒有醒過來,而是永遠地閉上了那一雙因呼吸不暢而憋得有點泛紅絲的雙眼。強巴梳理著那一頭干枯的灰發,平靜得像一尊塑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