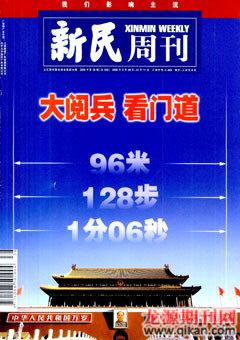法治之路始于依法治官
王 琳
曾經轟動一時、被媒體高度聚焦的內蒙吳保全網絡誹謗案,在經過了一審、二審等法律程序后,9月16日由內蒙古自治區鄂爾多斯市東勝區人民法院再度重審。最新的結果是,被告人吳保全誹謗罪名成立,吳保全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零六個月。而這次,吳保全當庭表示不上訴。
自彭水詞案以來,公民因言獲罪不斷重演,舉凡稷山文案、五河短信案,直至今年的靈寶帖案等等,都曾為公眾所耳熟能詳。這些個案在經媒體曝光之后,也幾乎獲得了一邊倒的輿論支持。輿論的外力又促進了案件的公正處理。如我們所看到的,在這些案例中,地方公安司法機關或撤案,或道歉,或賠償,“誹謗者”基本被洗刷了“罪名”。
然而吳保全案卻是例外,當地法院在歷經一審、二審和再審之后,吳保全的誹謗罪名依舊。從報道公布的信息來看,地方檢方指控和法院認定的事實與理由均沒有多大變化,那么當地法院對此案提起重審的理由又何在?
我國實行的是二審終審制,二審結果已是終審裁判,作為例外存在的“再審”只有當法定事由發生時才能提起。依刑事訴訟法,這些法定理由包括:有新的證據證明原判決、裁定認定的事實確有錯誤的;據以定罪量刑的證據不確實、不充分或者證明案件事實的主要證據之間存在矛盾的;原判決、裁定適用法律確有錯誤的等等。簡言之,只有當法院認為原審裁判很有可能存在違法或錯誤而必須糾正時,才會引發重審。如果重審僅僅是原審的翻版,這個案件本就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定性準確,豈不說明中院提起的重審純屬“瞎折騰”?這引人深思。
當然,如之前的眾多評論和專業人士所分析的那樣,當地司法官員在吳保全案中“涉嫌違法”之處甚多。如誹謗罪在刑法上是個以自訴為主公訴為輔的罪名,吳保全即便有誹謗之實,也遠遠達不到“嚴重危害社會利益和國家利益”的程度。誹謗一位地方官員,哪怕某地的“一把手”,也是誹謗個人,其危害也主要及于這位官員個人。不存在一危害到地方官員的聲譽就等同于“嚴重危害社會利益和國家利益”。重審本來為糾正這些“涉嫌違法”的司法行為提供了一個機會,現在看來,這個機會已再次被錯過。
在筆者看來,司法官員必須具備這樣常識與認知:其一,官員也是人,不管他是何等級的官員;其二,某位官員并不代表社會,更不代表國家,而只代表他自己。若有官員認為遭到他人的“誹謗”。完全可以自行向法院遞交自訴狀。既然官員沒有行使自訴的權刊,這宗誹謗案在司法上就不應該成立。吳保全案中,當地公安部門和檢察機關主動出擊,應當說超越了法定職權,理應得到糾正。
其實誹謗行為在社會上多有發生,受眾自有其理性判斷一些出格的言論,多數情況下完全用不著司法介入。如有些地方官員動輒誹謗老百姓為“不明真相的群眾”,“一小撮別有用心的黑惡勢力”以及“刁民”等等。假如按照吳保全案中的司法邏輯,設想一下這樣一幕:一旦發現官員有上述言辭,稽查機關就可立即出動,將該官員刑拘。并從嚴從快處理,至于刑法上對誹謗罪的規定是以自訴為一般原則,公安司法機關也完全可以不予理會,到了法庭之上,公訴機關可以這樣指控:被告人某某官員為推諉責任,逃避法律追究,利用網絡、報刊、廣播電視等媒體。憑空想象、捏造事實,誹謗群眾,情節惡劣,不僅嚴重損害了一小撮“刁民”和一大批不明真相的群眾所依法享有的人格和名譽,而且嚴重危害了當地的社會秩序。
無須多言,上述假設在現實語境下純粹只是個“假設”。現實中,不會出現如此荒唐的情形。但實踐中。常可見到某些官員抱怨法治觀念不能根植于社會。權利意識不曾深入人心,但在一些官員的心底,卻仍是“法律工具主義”的領地。今年“五五普法”的主題是“法律進機關”。我作為某省“領導干部學法用法征文活動”評委會的副組長,認真審閱了兩百多篇應征稿件,卻發現這些領導的文章絕大多數都在侃侃而談應該如何用法律來管民,而極少涉及如何依法來律己。法,在一些官員看來,只不過是用來治理民眾的工具,而不是規范自身行為的準則,
為這種潛伏于官員心中的觀念追根溯源,還在于公眾并未真正成為法律的主人,在許多時候,公眾也無法運用法律武器來監督權力、制約權力。在我們這個“民以吏為師”的觀念源遠流長的國度里,要讓法治觀念根植于社會。必先讓法治觀念根植于官員。法治之路始于依法治官,也將成于依法治官。舍此,別無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