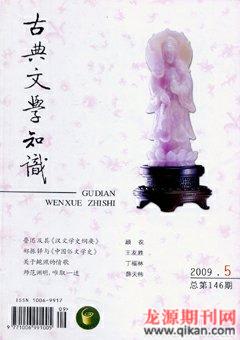浩浩蕩蕩 從從容容
彭新有
《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又名為《陪侍御叔華登樓歌》,是李白被“賜金放還”后,游歷至宣城時創作的一首餞別詩。全詩為: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長風萬里送秋雁,對此可以酣高樓。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
它是李白歌行的代表性作品,歷來深受世人激賞,《唐詩選脈會通評林》稱贊它“厭世多艱,興思遠引”,《唐宋詩醇》評價它“遙情豎,逸興云飛”。該詩題目為“餞別”,但全詩思想情感卻不僅僅是離別,還有更為豐富復雜的情感內涵包蘊其間。與李白的其他歌行作品一樣,該詩結構騰挪跌宕,是“風雨爭飛,魚龍百變;又如大江無風,波浪自涌,白云從空,隨風變滅”。這些復雜因素使得人們對全詩的情感把握有了一定的難度。本文嘗試通過對字詞的細致品味來還原李白創作時的情感狀態,理清其中思想情感發生發展的脈絡,從而對詩中的情感內涵進行簡單探析。
一、 悲感
宋嚴羽《滄浪詩話?詩評》云:“太白發句,謂之開門見山。”《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一詩的開篇亦是如此。“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詩人開篇接連使用兩個十一言長句,就令人感覺如破山之斧迎面劈來,天為之開,地為之辟,人心為之震栗,還未來得及細細回味,就已經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擊倒。這是一種怎樣的力量?它是如何形成的?細心體味就可知道,這是詩人心中長期沉積郁結的各種悲感,驟然勃發怒放,而在詩歌中產生的一種沖擊力。表面上看,這兩句詩起勢突兀,與餞別無涉,實則是詩人內心情感怒潮無法遏制而發生的突然傾瀉,李白正是把他這種瞬間感受表現了出來。那么到底是些什么樣的情感沖破了李白的情感堤岸呢?
時光流逝之悲。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子罕》)對每個人來說,時光的悄然流逝都是難以回避的悲哀,希望建功立業的英雄,性情敏感多思的詩人,對時光的流逝和不可把握的體驗尤其顯得深刻和殘酷,更何況李白是一個希望建功立業的多情詩人。“昨日之日不可留”,詩人在驀然回首之間,發現昔日“銀鞍白馬度春風”(《少年行》)的瀟灑已經褪色,唐玄宗“降輦步迎,如觀綺皓”(李陽冰《草堂詩集序》)的榮耀已經消失,青春在時間的流逝中遙遠,理想在時間的流逝中沉重,功業在時間的流逝中模糊……一切的一切,恍如春夢,而美夢易醒,好事難再,乍見自己“朝如青絲暮成雪”(《將進酒》),怎能不悲從中來,痛從中來?
漂泊離別之悲。昨日已逝,感傷已是無可奈何,還是得面對眼前的現實,然而眼前卻是“今日之日多煩憂”。不僅有煩惱,而且煩惱簡直紛繁至極。當初“仗劍去國,辭親遠游”(《與韓荊州書》),就是為了“愿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李白《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而今輔弼未成,海縣未清,自己卻是流落塵俗,亦足悲矣!還更有可悲者在,就是眼看就要與好友離別。親友本是同路人,而今離別各紛飛,離別之痛不僅為思念,為擔憂,更為兩處的孤獨。凄然漂泊天涯的詩人已經是孤單至極,幸遇友人,旋即又要別離,此中苦痛處只有詩人可知了。如果轉而追問:這是上天的安排,還是命運的捉弄?那么詩人對悲苦命運的追索已經陷入以額扣關式的憤怒了。這種憤怒必然化作詩中一股動人心魄的力量。
人生無奈之悲。詩人把“昨日之日”與“今日之日”的兩個時空對舉,可以說是對自己的整個人生的濃縮與概括。此時,詩人一生的升沉起伏之狀況已歷歷在目,詩人在對自己的人生進行總結和反思,然而得到的是“昨日之日不可留”、“今日之日多煩憂”的悲劇性結論。一生之中,不唯有顛沛流離,還有苦多樂少,更有甚者,如此反思使得詩人更清晰地意識到自己的悲苦:“不可留”,不是自己主觀上不努力,而是客觀上就留不住;“多煩憂”,不是自己徒尋悲愁,實在是生活多憂。這種清晰的認識更讓人失落傷悲。詩人把“棄我去者”和“亂我心者”并提,“棄我去者”讓詩人明白是時光在拋棄我,離我而去,并不是我誠心挽留就能奏效;“亂我心者”使詩人清楚地認識到是世事擾亂我心,致我煩憂,并不是我執著求安就能得到。對人生反思的結果落空,對時光世事反抗的結果無奈,這種落空、無奈于心中盤旋往復,其痛苦又怎是一個“悲”字可以描述的?詩人的情感堤岸已幾近崩塌的邊緣。
景物動人之悲。“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柳永《雨霖鈴?寒蟬凄切》)。離別之際,李白與友人攜手登樓,秋風蕭瑟,山川寂寥,雁陣驚寒,“長風萬里送秋雁”既是寫實景,更有言外之意。長風送雁暗指自己與友人相送;萬里之遙,可言離別之遠,更增傷悲;物候中秋天大雁南歸,雁歸成群而行,而多情之詩人卻是孤身飄零,兩相比較,真是人不如雁多矣。凄清的秋景感發著詩人情思,使詩人傷感更深。
面對此情、此事、此景,詩人只有“對此可以酣高樓”了。當火辣的烈酒沖向喉嚨,人生的諸般況味便涌上心頭。霎那間,詩人的滿腔悲感化作洪流,沖破閘門,湮沒一切……當讀者遭遇這樣的情感洪流,誰不為之驚心動魄?遭遇這樣的心靈巨創,誰不為之心神俱奪?諸多的悲感一直糾結在心里,揮之不去,成為了李白詩歌創作的源泉。此處著一“酣”字,表面上揮灑從容,實有千斤之重;表面是對朋友離別的勸慰祝禱,實際上更多的是對自己悲感的排遣。同時,這也表明詩人由面對現實的清醒認識狀態轉而進入了一種對迷離醉夢狀態的體驗中,詩人的情感狀態由人生悲苦的宣泄而變成了迷夢里的萬丈豪情。
二、 豪情
宗白華先生在《略論文藝與象征》一文中說:“詩人善醒……但詩人更能醉能夢。由夢而醉,詩人所以能暫脫世俗,超越凡近,深深地墜入這世界人生的一層變化迷離、奧妙惝恍的境地。”李白好酒善飲是出了名的,杜甫云:“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杜甫《飲中八仙歌》)李白因酒而醉,因醉而詩,以詩來抒發自己的思想情感,以詩來表達自己的人生體驗。“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寫的就是自己醉酒之后的體驗,其中所流露出的豪邁興致,頗耐人尋味。
追慕前賢和自我認同之豪。酒酣耳熱之際,李白不禁神追古人,“蓬萊文章建安骨”,其中的蓬萊文章代指友人的文章,因為漢代東觀為朝廷收藏經籍之所,被學者稱為“老氏藏書室,道家蓬萊山”,而友人時任秘書省校書郎,唐時的秘書省就類似漢代東觀,故借“蓬萊文章”代指友人文章;“建安骨”指漢魏之際以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幹、劉楨、應玚、阮瑀)為代表的文人創造的慷慨悲涼、剛健質樸的詩文風格。此處李白既是追慕前賢的造詣,又是借前賢來贊美友人,頗多溢美之詞。同時李白對自己的才華也表示了當仁不讓的強烈自信,“中間小謝又清發”,“小謝”即謝朓,李白既是因眼前謝朓樓而產生的聯想,也是心中真情的抒發。李白對建安以來的綺靡文風格外鄙視,唯獨對謝朓清新秀發的詩風稱賞不已,甚至“一生低首謝宣城”(王士禎《論詩絕句》),此處李白既是對謝朓的贊美,又是以謝朓自擬,放眼文壇,自己的才華毫不遜色,堪與謝朓比肩。這種佯狂放誕的自我欣賞,表現了詩人對自身才華的強烈自信和自我張揚的人格氣質。率真坦露,肝膽淋漓,毫無矯作,此種豪氣唯太白獨有。當然,有人說這首詩里的友人是指李云,有人說是指李華。其實,對于體味這首詩的思想情感來說,友人具體指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從李白對友人、對自己的贊美中,感受到李白處于迷醉中的神采飛揚、豪氣干云的狀態。李白的這種神追前賢和自我認同,是對自身價值的自我肯定,也是主動承擔起推動文壇發展的責任的表現。唐孟棨《本事詩?高逸》載:“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先后合德。其論詩云:‘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與?”李白這種以改變文壇風氣為己任的思想意識是非常強烈的。
懷抱逸興和抒發壯志之豪。有才無志是小境界,有志有才乃為大氣魄。李白在對自我才華的肯定之際,又抒發了自己與友人的豪情壯志:“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李白和友人都懷抱大濟蒼生、安定社稷的豪情壯志,理想在胸中涌動,躍躍欲出,豪興在心間勃發,飄飄欲飛,遠大的理想和崇高的志向激勵著詩人,產生出了巨大的生命力量,這種偉力使得詩人感到自己無所不能,簡直連天上的明月都能摘取下來。這是一種浪漫的精神狀態,更是一種英雄主義的豪邁情懷。
由悲而豪是李白詩歌的情感發展的典型特征,李白詩歌常常是“悲感至極而以豪語出之”。笑傲謔浪是李白反抗現實悲感的姿態,豪情壯志是李白反抗現實悲感的資本。這是李白在反抗中獲得的斗志,這是李白在對命運的反抗中產生的豪情。要反抗就需有強大的力量,就需要強自奮發。所以詩人由醒而醉,在醉夢的世界里,在個人的天地里,詩人把個人理想的激情揮灑到了極致,給予自己不屈的靈魂最大的肯定。然而,畢竟這是在醉中,在夢里,醉后夢醒依然得面對現實,詩人又開始以一種新的思想狀態來面對現實生活。
三、 逸興
客觀現實是無可回避的存在,當醉后夢醒,痛定思痛,回憶過往時,詩人不禁發出了“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的喟嘆。“抽刀”是動作行為,“斷水”是目的,就如同“舉杯”、“銷愁”一樣,詩人已經盡了最大努力,付出全部心力,結果卻是“水更流”、“愁更愁”。一切的努力奮發都變成枉然,一切的執著堅持都成為徒勞。程度副詞“更”的使用,使得這種枉然、徒勞更增一倍的悲哀。詩人清醒而又無奈地面對現實,得出了“人生在世不稱意”的結論。這一結論的得出,說明詩人的人生態度起了一定的變化,即使這種變化可能只是暫時的,但這句詩記錄的瞬間感受,無疑顯示著詩人的情感發生了由豪情而至逸興的轉變。
自由超脫之逸。對于不如意的現實,詩人此時已經完全絕望;對于不稱意的人生,詩人此時已經萬分傷痛。在這種情況下,詩人做出了新的人生選擇:“明朝散發弄扁舟。”“散發”,披散著頭發放浪形骸,這是無拘無束的生活;“弄扁舟”,輕靈而隨意,正是“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蘇軾《赤壁賦》)的飄逸如仙般的生活……在想象的天地里,一切的悲苦此時都煙消云散,一切的矛盾焦慮此時都已經化解,詩人的心靈獲得了自由和寧靜,詩人的情緒也變得雍容和緩。然而,這種祥和寧靜也不過是剎那間的存在,因為,詩人對“明朝”生活的急切期待正說明了詩人當下的痛苦是多么深重,詩人對眼前的痛苦是如此難以釋懷。詩人自由超脫的飄逸情致只不過是想象的產物,詩人“散發弄扁舟”的生活與“對此可以酣高樓”的狀態在本質上并無不同,它們只是詩人反抗現實的不同姿態罷了,“酣”是醉夢,而“弄”是白日夢。
李白《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云》中的思想情感都呈現得很極端,悲則大悲,豪則大豪,逸則大逸,大起大落,跌宕起伏。如同黃河九曲,怒發時浩浩蕩蕩,驚心動魄;平緩處又從從容容,悠遠寧和。從悲感到豪情,從豪情到逸興,這浩浩蕩蕩、從從容容的情思,形成了李白文字中一股讓人欲罷不能的巨大力量。仔細體味,這些都是由詩人的情感噴涌而致,完全符合詩人的情感特質,真氣貫注,通體自然,毫無滯澀。
(作者單位:德宏師范高等專科學校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