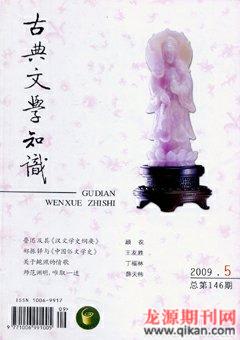師范淵明,唯取一適
薛天緯
北宋大文豪蘇軾在文學藝術領域極富創造精神,和陶詩——即“和陶淵明詩”,就是他的一種新創,繪制了古代詩歌史上的一道獨特景觀。這里先把和陶詩與陶詩對照起來算一筆賬:和陶詩未和《命子》等15題19首,《歸園田居》、《連雨獨飲》、《擬古》各多和1首,《雜詩》少和1首,算下來實際和了56題108首,其中包括了“準詩體”的《歸去來兮辭》,其數量大約是陶詩的85%。蘇軾對自己這一新創是有充分自覺的,他說:“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始于東坡。”(蘇轍《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引》)袁行霈先生論及和陶詩,曾說:“平心而論,和陶并不是一種很能表現創作才能的文學活動……在眾多的和陶詩中(引者按:蘇軾同時及身后,歷代都有寫作和陶詩者。他的弟弟蘇轍當時就有“繼和”40余首),稱得上佳作的并不很多。”(《論和陶詩及其文化意蘊》,《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6期)既然如此,蘇軾為什么專意做這件事呢?他寫作和陶詩出于何種心態,抱著怎樣的目的?這是我們閱讀和研究其和陶詩必須解決的問題。
東坡寫和陶詩始于哲宗元祐七年(1092)任揚州知州期間,當年他56歲。此后,在惠州、海南寫得更多,最后一首寫于徽宗元符三年(1100)由儋州北歸時,當年他64歲。次年即病卒于常州。寫作和陶詩貫穿了蘇軾整個晚年,詩以直白、寫實或內省的筆法寫成,是他在人生最后一個時期生活景況與心路歷程的真實記錄。循著蘇軾晚年的足跡,其《和陶詩》寫作自然地分成了三個時期。
一、 和陶之始作——知揚州時期
蘇軾知揚州時,不僅已經歷了發生在神宗朝的“烏臺詩案”等一系列重大人生磨難,而且在哲宗朝也時遭不虞。元祐六年,剛剛回到朝廷的蘇軾“在翰林數月,復以讒請外”(《宋史》本傳),看來朝中真沒有他的立足之地。這年六月外放潁州,次年徙揚州。有了這樣的人生經歷,又在這樣的現實處境中,詩人亟待找到一種精神依托,以應對難測的人生。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陶淵明:“吾于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為人,實有感焉。……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淵明,欲以晚節師范其萬一也。”(同前蘇轍文)詩人明白,無論在怎樣的情勢下,自己都不可能如陶淵明那樣辭官歸隱,所以在抱愧于淵明的同時,精神上盡量“師范”這位先賢,向他靠攏,“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淵明”(同前蘇轍文),此即蘇軾開始寫作和陶詩的心理動因。
和陶自《飲酒二十首》始。和詩《序》曰:“在揚州時,飲酒過午輒罷,客去,解衣磐薄,終日歡不足而適有余,因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庶幾仿佛其不可名言者。”第一首開宗明義,統攝全局:
我不如陶生,世事纏綿之。如何得一適?亦有如生時。寸田無荊棘,佳處正在茲。縱心與事往,所遇無復疑。偶得醉中趣,空杯亦常持。詩人自知在行動上確實無法效法淵明,難以擺脫世事的羈絆,但如淵明那樣追求精神之“一適”,卻是可以效法的。“適”遂成為蘇軾與淵明之間的心靈默契。“適”之要領,就是主觀之“心”毫無掛礙,無條件地順應客觀外界之“事”,由此進入“佳處”,達到“適”的境界。結句回應詩題,表明飲酒之事本身并不真正重要,關鍵是體驗所謂“醉中趣”,其實就是追求內心“適”的感受。這首詩可視為蘇軾和陶詩的總綱。
由于在揚州期間生活得波瀾不驚,所以《飲酒二十首》較少紀實成分,而側重抒寫對人生的感悟。如以小舟夜行比喻人之不得已而奔波于仕途:“嗟我亦何為,此道常往還。未來寧早計,已往復何言!”(其五)由此而確定了對仕進的態度:“倒床自甘寢,不擇菅與綺”(其六),“乘流且復逝,得坎吾當回”(其九)。草席也罷,綺被也罷,躺下去就能睡得香;能進則進,遇到障礙就折回來。不管遭際如何,全都能順應,以不變應萬變,保持內心“適”的狀態。
二、 和陶之繼續——惠州安置時期
蘇軾知揚實際時間僅半年,遂即還朝,迎來了仕途上最為輝煌的一段經歷,官至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禮部尚書。然而好景不長,次年即因朝政變化,不得不乞補外。紹圣元年(1094),遭御史彈劾,經三改謫命,被貶到嶺南的惠州安置。58歲的詩人在短時間內經歷了這次大起大落后,進入了艱辛備嘗的人生最后一個時期。如果說蘇軾在揚州和陶《飲酒》尚屬一時興起,那么,其在惠州之和陶則形成了完整的寫作計劃:“始余在廣陵和淵明《飲酒二十首》,今復為此,要當盡和乃已。”(《歸園田居六首序》)又一次陷入人生逆境的蘇軾,被現實處境所驅而更加貼近了陶淵明,因而做出了將陶詩“盡和乃已”的決定。落筆第一首,即重申了追求內心之“適”的要旨:
環州多白水,際海皆蒼山。以彼無盡景,寓我有限年。東家著孔丘,西家著顏淵。市為不二價,農為不爭田。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我飽一飯足,薇蕨補食前。門生饋薪米,救我廚無煙。斗酒與只雞,酣歌餞華顛。禽魚豈知道?我適物自閑。悠悠未必爾,聊樂我所然。由詩句不難看出,蘇軾在惠州的物質生活很困窘,連吃飯都成問題,柴米也要靠人接濟。但他的心情卻不賴。心情決定了他對環境的感受,覺得惠州山水優美,民風淳樸,實在是個令人羨慕的好地方。這與陶淵明原詩對故園的贊美態度完全一致。此中奧妙,即“我適物自閑”,主觀心境之“適”起著決定作用。即使實際情況未必如此,我也能自得其樂。有了這樣的態度,就把握了人生的主動權。淵明這組詩本五首,蘇軾有意多寫了一首,來凸現自己和陶的初衷:“昔我在廣陵,悵望柴桑陌。長吟飲酒詩,頗獲一笑適。”既然當初在揚州一開始寫和陶詩就獲得了“適”的效果,“矧今長閑人”,豈不更需要把這件事做下去?
從惠州所作開始,蘇軾的和陶詩有了更多的實際生活內容。尤其當詩人的現實景況與淵明當年的遭際相似時,他與淵明更有了異代相接的感受。比如,淵明在極度貧困中作《詠貧士七首》以自勵,蘇軾重陽節作《和詠貧士七首》,與陶詩最為切近,詩《序》寫道:“予遷惠州一年,衣食漸窘,重九俯邇,樽俎蕭然,乃和淵明《貧士》詩七篇。”詩人在“典衣作重九,徂歲慘將寒。無衣粟我膚,無酒顰我顏”(其五)的貧困之中,仍能從淵明那里得到一絲慰藉:“誰謂淵明貧?尚有一素琴。心閑手自適,寄此無窮音。”(其三)這里不說心之“適”,而說“手自適”,是把“適”的感受外化了,而心之“閑”恰與“適”同義。《宋史》本傳載,蘇軾在惠州“居三年,泊然無所蒂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其所以能達到這樣的境界,不能說其間沒有寫作和陶詩的作用。
三、 和陶之完成——居海南時期
蘇軾于紹圣四年(1097)被貶為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渡海來到海南,居住在昌化縣。“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宋史》本傳),他的生活境況較惠州更為惡化。在這般處境中,更需要憑借和陶來安頓精神,這一時期他寫作和陶詩也最多。初到海南,即和了《怨詩楚調示龐主簿及鄧治中》:
當歡有余樂,在戚亦頹然。淵明得此理,安處固有年。嗟我與先生,所賦良奇偏。人間少宜適,惟有歸耘田。我昔墮軒冕,毫厘真市廛。歸來臥重茵,憂愧自不眠。如今破茅屋,一夕成三遷。風雨睡不知,黃葉滿枕前。寧當出怨句?慘慘如孤煙。但恨不早悟,猶推淵明賢。這首詩對于我們解讀蘇軾的和陶詩也是十分關鍵的,因為它再次提示我們,蘇軾無論遭到何種貶謫,他的官員身份并沒有變化,所以詩中說:“嗟我與先生,所賦良奇偏。”但貶謫使他的實際生活狀況接近歸田后的陶淵明,因而促使他在精神上對陶更加靠近。詩中反思,“我昔墮軒冕”,臥在舒適的重茵上尚不能安眠,眼下在風吹雨打的破茅屋里反倒睡得香,這是為什么呢?他明白這正是學習陶淵明的緣故。自己雖不能如陶淵明一樣而“歸耘田”,但可以在精神上效法這位先賢,不論客觀處境之“當歡”或“在戚”,都使“人間少宜適”的處境變得“宜適”了。
蘇軾在海南的和陶之作中,最可注意的是當他的具體生活遭際與陶淵明相同或相近時,引起情感共鳴,在困境中借和陶以尋求精神自適的篇章。比如,蘇軾始到海南,“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筑屋,儋人運甓畚土以助之”(《宋史》本傳)。而陶淵明《和劉柴桑》也寫到治屋,有“挈杖還西廬”、“茅茨已就治”的句子。蘇軾就針對筑屋這件事寫了和詩《和劉柴桑》。詩云“稍理蘭桂叢,盡平狐兔墟”,可知這所屋子是建在荒野之中。房屋雖然簡陋,但詩人很滿足,他十分欣慰地寫道:“漂流四十年,今乃言卜居。且喜天壤間,一席亦吾廬”,“竹屋從低深,山窗自明疏。一飽便終日,高眠忘百須。”筑屋之舉實出于被迫與無奈,現在卻成了一件樂事。比如,關于農事的兩首詩《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丙辰歲八月中于下潠田舍獲》,陶詩抒寫參加農業勞動的感受,曰:“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但愿長如此,躬耕非所嘆”,“貧居依稼穡,戮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蘇軾和詩同樣抒寫親近或參加農業勞動的感受,曰:“人間無正味,美好出艱難”,“休去復休去,食菜何所嘆”,“聚糞西垣下,鑿井東垣隈。勞辱何時休?燕安不可懷。”不僅與陶詩敘事相近,感受相通,就連聲口都一樣。他們都從艱苦的農業勞動中體會到了人生真味,獲得了精神的充實和滿足。
需要指出的是,蘇軾有時對陶淵明又會有所超越。比如其《歲暮和張常侍》序曰:“(紹圣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酒盡取米欲釀,米亦竭。時吳遠游、陸道士皆客于予,因讀淵明《歲暮和張常侍》詩,亦以無酒為嘆,乃用其韻贈二子。”待客無酒,本是很尷尬的,陶詩有句:“屢缺清酤至,無以樂當年。”蘇軾和詩對此表示不解,曰:“何事陶彭澤,乏酒每形言?”又轉而對著兩位客人說:“米盡初不知,但怪饑鼠遷。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沒有酒也能醉,看來蘇軾和陶而較之乃師竟有青出于藍之勢。他和陶的《歸去來兮辭》,一方面重申了以淵明為師的初衷,但實際上也已經超越了陶,因為陶畢竟有一個實實在在的園田可歸,而他卻是“以無何有之鄉為家”(《序》),“我歸甚易,匪馳匪奔;俯仰還家,下帷闔門”,一切都是虛擬的,一切都是純精神活動。就在這虛擬的“歸去來”中,他體會到了“均海南與漠北,挈往來而無憂”的解脫,領悟了“吾生有命歸有時,我初無行亦無留”的人生要義。由此他做好了“請終老于斯游”的打算,只有這樣,他才能獲得精神之適。
然而,正如我們反復強調過的那樣,蘇軾并未脫離仕途,他和陶卻不可能走上與陶一樣的道路。徽宗元符三年(1100),蘇軾64歲時被朝廷招還,他義無反顧地告別淵明(當然是在精神上),踏上了北歸之路,其和《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寫道:“淵明墮詩酒,遂與功名疏。我生信良時,朱金義當紆。天命適如此,幸收廢棄余。獨有愧此翁,大名難久居。”蘇軾在行動上雖然背棄了淵明,但追求自我精神之適的人生態度卻是不變的,他并沒有背棄自己在和陶之初就說過的原則:“縱心與事往,所遇無復疑。”也就是這里所說的“天命適如此”,一切都聽任命運的安排,無所疑慮地接受已經到來和即將到來的“天命”。
雖然和陶詩并非每篇都與陶淵明原作內容相關,但總體觀之,這些詩或回首往事,或著眼當前;或寫為官,或寫閑居;或記交游,或懷古人;或抒儒者情懷,或發仙道向往,其精神實質均不離對“適”的心境的追求。中國士人的傳統人生之路是仕途經濟,進入仕途,就意味著必須放棄自我,然而如蘇軾一流人物又要堅持自我,這就注定了他們必定仕途多舛。和陶詩反映了蘇軾在仕途中完全不能主宰自己命運的情況下,在絲毫無力改變現實的境地中,轉而進行精神上自我療救的努力。他請出高士陶淵明為精神偶像,設下一道精神防線,居安而思危,臨變而不驚,由此稍稍獲得一點人生的主動。以和陶而求取自我精神之“適”,顯示了蘇軾對人生的放達態度,但說到底,不過是蘇軾處世的一點智慧罷了。
(作者單位:新疆師范大學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