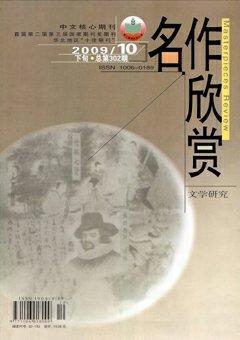用“語言的利斧”歸還一切
編者按:戈麥(1967-1991)是一個久被忽略的重要的漢語詩人。他在現代詩歌和現代小說這兩種極為不同的思維軌道上,走的是雙向修遠的道路。他的詩歌顯示出深厚的文化功底和語言素養,以及豐富的文風。1991年9月24日,年僅24歲的戈麥自沉于北京西郊萬泉河,決絕地他毀棄全部書稿,也沒有任何遺言,為世人留下幾多遺憾。本期我們特邀三位詩評家對其作品作不同方面的分析,以聊慰讀者。
《最后一日》寫于1990年8月,曾被戈麥的好友、詩人西渡認為“這是一個神明最后一次悵望人間。這是他留給朋友們的遺言。”①這個結論從今天的眼光看來,至少包括詩歌主題意蘊以及藝術價值兩個層次的內容。毫無疑問,戈麥是一個以全部生命實踐其創作的詩人:從《戈麥詩全編》收錄其遺作的情況來看,戈麥的文學生涯不過短短的4年(1987年7月至1991年9月),但其自覺的精神、獨創的風格以及生命的沉思卻足以使其作品成為“語言的利斧”——“詩歌應當是語言的利斧,它能夠剖開心靈的冰河。在詞與詞的交匯、融合、分解、對抗的創造中,一定會顯現出犀利奪目的語言之光照亮人的生存。詩歌直接從屬于幻想,它能夠拓展心靈與生存的空間,能夠讓不可能的成為可能。”②戈麥對詩歌的認識決定了詩歌在其心中的位置,因而,詩歌、語言與生存最終在其筆下可以得到完整的統一、融合,不過是自然的邏輯。
一
顧名思義,“最后一日”在客觀敘述上呈現某種終結的意味,而從詩人主體的角度來看,則帶有強烈的“訣別”意識。盡管,翻開《戈麥詩全編》,《末日》、《歲末十四行》、《死亡詩章》、《死后看不見陽光的人》等作品單純從題目上看,就具有強烈的“死亡意識”,但具體到《最后一日》本身,其瀕臨“界限”的書寫仍然如此與眾不同:
我把心靈打開
我把幸福留下
我把信仰升至空中
我把空曠當作關懷
在“最后一日”,詩人的生命姿態竟然如此澄明清澈。他以近乎超然的心態面對生命、死亡和蕓蕓眾生,那種“凌空蹈虛”般的姿態體現了沉思冥想后某種日趨成熟的“勇氣”——“既然我們的生命每一天都要被奪走一部分——既然我們每一天都處于死亡之中——我們停止生存的最后那一刻本身并未帶來死亡,它僅僅完成了死亡的過程。與這最終時刻相聯系的恐怖只是一種起于想象的東西。當把我們投射給死亡的恐怖面罩摘掉后,恐怖也就消失了。”③這顯然是屬于詩人的“最后一日”,屬于坦蕩面對生命的一日。由此聯想到古今中外多少詩人以身殉詩、慨然赴死的歷史,所謂“詩人之死”以及“最后的書寫”始終包含著對人性、生存終極的叩問與質詢,那些“向死而生”的鋒芒必現,使其在揭示和批判人性的限度時往往毫不留情。但此刻,戈麥的《最后一日》卻顯現了內心劇烈沖突已然閃過的傾向,“我把黑夜托付給黑夜/我把黎明托付給黎明/讓不應占有的不再占有/讓應當歸還的盡早歸還”,詩人以如此高度的理性表達“最后一日”的所作所為,他的情感飽滿但絕無過分的感傷,這一寫作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與海子晚期的抒情詩有幾分相似之處,“眷戀”、“托付”以及宗教般的情懷,構成了“最后一日”獨特的風景。
按照現有掌握戈麥詩歌創作的材料,《最后一日》屬于“厭世者時期”之后的作品④。無論是詩歌《厭世者》本身,還是作為自印合辦刊物之《厭世者》,之后的戈麥“一變過去的寫法,創造了一種全新的形式”,“這是他天才煥發的最初的日子。之后,他的創作就進入一個完全自覺的時期,而他也因此陷入了全面的孤獨。”⑤而后,即1990年7月至8月,戈麥又完成了詩集《鐵與砂》,在這部被友人稱之為“關于他的生命,關于詩歌,關于人和世界的命運”{6}的創作,顯然構成了戈麥創作的一次“綜合”與“轉向”——無論從主題還是詩藝,《最后一日》對于曾經的寫作具有總結性的意義,從此,他進入了生命同時也是創作的最后階段;《最后一日》同樣也是一種關于生命和寫作的告別,詩人最后的生命選擇在這里已顯露出“預兆”。
二
戈麥,原名褚福軍,來自黑龍江邊境的一個農場。戈麥1985年考入北大中文系,但與當時一代大學生普遍對文學懷有濃厚的興趣相比,戈麥開始寫作似乎有些見遲,“直到1987年,應當說是生活自身的激流強大地把我推向了創作,當我已經具備權衡一些彼此并列的道路的能力的時候,我認識到:不去寫詩可能是一種損失。”⑦1987年以后,戈麥開始正式接觸現代詩歌,并開始著手創作。1989年大學畢業后,詩人開始使用“戈麥”這個筆名,在朋友眼中,詩人終于在“戈麥”這個筆名中找到了自己——“某種堅實、嚴峻的東西。”不過,對于另外一些人來說,卻將戈麥的早逝和他的筆名聯系起來,認為“戈麥”這個名字不吉利,“戈”為兵器,加于“麥”,“分明意味著殺戮”⑧,但顯然,“戈麥”兩個字無論從單字解讀還是諧音角度,都具有不同的意蘊,這種與生俱來的意象性所指,或許正是詩人臧棣評價時指出的詩人的“天賦之債是最難理喻的”⑨。
從意象的角度,《最后一日》使用了黑夜、黎明、田野、谷穗、往日等元素,這些元素在配合整首詩那種時而哲理,時而敘述;時而遙想,時而回顧的筆觸過程中,構成了某種懷舊的情調——
屋宇寬敞潔凈
穹寰熠熠生輝
勞作的人安于田上
行旅的人四處奔忙
我把黑夜托付給黑夜
我把黎明托付給黎明
讓不應占有的不再占有
讓應當歸還的盡早歸還
眷戀于我的
還能再看一看
看這房屋空無一物
看這溫暖空無一人
此時,戈麥的詩歌態度,既構成了漢語詩人進入“青春寫作”所流露的典型狀態,同時,又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有幸進入語言與藝術層面上的孤獨直至疏離的狀態。可以想象的是,正如《戈麥自述》中提到的那樣,“戈麥欣賞叔本華的哲學,我懷疑若能從頭再來的話,他很可能放棄文學生涯,因為他對哲學和思想史的東西有更大的興趣”;“戈麥經常面露倦容,有時甚至不愿想25歲之后的光景”⑩,構成(也許,使用“反襯”更為合適)了此刻《最后一日》中表現出來的思想、形象與智慧共同構筑的景象。“詩是對人的生存和內心的省悟,是語言的冒險。”{11}《最后一日》中那帶有明顯古典主義氣息的味道,顯現了詩人對理想、情感、生命經驗的把握能力。在幾個簡單的意象遍布之間,戈麥對于漢語詩歌本身的洞察力超越了他對詩歌意象與素材本身的洞察,他由寫作本身表現出來的懸浮狀態,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語言所能抵達的可能與高度。
三
《最后一日》曾多次提到第一人稱“我”,其中處于句首位置的更多達八次。“我”這一人稱的反復出現,很容易讓人想到那些浪漫主義式的抒情詩篇。但在這里,戈麥對于“我”的使用卻更多偏重一種對應結構——“我”與生存世界的“對應”。在“最后一日”,“末日”般的啟示來自于心靈的感知與外化。“我”把幸福留下,并不意味著“我”無所眷戀;而那“始終惦念著的”,又成為某種“遙想”。在《最后一日》中,“你”僅出現一次,但顯然,此刻的“你”與“我”已經獲得了統一。在可以面向任何一個對象的同時,戈麥使詩作獲得了廣闊的空間,從而獲得了自由與毫無限制的交流。
在《文字生涯》中,戈麥曾寫道:“我常常在夜里坐在庭院之中空望明月,直到曙光升起。我將一輪明月看作一面虛幻和真實世界的鏡子。有時,從它的面龐上還能看到一些不可思議的事情,還有我。這種習慣與死亡相通,我在過著一種無死無生的日子。有時,我對這樣一種文字生涯有些惶惑。”{12}由此可見,對于《最后一日》以及此前寫作中大量出現的“我”,除了可以理解為某種“理性的抒情”,還可以理解為某種“自我想象”直至“自我虛幻”的結果。戈麥以“我”的形式將生命的訊息和自我的經驗撒播給寫作,他的寬博、恬淡以及虛擬和寫作之間的“矛盾感”,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主體對“自我”和文字負載的多義性理解。正如戈麥在同篇文章中提及他心儀的文學大師博爾赫斯,那位洞徹萬物又因此陷入唯心、孤獨的阿根廷作家,和關于他“因痛苦而幸福,因沉湎于細瑣而抵達無限”{13}的判斷,誰說不與戈麥的《最后一日》具有異曲同工之處?!
由此推究戈麥這位“死于青春”的詩人,其過早的辭世一方面在于“我”的分裂直至喪失,另一方面,則在于主體把握語言時代焦慮滲透生命的旅程。“詩人之死的助推力主要不是由性格和心理因素產生的,而是對語言的欲望產生的”{14},說明了寫作在一個被規訓的歷史情境下,可能引發的語言的悲劇。作為一個使用現代漢語寫作的年輕詩人,戈麥以自己的個性回應寫作帶給他的壓力,他對語言的貪婪和歡樂構成了生命中某種神秘意識,同時,也構成了對自我的嚴重消耗,“不能說:這時候的我就是現在的我”、“像一筆堅硬的債,我要用全部生命償還”,戈麥在《未來某一時刻自我的畫像》中的詩句不止一次以類似的表象出現在其寫作之中。“我是唯一的表演者,觀眾們在周圍復仇似的歌唱”,體現了戈麥面對自我時刻的冷峻、高傲和毫不留情,“他追求絕對和徹底。他不能容忍妥協,這人性的弱點。他在內心里默默承受了生活和時代的全部分量。他實現了里爾克的名言:‘挺住意味著一切。”{15}是的,戈麥以燃燒自我的方式凝視“最后一日”,此時,他唯余肉體和靈魂的“自我分離”。
四
從以上《最后一日》中關于“我”的解讀,再聯系詩中的鋪敘,比如——
我把黑夜托付給黑夜
我把黎明托付給黎明
讓不應占有的不再占有
讓應當歸還的盡早歸還
……
但是也只能再看一看
但是也只能再想一想
我把肉體還給肉體
我把靈魂還給靈魂
詩人妄圖通過語言“歸還”一切已一目了然。但是,值得指出的,這些平淡無奇的句子,一直隱含著詩人在“最后一日”的“自我分裂”。顯然,此刻的戈麥期待以“語言的利斧”將不屬于自己的東西“歸還”,進而回歸“源出”或者介入“未來”的情境,但這種詩意的想象,在現實意義上反映的卻是語言和生存環境之間的張力。如果可以進一步聯系戈麥以往的創作,在寫于1989年末的《家》中反復出現“我要拋開我的肉體所有的家”;《誓言》中的“我已經可以完成一次重要的分裂”,那么,《最后一日》的“歸還”或許只是一個階段的終結。
當代詩歌發展到20世紀90年代,究竟使用怎樣一種語言進行寫作和表達生存問題已成為重要的課題。無論從“第三代詩歌”帶來的口語化、淺表化和世俗化情境,還是生存問題本就是文化轉型之90年代的“第一要務”,都對往日的詩歌寫作或曰傳統的詩歌標準給予了解構。從這個意義上說,那些以語言實踐和生命探尋為己任的詩人往往倍感孤獨,海子、戈麥之死在一定程度都可以理解為語言“漲破”生命的結果。反思上述事實,不難發現:在某些時候,“曲高和寡”和“難以為繼”具有等同的意義。“我把肉體還給肉體/我把靈魂還給靈魂”,代表了詩人以語言還原生命的過程,只是這樣的刀鋒隱含著自我的戕害,其分裂的傷痛始終大于外在的壓力。“靈魂與肉身在此世相互找尋使生命變得沉重,如果它們不再相互找尋,生命就變輕”{16},劉小楓關于“沉重的肉身”的論斷,很能說明《最后一日》中的語言的“歸還”,在“拓展”與“承受”之間,能給詩人提供最大限度的自由正在于“生命不能承受如此之輕”。
從詩歌本身看待戈麥最后的日子,“我”的隱退使《眺望時光消逝》(一)、《眺望時光消逝》(二)、《關于死亡札記》等充滿了末日預言的特質。從事實的角度,這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啟示:戈麥已經告別了個人的傾訴走向了世界本身,而這,正是其處理個人與世界的最后的方式……
作者簡介:張立群,遼寧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文學博士。
① 西渡:《戈麥的里程》,《守望與傾聽》,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頁。
② 戈麥:《關于詩歌》,《戈麥詩全編》,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426頁。
③ [美]P.蒂利希:《存在的勇氣》,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頁-第14頁。
④⑤⑥ 《厭世者》一詩寫于1990年5月1日,《厭世者》作為與友人合辦刊物在1990年4月至6月,共出5期,之后戈麥開始刊印《鐵與砂》,具體可參見西渡:《死是不可能的》,《戈麥詩全編》“序言一”,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5頁,第6頁。
⑦{11} 戈麥:《〈核心〉序》,《戈麥詩全編》,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420頁,第421頁。
⑧ 西渡:《燕園學詩瑣憶》,《守望與傾聽》,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頁。
⑨{14} 臧棣:《犀利的漢語之光——論戈麥及其詩歌精神》,《戈麥詩全編》,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436頁,第435頁。
⑩ 戈麥:《戈麥自述》,《戈麥詩全編》,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425頁。
{12}{13} 戈麥:《文字生涯》,《戈麥詩全編》,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428頁,第432頁。
{15} 西渡:《死是不可能的》,《戈麥詩全編》“序言一”,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8頁。
{16} 劉小楓:《沉重的肉身》,北京: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93頁。
(責任編輯:呂曉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