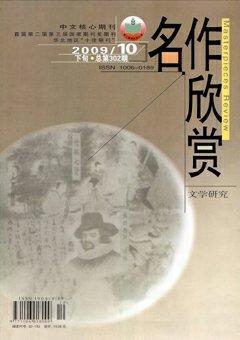當下高校知識分子的精神創傷
趙樹勤 龍其林
關鍵詞:《風雅頌》 高校知識分子 精神創傷
摘要: 閻連科長篇小說《風雅頌》逼真地刻畫了當下中國高校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他們主動或被動地被納入到高校體制,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被消解,個人自由與獨立人格逐漸地喪失。小說憑借對現實的敏銳觀察和對當下存在的犀利剖析,深化了當前知識分子小說的表現題材與精神內涵。
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成為當下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在反映高校知識分子生存狀態的作品中,不論是對知識分子精神境界和價值理想的肯定(如宗璞的《東藏記》、馬瑞芳的《天眼》等),還是對知識分子精英神話的解構和褻瀆(如張者的《桃李》,史生榮的《教授不教書》、《學者》、《導師》、《所謂教授》,邱華棟的《教授》等),作家們從不同的角度對高校知識分子的精神追求、價值觀念進行了審視。但問題是,這些作品中所描繪的高校知識分子與其他人文知識分子的區別被淡化了,未能揭示出這個群體在大學校園這一體制內衍生的充滿矛盾的精神因素,因而也很難醒悟到這一個群體被體制不斷銷蝕個性和陷入市場時代信仰闕如的精神危機。從這一點來看,閻連科的長篇小說《風雅頌》在當代知識分子題材小說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這部小說不僅拓展了高校知識分子小說的思想深度和生活廣度,將人們習焉不察的高校體制對知識分子的精神奴役進行了入木三分的揭示,而且更以令人驚駭的觀察力捕捉到了在這一體制化過程中知識分子精神深處的變異與恐慌。正是這種直抵精神根系的深度,使這部小說必然以其直面生活的勇氣成為人們反觀自我的觸點,引發出認同或拒斥、褒貶不一的爭議。
一
《風雅頌》主要講述了清燕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的教授楊科求學、治學的歷程,透過他進入皇城到讀博、留校、當教授的二十年間的經歷,深刻地揭示出一個出身農村的知識分子如何被高校體制約束、委曲求全直至精神分裂的變異過程。離開家鄉耙耬山、離別戀人玲珍的青年楊科,在進入大學報到的那一天便感覺“玲珍穿那件布衫兒有一千一萬個不合適”。接受了中文系趙教授女兒的示愛后,楊科順利地考研、讀博、留校、評職稱,過上了“一抬頭就能看見晨起的曙色和日暮的霞光”式的高校生活。本科時代就能寫出《〈木瓜〉新解》這樣見解獨到的論文的楊科,在市場語境下突然發現自己已淪為時代的落伍者,不僅論文被編輯部收取發表費,課堂上學生也因喪失了對文化經典的興趣而人數漸少,連花費五年心血完成的學術著作出版社也要收取高額費用才愿出版。這樣一個忍氣吞聲、低聲下氣的教授,竟然因為偶然撞破了妻子與副校長李廣智的奸情而機遇凸現,不但順利地保住了《詩經解讀》的課程,還有可能獲得不菲的經費出版學術著作。后來偶然參與到學生抗擊風沙的行動中,使學校成為輿論的中心,楊科被校領導強行送往精神病院。逃離醫院的楊科回到了自己的故鄉,見到了昔日的戀人玲珍,卻無法找到曾經的愛情,只能在天堂街的風塵女子身上獲得一種精神的慰藉。因為不愿玲珍的女兒小敏與木匠結婚,楊科失手殺死了木匠,逃亡途中發現了古代遺留的詩城,他率領一群妓女和失意的教授來到了詩經古城,試圖建構起一種沒有權力、不存在壓迫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學術成為手段,知識轉化為權力與經濟利益,不學無術者成為了高校體制的操縱者,知識分子由于受體制的長期抑制唯唯諾諾、麻木不仁,這便是小說所揭示的當前中國高校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和時代真理。經歷過高校體制的不斷改造,楊科在小說開始時已經喪失了作為人文知識分子的尊嚴和責任感,遑論關注社會公平、追求人類良心的公共使命,扭曲為對體制的順從。楊科一方面具有知識分子殘留的價值追求,他希望通過對詩經的研究,“重新揭示了一部經書的起源和要義,為一個沒有信仰的民族重塑了精神的家園與靠山”,在內心深處,他意識到自己“是教授,是知識分子……是個有尊嚴的人”;但在另一方面,他又無奈地認識到,權力和金錢是這個時代的中心話語。發現妻子與副校長偷情后,楊科并沒有大發雷霆,反而“讓我覺得有些內疚,只好一連聲地說,對不起,對不起……我應該先給你們打一聲招呼再回來”。他所以如此的原因非常簡單,那就是楊科在高校的生存和發展必須得仰仗體制的認可,否則便沒有生存的空間。發現妻子偷情的人物竟是副校長李廣智后,楊科要求的是希望李廣智“給系里說一下,古代文學教研室可以沒有,但《詩經解讀》這門課我不能不講”。不僅如此,楊科還利用偷情事件要挾妻子與副校長:“我用五年時間寫了這部專著你說我不能不出吧?可現在除了垃圾外,有哪一本學術專著出書學校不贊助?哪一本書不是越有價值越是沒人看?我不能因為你和他有了那樣的關系,反而不能不去他那兒要該給我的出版經費吧。說他要是明白人,真的知道自己做錯了事,對不起了我楊科,這時候就該主動把出版經費送給我。”這種既渴望尊嚴、認同,又離不開體制規約的現實,使楊科面臨著兩難的選擇。他在不得不“原諒”妻子、表現出“大度”的同時,內心深處又有著難以抹去的恥辱。在高校體制不斷官僚化、大學日益市場化的時代氛圍中,知識分子的精神立場和價值追求越發顯得輕飄和曖昧。
二
《風雅頌》無疑是近年來知識分子題材小說的一大收獲,它是寫知識分子的,但又不局限于此,而是超越了知識分子具象,成為對這一個社會群體的靈魂狀態的反思。可以看出,閻連科是一位對中國精英知識分子群體十分關注的作家,同時也對他們的精神信仰的淡漠、缺失表示出了痛徹的憂慮。他在小說中寫楊科、趙茹萍、李廣智們,寫高校體制內的弱勢者、強勢者和依傍權貴者,既寫他們對現實利益的認同,又寫其心靈的蒼白和空洞,以及面對權力時的恐慌、握有權力時的心理異化,在不經意間刻畫出了這個群體的不同部落的精神根性。
還在本科時代,楊科并未經過多少猶豫便作出了和趙茹萍戀愛的決定。因為趙茹萍曾這樣對楊科說,“只要我倆一結婚,你就完全可以擺脫你的農民身份了,可以名正言順地成為趙家的女婿,京城第一名校的教師”,渴望成為體制內一員的楊科毫不遲疑地選擇了趙茹萍。留校之后的楊科,已經習慣了體制內的生活:“撰寫論文,結集成書,出版發表,參加各種《詩經》學術研討會”,和到“討論會上做重點發言。回來后領著紀念品,再到課堂上介紹討論會上的見聞和各路專家對《詩經》獨辟蹊徑的理解和高見,有時也把自己某篇獲獎論文的證書拿到課堂上展示一番”。然而,在這種習焉不察的高校體制內的長期生活中,科研、課題、出版等體制內的生存方式徹底約束了楊科的精神狀態、思維方式。如何適應高校體制的規則,成為楊科精神的基本出發點。在這個過程中,楊科也曾清楚地意識到高校官僚的權力——“他把他的李廣智三個字往某一頁紙的右下角一寫,某某副教授就可能成了教授、成了學術帶頭人、成了某個科研項目的領軍人物。從此,那領軍人物他們家的柴米油鹽就可以在科研項目里報銷了”,但是這種認識不僅沒有給楊科帶來警惕與幫助,反而使他在體制內越陷越深。當楊科拿著潛心五年研究的學術手稿回到家里,卻發現妻子趙茹萍和副校長李廣智偷情在家。他幾乎沒有作為丈夫的憤怒和作為知識分子的恥辱感,而是內疚與惶恐,面對“副部級的知識分子李廣智”、“管著皇城赫赫名校教學的副校長”、“全國所有大學博士點審批小組的權威組長”,楊科“想說啥,卻只嘆了一口氣”。此時,楊科所想到的仍然是高校體制所認可的學術資源、地位,內心的價值觀念、是非觀念就在這種體制內的消磨中完全扭曲。在出版《風雅頌》遇到經費困難時,楊科又想到了利用妻子與李廣智的偷情來獲取學術資源,“我們夫妻倆就該聯手向他要,趁我出版《風雅頌》這機會,打報告要他批上二十萬、五十萬,有可能就批上一百萬。他要給我們批了一百萬,過去的事我們真的既往不咎,拿二十萬我出精裝豪華本的《風雅頌》,那八十萬就存到存折上”。當楊科牽涉到和學生阻擋風沙事件、惹怒當局時,學校領導表決送他去精神病院,李廣智猶豫了一會兒才舉手,這在楊科便是受寵若驚的舉動:“李副校長是個好人……你一定跟他說一下,說我楊科謝謝他”。懷著對《詩經》的無比熱愛,楊科被納入到高校體制,并逐漸地淪為制度的附庸,喪失人之為人的精神追求、價值信仰,直至最后被迫變成了一個神經官能癥患者。
閻連科寫出了知識分子的精神殘缺,而這種殘缺因具有相當廣泛的代表性而成為了對時代語境的某種寓言。“意識形態主流文化的拒斥尤其是90年代以來大眾文化的僭越,人文學術的啟蒙功用和現實功能在二者的擠兌下日益萎縮,其神圣的中心話語地位已然被無形消解”①。這種高校體制中的科研、評職稱、申請經費、著作出版等規范對身處其中的知識者的奴役、蹂躪,知識分子面對這種奴役、扼殺時的無奈和絕望,他們陷入絕望之時所顯現的文化劣根性、精神缺陷性和人格的矮化,在小說中得到了令人震驚的描繪。魯迅終其一生的創作,一個重要的使命就是喚醒富于理性的人們認識自己的處境,并因此而清理國民性中的劣根性,以便獲得重新為人的資格。而在楊科身上,我們不得不悲哀地發現,這種清理劣根性的任務不僅未能在普通民眾中普及,甚至在精英知識分子身上得到了隔代的繁衍,這或許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地方。
三
在當代社會中,各種權力機制都向知識專業和生活領域進行滲透,從而使知識分子不再幻想成為社會的先知先覺者。正是社會生活的現代化和知識分子的有機化,使蘇格拉底所強調的知識分子的牛虻精神在這個時代喪失了發展的契機。相反,由現代化引發的世俗化,使人們從對經典、神圣和信仰的堅守中剝離出來,轉而以經濟利益、現實利害關系作為自己的行為標準。閻真先生曾這樣闡述自己對時代語境中的知識分子的認識:“在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意識和責任意識正在淡化,而這兩點,正是他們身份標記,我因此痛感‘死亡之說正在成為中國的現實,我自己也強烈地感到了內心的動搖,以至崩潰。可以說,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都選擇了放棄,很多人利用一切機會在‘灰色地帶上下其手”,正是“普通知識分子生活中那種宿命性的同化力量,它以合情合理不動聲色的強制性,逼使每一個人就范,使他們失去知識分子的身份,變成一個個僅僅活著的個體,虛無主義者”②。
為時代語境規約的知識分子們,在相對主義的氛圍里失卻了對終極價值和烏托邦理想的信仰,崇高與神圣成為明日黃花。在知識分子的世俗化、無根化的潮流下,他們所追求的知識正在逐步地遠離神圣,而成為謀生、謀權的有效手段。《風雅頌》中的趙茹萍、李廣智等人,便是這些遠離神圣、在權術金錢中奔突的知識分子的詮釋。作為學校副校長的李廣智,利用手中掌握的評定職稱、評獎和分配科研經費的權力,與楊科的妻子趙茹萍公然在家偷情。事情敗露后,李廣智為挽救自己的仕途,他鮮廉寡恥地用保證楊科的《詩經解讀》課程、撥一筆出版經費的條件進行交易。作為楊科妻子的趙茹萍是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角色。拋開中學時期發生的早戀、墮胎的往事不談,進入清燕大學之后的她成為利用規則、玩弄權色交易的行家里手,并順利地從圖書管理員成為講師、副教授、教授。但作家并沒有將這一形象簡單化,而是寫出了她自身的屈辱與不易。偷情敗露后,趙茹萍對楊科說,“物價又漲了你知道不知道?以前雞蛋是三塊二一斤,現在是四塊六一斤;以前花生油是三十塊錢一桶,現在是四十七塊錢一桶;以前一美元能換八塊六人民幣,現在這比價嘩一下落到一美元兌換八塊一”,將這種身處體制不得不認同、利用的無奈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出來。同時,小說還反映出了目前高校知識分子的結構上也呈現出世俗化的特點。作品中出現了眾多的知識分子形象,無論是校長、系主任還是普通教授,他們幾乎沒有表現出多少傳統人文知識分子所具有的社會批判意識與人類良心的特點,相反更多地體現出權力話語知識分子、技術知識分子和經濟型文化人的特點,即注重為現實體制服務、注重知識的實用性、注重知識的效益原則和交換原則,他們已經放棄了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與人類良知的作用,完全退守到個人生存的世俗空間和經濟利益之中,幾千年從未在知識分子群體中獲得過道義合理性的世俗原則,在體制內的高校知識分子中不動聲色地獲得了現實的合理性、合情性,這不得不說是這個時代的一大悲哀。
《風雅頌》是對當下高校知識分子精神生態的一種劍走偏鋒式的冷峻逼視,是現實合理性作用下產生的荒誕事件的真實反映,它是對知識分子題材的一次集中審丑,更深層的則是對知識分子精神信仰和立足點的找尋,直接追問部分精英知識分子的體制性墮落與精神沉淪。《風雅頌》以其獨特的精神力度和心靈深度,提醒著我們真正的小說應該是對現實存在的敏銳發掘和勇敢表達,而不是恰恰相反。
作者簡介:趙樹勤,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文學博士,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女性文學;龍其林,中山大學中文系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生,研究方向為中國當代文學。
① 梁振華:《宿命與承擔——市場經濟浪潮中人文知識分子的角色選擇》,《當代文壇》2001年第2期。
② 閻真:《時代語境中的知識分子——說說〈滄浪之水〉》,《理論與創作》2004年第1期。
(責任編輯:范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