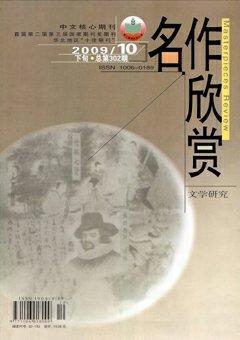荒誕境遇下的存在狀態(tài)
關(guān)鍵詞:存在主義 荒誕境遇 存在狀態(tài)
摘 要:作為新寫實作家的中堅的劉震云,深切關(guān)注人的生存境遇、生存狀態(tài)等存在圖景。他雖然不是純粹意義上的“存在主義”作家,但對存在的非理性狀態(tài)具有深切認(rèn)識和感悟。從存在主義的角度切入劉震云的小說創(chuàng)作,看到的是在荒誕境遇下人生道路的扭曲,普通人日常生活存在的沉淪,在物質(zhì)與權(quán)力侵蝕下生存狀態(tài)的異化。
20世紀(jì)80年代末90年代初興起的新寫實小說,在新時期文學(xué)領(lǐng)域中掀起一股熱潮,并涌現(xiàn)出了劉震云、劉恒、池莉、方方等一批中青年作家。其中劉震云以其獨特的風(fēng)格,一直以來被評論家認(rèn)為是新寫實作家的中堅。劉震云以一種旁觀者的眼光和冷峻的筆調(diào),對人的真實生存狀態(tài)作不動聲色的描寫,從而為淹沒在滾滾紅塵中的眾生畫像。對生活的深刻而犀利的關(guān)照,使他的小說具有了魯迅風(fēng)格般的冷峻,使人在表面庸碌繁忙的生活中警醒,更有一種發(fā)人深思的力量。
劉震云的創(chuàng)作始于1982年,創(chuàng)作的《瓜地一夜》、《鄉(xiāng)村變奏曲》等多是一些描寫鄉(xiāng)土生活的作品。從1987年的《塔鋪》開始,劉震云轉(zhuǎn)變風(fēng)格,創(chuàng)作出一系列被評論界稱為“新寫實”的系列作品。作品關(guān)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物的生存處境,展示了一幅當(dāng)代人的世俗生存畫卷。洪子誠這樣評價他的小說:“無法把握的欲望,人性的弱點和嚴(yán)密的社會權(quán)力機(jī)制,在劉震云所創(chuàng)造的普通人世界中,構(gòu)成了難以掙脫的網(wǎng)。生活于其間的人物面對強大的‘環(huán)境壓力,對命運有不可知的宿命感;同時又在適應(yīng)這一環(huán)境的過程中,經(jīng)歷了人性的扭曲。”①劉震云的“新寫實”系列小說正是通過描寫處在荒誕生存境遇中普通人的存在狀態(tài)表現(xiàn)出對命運和人性的關(guān)注,文章從存在主義的角度來重新解讀劉震云的小說。
一、荒誕境遇下人生道路的扭曲
存在主義人學(xué)的基本觀點是世界荒謬、人生孤獨。每個自為的人處在世界中遇到的常常是障礙、限制和奴役。每個人可以通過行為選擇把握自己的命運,通過自由選擇實現(xiàn)自己的存在。存在主義哲學(xué)的另一個重要命題是生存境遇說。認(rèn)為人的生存從根本上說是一種境遇中的存在,人并沒有選擇他的那種特殊境遇,但是發(fā)現(xiàn)自己受到一個陌生而敵對環(huán)境的壓制和包圍。在試圖控制自己的境遇時,會碰到新的頑固限制。當(dāng)人可以成功地改造并控制個別環(huán)境時,不可避免地會暴露他所不能應(yīng)對的最基本界限,例如痛苦、孤獨、虛無、罪惡、死亡。
劉震云的成名作《塔鋪》中的那些來自農(nóng)家的高考補習(xí)生們,扛著鋪蓋卷,拎著“饃袋”來參加補習(xí),從場院上抱回麥秸打地鋪,在四處漏風(fēng)的教室里點著蠟燭看書,頓頓窩頭就菜湯……他們真正的動機(jī)并不是為了崇高的理想與抱負(fù),而是因為他們將來一旦能夠考中,便可能脫離農(nóng)村,改變自己的人生境況。滿操場拎著棍子追打老婆的王全就曾嘆著氣對自己的孩子說:“等爸爸考了,做了大官,也讓你和媽媽享兩天清福”。②小說不回避現(xiàn)實人生的煩惱痛苦,深刻揭示了剛剛走過“文革”的那代人所面臨的人生尷尬。在權(quán)力魔影籠罩下的生活無疑充滿荒誕的色彩,在權(quán)力的壓制下,人不可能通過行為選擇把握自己的命運,更不能通過自由選擇實現(xiàn)自己的存在,生活在其中的個體只能通過高考這種唯一的方式,實現(xiàn)自己對于權(quán)力的認(rèn)同與渴望。他們在人生道路的選擇上完全喪失了主體性,人生道路走向扭曲。《塔鋪》中的高考生們除了“我”以外的集體潰敗:王全在離高考一個月時提前退出;李愛蓮為了救自己的父親嫁給了有錢人,沒有能夠參加考試;“磨桌”則在考試過程中住院,失去了考試的機(jī)會。劉震云在后來的創(chuàng)作談中還是自我消解了《塔鋪》里殘留的一點溫情:“《塔鋪》是我的早期作品,里面還有些溫情,這不能說明別的,主要說明我對故鄉(xiāng)還停留在淺層次的認(rèn)識上。”③
繼《塔鋪》之后,《新兵連》展現(xiàn)的是一群農(nóng)村士兵在特定年代的精神存在。劉震云在更高的層面上透視了社會權(quán)力話語運作機(jī)制籠罩下的生存荒謬和人生道路的扭曲。在《新兵連》中,由于權(quán)力欲和榮譽欲的驅(qū)動,上演了一幕幕沉痛的悲劇。作品以冷峻的筆調(diào)揭示了在“積極”、“上進(jìn)”的背后所隱藏的權(quán)力欲對人的捉弄。小說中綽號“老肥”的李勝兒,為了取得進(jìn)步,挖空心思地表現(xiàn)自己,但還是被同村來的好朋友,人稱“元首”的新兵告了密,因患羊角風(fēng)被遣送回家,最后因“丟面子”而投井自殺。而“元首”打“老肥”的小報告,只是因為想給軍長開小車,“為了少個競爭對象”。李上進(jìn)的悲劇,更令人深思。他是一個渴望上進(jìn)的老兵,一心想入黨,因而他積極表現(xiàn)自己。他認(rèn)為來當(dāng)一回兵,如果入不了黨就回去“那真是丟死人了”。由于他的入黨動機(jī)并不端正,最后沒能經(jīng)受住組織的考驗,在絕望中向指導(dǎo)員打黑槍,由“上進(jìn)”而成為階下囚。
曾有人用“中國生活”這樣的“術(shù)語”來評價劉震云的小說創(chuàng)作:“在屈指可數(shù)的一小批優(yōu)秀作家中,劉震云的過人之處即在于他對中國生活最痛切的體悟、最深刻的洞悉,以及對其體悟和洞悉的外具諧謔效果,內(nèi)具恥辱意蘊的藝術(shù)表現(xiàn)。”④《新兵連》描寫的是一群“文革”中的新兵。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決定了這一群初涉人世、閱歷簡單的農(nóng)村兵人生和精神存在的特殊性。他們在痛苦慘烈的人生追求中進(jìn)行著精神的煉獄。他們的價值理想蛻變?yōu)闊o目的和無意義的政治游戲,存在失去了其本真的面貌。他們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行動和目標(biāo)是悖離的。李上進(jìn)由一個渴望上進(jìn)的老兵淪為階下囚的人生命運,體現(xiàn)出他已不是獨立自為的生命個體(自為的存在),而是一個被客觀的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語境所派生的政治符碼或文化指令(非本真的存在方式)。
小說中原本憨厚、質(zhì)樸的農(nóng)家子弟,在“文革”那種荒誕的社會環(huán)境中遭遇到無數(shù)的障礙、限制和奴役。一到了軍營,他們發(fā)現(xiàn)自己受到一個陌生而敵對環(huán)境的壓制和包圍。在試圖控制自己的境遇時,碰到更多新的頑固限制,在環(huán)境的壓制下,只能認(rèn)同這種環(huán)境并進(jìn)行抗?fàn)?于是就出現(xiàn)了互相明爭暗斗、打小報告、拍領(lǐng)導(dǎo)馬屁、搞小陰謀等許多人性扭曲的現(xiàn)象。在荒誕的生存境遇中的人生道路沒有任何自由選擇的空間,只能認(rèn)同荒誕的社會規(guī)則,導(dǎo)致人生道路走向扭曲與變形。
二、日常生活存在的沉淪
存在主義哲學(xué)認(rèn)為,“此在”的日常生活方式就是“沉淪”,“此在”混跡于他人,在公眾意見中迷失本我。“此在”的存在狀態(tài),就是被其所寓的“世界”和日常的自己——“常人”所攫獲。因此從存在的日常維度切入劉震云的日常生活的新寫實文本,我們就能部分探尋到存在的奧秘和“此在”的日常生活狀態(tài)。進(jìn)入“新寫實”文本,我們直面的是“生活的原生態(tài)”。正是基于此,我們的目光常局限在寫實的層面上,從而遮蔽了向“存在”作進(jìn)一步的延伸和勘探,忽略了劉震云的“新寫實”小說是對人存在的非理性、個體生存的困頓的關(guān)照。
小說《單位》體現(xiàn)了劉震云對普通人命運的關(guān)注。作品中的小林和他的老婆兩個人都是大學(xué)畢業(yè)生,對生活有過美好的憧憬。剛到單位時,也很有個性,曾公開對勸他寫入黨申請書的人說“目前我對貴黨還不感興趣”。但三年以后,小林就“悔悟”了。由于小林是一個普通科員,只能與別人共住一套房子,而要獨立住一套房子,就必須當(dāng)上主任科員才行。要提職加薪,就得入黨,于是小林開始上班積極表現(xiàn),主動找黨員談心,還學(xué)會了給領(lǐng)導(dǎo)送禮,甚至幫領(lǐng)導(dǎo)家刷廁所馬桶。小林這種變化的背后,隱藏著強大的外在因素。劉震云借小林之口說出了自己對生存哲學(xué)和關(guān)系哲學(xué)的深刻體認(rèn):“世界說起來很大,中國人說起來很多,但每個人迫切要處理和對付的,其實就是身邊周圍那么多人,相互琢磨的也就是那么幾人,任何人都不例外”⑤。小林從純樸、有理想的大學(xué)生變成了一個被關(guān)系、環(huán)境捉弄的小職員,逐漸走向平庸、世俗、功利。小林“成熟”的過程就是關(guān)系哲學(xué)對小林不斷浸淫和吞噬的過程,也是小林逐漸喪失自我,失去自我本真面目的過程。人的理想的破滅,尊嚴(yán)的喪失,帶來的必然結(jié)果是人的沉淪,逐漸喪失了主體性。
在《一地雞毛》中,作家關(guān)注的目光由單位轉(zhuǎn)入家庭生活,小林夫妻所遭遇的瑣碎的、雞毛蒜皮的煩惱更具生活的原生態(tài)。他們面臨許多日常生活的尷尬,妻子要調(diào)轉(zhuǎn)工作,就要去求當(dāng)權(quán)者,需要拉關(guān)系,送人情;孩子入托,同樣要去求人,而且更加艱難,小林連門口的修車的老大爺都求到了,也沒有辦通。在世俗權(quán)力的強大支配力面前,個人力量顯得非常渺小與無奈。
《一地雞毛》里,小林已不得不融入到世俗的河流里,向現(xiàn)實妥協(xié)和認(rèn)同。劉震云曾說:“在這個世界面前,任何人都是輸者。”⑥小林生活的日常過程就是“沉淪”。沉淪的核心在于放棄自己本身。人有兩種選擇,即選擇“是自己本身”或選擇“不是自己本身”。這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甘于墮落”或“抵抗沉淪”。抵抗“沉淪”正體現(xiàn)了人的存在價值和存在意義。小林的存在意義上的悲劇即在于他的“自甘墮落”與沒有意識地去抗拒“沉淪”。小林放棄了他自己本身,逐漸消除了自身的獨特性趨向眾人。實際上小林不是按照他自己的價值或標(biāo)準(zhǔn)行事,而是按照一個共同依循的“他”作為標(biāo)準(zhǔn)。這個“他”就是通常所說的“自古以來”、“常言道”的代言人。“他”給我們擬定了共同的行事標(biāo)準(zhǔn),我們不能違拗和反叛“他”的旨意。在日常生活中,小林并不是作為“小林自己”,而是作為“常人”或“他人”存在的。在這樣的存在方式中,“自身”完全消融于“他人”,“他人”決定我們的生存價值和存在方式。小林在進(jìn)入“單位”之初,在進(jìn)入“一地雞毛的日常生活”之初,無疑是個“例外”。而小林由“例外”向“常人”的位移就是小林喪失自己的本真存在而向非本真存在的“沉淪”。
三、生存狀態(tài)的異化
海德格爾把此在的本質(zhì)規(guī)定為生存,因此從存在的生存論上解讀劉震云的“存在”主題應(yīng)是分析闡釋其文本的必然途徑。按照薩特的劃分,“存在”可以分為兩種:物質(zhì)存在和精神存在。劉震云早期小說中的存在圖景,無論是物質(zhì)層面還是精神層面,都極為貧乏。正是物質(zhì)生存的極端匱乏導(dǎo)致了精神生存的異化和扭曲。從《瓜地一夜》的寫作開始,到《塔鋪》、《新兵連》的問世,其間還有《鄉(xiāng)村變奏》、《被水卷去的酒簾》、《栽花的小樓》、《罪人》等篇,物質(zhì)匱乏成了鄉(xiāng)村社會最顯在的生存特征。《瓜地一夜》凸顯的是鄉(xiāng)村社會權(quán)力的實質(zhì)。《被水卷去的酒簾》是一出由貧窮所引發(fā)的愛情悲劇,人的命運、情感遭遇受到了物質(zhì)主義的嘲弄和譏諷。雖然前期作品尚屬淺層次的生存現(xiàn)狀的描繪,還沒有進(jìn)入更深層次的精神領(lǐng)域,但劉震云的平民姿態(tài)和平民視角及對鄉(xiāng)村生存現(xiàn)狀的關(guān)注、同情的價值立場已初露端倪。
《官人》中的袁、張、王、李、趙、劉、豐、方八位正副局長,因新部長上任要“大換血”而面臨升遷去留的命運選擇,于是展開了一場勾心斗角,你爭我奪的丑劇。局長老袁到部里活動,找部長談話,探聽虛實。實為常務(wù)副局長的老張,為探聽消息也低三下四地陪部長的秘書去釣魚,又挑撥打字員誣告局長老袁,結(jié)果反被小姑娘奚落。其他幾個局長也是各顯神通,走上層路線,放明槍暗箭……一個個粉墨登場,出盡了丑態(tài)。《官場》中的幾個縣委書記也同樣為地區(qū)缺額一個副專員睡不著覺。結(jié)果金全禮被提拔為副專員,因為他和新到任的省委書記是十年前的老相識。而金全禮當(dāng)上副專員剛一年多,就遇上專員吳老提前退休,又卷進(jìn)了新一輪的明爭暗斗中。
在作者筆下,官員們?yōu)榱藸帄Z權(quán)力,貪婪、卑劣、陰險、狡詐、虛偽等種種丑態(tài)畢現(xiàn):在《單位》里,副處長為一個正處長、處長們?yōu)橐粋€副局長的位子,絞盡腦汁、費盡心機(jī);《故鄉(xiāng)天下黃花》為了爭奪一枚象征權(quán)力的木頭公章,不惜煽動武斗,將全村百姓做了名利場上的犧牲品;《新聞》里為了整掉對方,挖空心思,市長搞“芝麻變西瓜”工程,書記搞“毛驢變馬”工程,勞民傷財,荒唐至極;《頭人》里為了一個村長的位子,真刀真槍、明爭暗斗幾十年。這些“官人”為什么如此熱衷于求官、爭官、護(hù)官、保官,他們絕不是為了當(dāng)“公仆”,更不是想“為人民服務(wù)”,而是為了那一份炙手可熱的權(quán)力,以及由權(quán)力帶來的無法計算的實際利益。
作者著力挖掘在帶著濃厚專制主義色彩的文化背景下,中國人權(quán)力膜拜的集體無意識,是怎樣化為身上的“奴性”,進(jìn)而產(chǎn)生出一批批的“奴隸”來。小說透過日常生活表象,揭示了隱藏在背后的權(quán)力因素,讓我們看到了在權(quán)力欲和榮譽欲的驅(qū)使下,人們所遭遇的生存尷尬以及權(quán)力對人的愚弄,在權(quán)力面前人的生存狀態(tài)被異化,精神存在處于空前的危機(jī)之中。
劉震云被譽為“中國生活的批評家”,是因為他最大限度上表達(dá)了“中國式的痛苦”和“對當(dāng)代人生的苦思冥想”。而從存在主義的角度來解讀劉震云的小說看到的是在荒誕境遇下人生道路的扭曲,普通人日常生活存在的沉淪,在物質(zhì)與權(quán)力面前生存狀態(tài)的異化。這無疑為分析劉震云的作品提供了新的角度與闡釋空間。
作者簡介:萬海洋,菏澤學(xué)院中文系教師,文學(xué)碩士。
① 洪子誠.《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史》[J].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9年版,第346頁.
② 劉震云.劉震云小說集[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97.
③ 程光煒.在故鄉(xiāng)的神話坍塌之后[J].文學(xué)評論,1999(3).
④ 摩羅.中國生活的批評家[J].當(dāng)代作家評論,1997(4).
⑤ 劉震云.《一地雞毛》文集[M].江蘇: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
⑥ 丁永強.新寫實作家、評論家談新寫實[J].小說評論,1991(3).
參考文獻(xiàn):
[1] 劉震云.《一地雞毛》文集[M].江蘇: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
[2] 丁永強.新寫實作家、評論家談新寫實[J].小說評論,1991(3).
[3] 譚雁.存在主義對我國新時期小說的影響和滲透[J].甘肅社會科學(xué),2000,(2).
[4] 吳格非.薩特與中國新時期小說對人的“存在”的探詢 [J].安徽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人文社會科學(xué)版),2004,(3).
[5] 薩特著;湯永寬,周煦良譯.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
(責(zé)任編輯:呂曉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