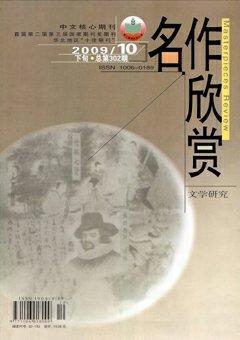荒誕美學的雙重性
舒 偉
關鍵詞:英國 童話小說 《愛麗絲奇境漫游記》 荒誕之美 雙重性
摘 要: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年,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童話小說異軍突起,開創了英國文學童話史上第一個“黃金時代”。劉易斯·卡羅爾的兩部“愛麗絲”小說是英國童話小說的代表作。本文在維多利亞時代英國兒童文學兩極傾向相互碰撞的語境中探討愛麗絲故事所體現的童話荒誕美學的雙重性,包括童心世界的荒誕之美和成人審美視野中的荒誕之美。
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年,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童話小說異軍突起,開創了英國文學童話史上第一個星云燦爛的“黃金時代”。童話小說是歷久彌新的童話本體精神與現代小說藝術相結合的產物,一般以中長篇小說的形式出現。從根本上看,童話小說具有一種獨特的雙重性:一方面它是兒童文學語境中的幻想文學,要突出兒童性(童心、童趣、童樂)和兒童本位(關愛與責任)——這使它區別于一般奇幻小說(幻想小說);另一方面它又致力于突破和超越兒童性——正如托爾金所強調的,“童話故事”絕不能局限于為兒童寫作,它更是一種與成人文學樣式密不可分的類型。①劉易斯·卡羅爾的《愛麗絲奇境漫游記》(1865)是英國童話小說的最重要代表作之一,充分體現了童話小說的雙重性。作為能與童心對話,又能滿足成人審美需求和認知需求的“模糊童話”,愛麗絲故事對于探討英國童話小說的藝術特征具有極其重要的認識價值。本文在維多利亞時代英國兒童文學兩極傾向相互碰撞的語境下,從童心世界的荒誕之美與成人審美視野的荒誕之美探討愛麗絲故事所體現的童話荒誕美學的雙重性。
一、童心世界的荒誕之美
《愛麗絲奇境漫游記》的原稿名為《愛麗絲地下奇遇記》,是作者于1862年7月一個“金色的午日”與利德爾家的幾位小姑娘一塊乘舟漫游泰晤士河時講述的童話故事,其主人公就以二姑娘愛麗絲的名字命名。三年之后,在作家喬治·麥克唐納的建議下,作者對手稿進行了擴充和加工,并請著名政治漫畫家約翰·坦尼爾為其制作了新的精彩插圖,終以《愛麗絲奇境漫游記》為名于1865年圣誕節正式出版。掉進兔子洞是愛麗絲進入這個奇境世界的開端。五月的一個夏日,小姑娘愛麗絲跟姐姐一塊坐在泰晤士河邊。姐姐在讀一本書,可愛麗絲對那本圖書毫無興趣,她漸感疲倦,不覺悄然入夢——就在這時,一只眼睛粉紅的大白兔,穿著一件背心,帶著一塊懷表,一邊自言自語地說它要遲到了,一邊急匆匆地從愛麗絲身邊跑了過去。出于兒童天然的好奇心,愛麗絲毫不猶豫地追趕上去。她看見兔子跳進了矮樹下面的一個大洞,也不假思索地跳了進去,從而進入一個充滿荒誕色彩的童話奇境。這里有許多情態各異,童心未泯的動物、禽鳥,愛麗絲發現自己居然可以同它們親密地交談,好像從小就跟它們認識似的。在這個奇異的世界里有頑童般的三月兔、瘋瘋癲癲的制帽匠、酣睡不醒的榛睡鼠、后來作為陪審員出庭的小蜥蜴比爾;有不時咧著嘴傻笑而且時隱時現的柴郡貓;有脾氣怪僻、為人虛偽的公爵夫人;更有一個性情殘暴,動輒就下令砍掉別人腦袋的紅心王后,以及她的丈夫,那缺乏主見,偏聽偏信,但心地不壞的紅心國王……這個充滿荒誕的奇境世界是維多利亞時代英國兒童文學創作中崇尚理性原則與張揚幻想精神這兩極傾向相互碰撞的產物。
18世紀上半葉,約翰·紐伯瑞在倫敦成立了專為兒童出版圖書的公司。一般認為,真正意義上的英國兒童文學即始于紐伯瑞公司開始出版兒童圖書的1744年。紐伯瑞陸續出版了為兒童讀者設計和改編的各種讀物,注重文字生動,插圖精美,但沒有脫離道德與宗教的教育主題。長期以來,在英國占主導地位的清教主義思想認為人性本惡,兒童的靈魂亟待拯救和改造,兒童的想象力應當加以克制。因此,持清教主義道德觀的人士認為童話故事和幻想故事具有明顯的非道德因素,對于兒童是有害無益的。他們提倡的是以“嚴肅文學”出現的瑪麗·舍伍德的《菲爾柴爾德一家》這樣的“勸善文學”和道德故事。18世紀以來英國兒童文學取得了很大發展,但大多數作家主要通過藝術手法的創新來開拓道德與宗教教育的主題,如安娜·巴鮑德的《兒童讀本》(1780),伊麗莎白·休厄爾的布道書《艾米·赫伯特》(1844),瑪麗亞·埃奇沃思的道德故事集《父母的幫手》(1796)等。隨著浪漫主義思潮席卷歐洲各國,要求把兒童教育從禁錮兒童的宗教統治下解放出來的呼聲愈加強大。同時在翻譯引進的歐洲經典童話的影響下,童話和幻想文學的創作在英國也蔚然成風,與堅持“教誨”或道德說教的作家陣營發生針鋒相對的碰撞。于是,為兒童寫作應當遵循“理性”原則還是張揚“幻想”精神成為英國兒童圖書創作的價值取向——在19世紀英國兒童圖書出版商看來,這就是要“教誨”兒童還是要“娛樂”兒童的兩極傾向。
愛麗絲故事的革命性在于它徹底顛覆了維多利亞時代的說教文學,“把荒誕文學的藝術提升到最高水平”。在《愛麗絲奇境漫游記》的第9章,公爵夫人告誡愛麗絲“每一件事情都有一個教訓,只要你能夠發現它的話”。這代表了維多利亞時代那些堅持對兒童進行理性教育與道德說教的人們的普遍看法。然而“愛麗絲”故事表明了艾米莉·迪金森所說的,“太多的理性就是赤裸的瘋狂”。而那看似瘋狂的幻想世界則具有洞穿真相的生命力和奇特的藝術吸引力。在愛麗絲故事里,要發現有理性的教訓成為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疑難問題。正如C·N·曼洛夫指出的,在愛麗絲的世界里,那些本應具備各種理性及有意教訓的成人們,包括神經質的大白兔和精神變態者紅心王后等,都是瘋狂的。這些人誰也不能恰當地行事。許多人都把愛麗絲呼來喚去,但愛麗絲通常對他們回以顏色,因為他們的荒謬可笑消除了他們的權威。愛麗絲是兒童幻想文學中第一個不屑于接受無論什么教訓的兒童,除非那是關于變幻本身的“教訓”②。的確,在愛麗絲遭遇的這個世界里,小姑娘與小動物及鳥兒們還能夠恰當地處理她們自己的事情(見第3章“團隊賽和一個長故事”),而這個社會的當權者和其他成員卻不能恰當地進行任何有理智的行動。從白癡般的男仆到莫名其妙而又歇斯底里的公爵夫人,從瘋狂的茶會到混亂不堪的王后的槌球賽,從假海龜的荒誕故事到紅心杰克接受審判,人們看到的是最沒有理性的人物和最荒謬的行為。我們不妨見識一下王后的槌球游戲。槌球賽本是英國的一種傳統游戲,在戶外草坪進行,參加者用長柄木槌擊打木球,使之穿越一系列球門。在愛麗絲故事中,王后的槌球游戲是在一個古怪的槌球場開始的,場地里到處都是田坎和壟溝。更奇特的是,用來穿越球門的槌球由活的刺猬充當,用來擊球的球棒由活的火烈鳥充當,而槌球要穿越的拱門就由彎下身子,手腳撐地的士兵們充當。比賽一片混亂。參加比賽的人根本就不講任何游戲規則,為了爭奪刺猬而吵得不可開交。王后動不動就勃然大怒,時不時地下令把誰的頭砍掉。愛麗絲感到這真是一場可怕的游戲,但令她詫異的是,王后如此頻繁地痛下殺手,居然還有人能在這里活著。這是兒童本位的顛覆性幻想故事,體現了童話奇境的黑色幽默。(這需要由鷹面獸對王后的暴虐行為給予“真好笑”的評價:“那完全是她的胡思亂想罷了,他們從來沒有殺死過一個人。”)
此外,愛麗絲故事中的“荒誕詩”集中體現了童心世界的荒誕之美。這些“荒誕詩”全是針對卡羅爾那個時代非常流行的、要求孩子們誦讀的宗教贊美詩和道德教喻詩的戲仿之作,它們不僅徹底顛覆了那些要求兒童遁規蹈矩的詩作,而且成為英國兒童文學的珍寶,廣為流傳。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當時非常流行的以道德教誨與理性規勸為目的的原作早已湮沒無聞,只是作為卡羅爾戲仿詩的互文性因素而為人所知。《愛麗絲奇境漫游記》中愛麗絲背誦的《小鱷魚》是對18世紀著名的宗教贊美詩作家艾薩克·沃茨的兒童詩《不能懶惰和淘氣》(1715)的戲仿。沃茨的詩是這樣的:
你看小蜜蜂,整天多忙碌,光陰不虛度,花叢采蜂蜜。
靈巧筑蜂巢,利落涂蜂蠟,采來甜花蕊,辛勤釀好蜜。
我也忙起來,勤動手和腦。魔鬼要搗亂,專找小懶漢。
沃茨原詩用兒歌的形式宣揚道德教誨,其主題非常明確,就是要孩子們向小蜜蜂學習,不浪費時間,不虛度光陰。只有辛勤忙碌,才能像小蜜蜂一樣,有所收獲。而游手好閑,無所事事,就會被魔鬼撒旦看中,去干傻事、壞事。下面是卡羅爾的戲仿:
你看小鱷魚,尾巴多神氣,如何加把力,使它更亮麗。
尼羅河水清,把它來澆洗,鱗甲一片片,金光亮閃閃。
笑得多快活,露出尖尖齒,張開兩只爪,動作多麻利。
溫柔一笑中,大嘴已開啟,歡迎小魚兒,快快請進來。
忙碌的小蜜蜂變成了張口待魚的小鱷魚——成為大自然中神氣十足,笑容可掬,張開大口等待小魚兒入口的快活的捕食者。這看似信手拈來,但涉筆成趣,妙意頓生。卡羅爾以諷刺性的弱肉強食現象與尼羅河的勃勃生機營造了一種童話世界的喜劇性荒誕氛圍。
再看另一首荒誕詩《威廉老爸,你老了》,這是卡羅爾對羅伯特·騷塞的宗教訓喻詩《老人的快慰,以及他如何得以安享晚年》(1799)的戲仿。騷塞的詩用一老一少,一問一答的形式寫成,目的是告誡兒童心向上帝,虔誠做人。在詩中,年輕人詢問老人為何不悲嘆老境將至,反而心曠神怡?老人回答說,自己年輕時就明白時光飛逝,日月如梭的道理,而且他總是“心向上帝”,所以虔誠地服從命運的安排,無怨無悔,自然樂在其中。在愛麗絲故事第5章中,當毛毛蟲聽說愛麗絲在背誦那首《忙碌的小蜜蜂》時背走了樣,便讓她背誦《威廉老爸,你老了》,只見愛麗絲雙手交叉,一本正經地背了起來:
年輕人開口問話了:
“威廉老爸,你老了,
須眉頭發全白了。
還要時時練倒立,
這把年紀合適嗎?”
“在我青春年少時,”
威廉老爸回兒子,
“就怕倒立傷腦袋;
如今鐵定沒頭腦,
隨時倒立真痛快。”
“你已年高歲數大,”年輕人說,
“剛才已經說過了,
而且胖得不成樣;
為何還能后滾翻 ——
一下翻進屋里來?”
“在我青春年少時,”
老賢人說話時直把白發來搖晃,
“我四肢柔韌關節靈,
靠的就是這油膏——一盒才花一先令,
賣你兩盒要不要?”
“你已年高歲數大,”年輕人說,
“牙床松動口無力,
只咬肥油不碰硬;
怎能啃盡一頭鵝,
連骨帶頭一掃光,
敢問用得哪一招?”
“在我青春年少時,”老爸說,
“法律條文來研習。
每案必定窮追究,
與妻爭辯不松口。
練得雙頜肌肉緊,
直到今天還管用。”
“你已年高歲數大,”年輕人說,
“肯定老眼已昏花,
何以能在鼻尖上,把一條鰻魚豎起來——
請問為何如此棒?”
有問必答不過三,到此為止少廢話,
老爸如此把話答,
“休要逞能太放肆,喋喋不休讓人煩!
快快識相躲一旁,不然一腳踢下樓。”
維多利亞時代的兒童詩以道德教育和宗教訓誡為主要特征,其消極因素在于泯滅了童心世界的游戲精神和人類幻想的狂歡精神。卡羅爾的荒誕詩是對那些宣揚理性原則的說教詩和教喻詩的革命性顛覆,看似荒誕不經,實則妙趣橫生,意味無窮。“在我青春年少時,上帝時刻在心中”,這是騷塞詩中的老者形象。而在卡羅爾的詩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荒唐滑稽但充滿生活情趣的老頑童:他頭發花白,肚子滾圓,渾身上下胖得不成人樣,但見他又是勤練倒立;又是用后滾翻動作翻進屋里;飯量極大居然一下連骨帶肉吃掉一只整鵝;還能在鼻子尖上豎起一條鰻魚,上帝何在?自然規律何在?正是這個荒唐滑稽的老頑童張揚了契合兒童天性的狂歡精神和游戲精神,使童心世界的荒誕美學呈現出最大的吸引力。
二、成人審美視野中的荒誕之美
自問世以來,愛麗絲故事不僅以獨特的藝術魅力征服了不同年齡的讀者,而且深深吸引了文學批評和文化研究領域的學者。其中的魅力之一就來自成人審美視野中的荒誕之美。羅伯特·波爾赫默斯在論及“愛麗絲”故事對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文化產生的重要影響時說,卡羅爾為藝術、小說和推測性思想拓展了可能性。通過創造“愛麗絲”文本,他成為一個我們可以稱為無意識流動的大師。他指明了通往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道路……他還指出,“從卡羅爾的兔子洞和鏡中世界跑出來的不僅有喬伊斯、弗洛伊德、奧斯卡·王爾德、亨利·詹姆斯、弗吉尼亞·吳爾夫、卡夫卡、普魯斯特、安東尼·阿爾托、納博科夫、貝克特、伊夫林·沃、拉康、博爾赫斯、巴赫金、加西亞·馬爾克斯,而且還有20世紀流行文化的許多人物和氛圍”③。
作為能滿足成人審美需求和哲理思考的“模糊童話”,愛麗絲故事以充滿想象力的藝術手法表現出對人生意義的深切關注和對現實社會的批判性探索。如愛麗絲故事中對英國司法現狀的絕妙諷刺。首先是老鼠在敘述其悲傷故事的“荒誕詩”中對老狗惡行的控訴。一只狡猾的老狗不由分說地要將一只老鼠告上法庭,僅僅因為那天早上他無事可干。老鼠對這種“既沒有陪審團,也沒有法官”的審判提出抗議,惡狗竟然宣稱:“我就是法官,我就是陪審團,我要審理整個案子,然后判處你死刑。”而國王和王后對紅桃杰克的審判(起因是王后無端懷疑紅桃杰克偷了她做的水果餡餅)更是荒謬無比。陪審團由十二個動物組成,審判還沒有開始,他們就忙著把自己的名字記在石板上,因為他們擔心審判結束前就把名字忘掉了。開庭審判了很長時間,什么實質性的問題都沒有涉及。當國王發現愛麗絲的身體在不斷長高,眼看對自己形成了威脅時,當場頒布了一條法律條文:“第四十二條法律規定,凡是身高超過一英里的人都要離開法庭。”于是所有人都看著愛麗絲。愛麗絲據理力爭,說這不是一條正式的法律,是國王瞎編出來的。國王卻說這是法典上最古老的法律,于是愛麗絲反駁道:“這樣說來,那就應當是第一條。”國王自然無言以對,便讓法庭進行裁決。大白兔煞有介事地拿出一張紙,作為證據提交法庭,紙上寫了一組莫名其妙的詩。紅桃杰克辯白道:“啟稟陛下,這不是我寫的,他們不能證明是我寫的。末尾都沒有簽名。”國王卻說:“要是你沒有簽名的話,那就只能說明情節更惡劣。你一定是想干什么壞事,不然的話,你就會像個正人君子那樣簽上你的名字。”愛麗絲目睹如此荒唐的審判,吼道“這根本就不能證明他的罪行,你們連這些詩歌說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呀!”然而沒有任何人去解釋那首詩。這之后是王后宣布的荒謬無比的判決:“先處決,后裁決。”在愛麗絲故事“滿紙荒唐言”的后面,人們讀出了作者卓越的社會評論與批判。
這里的“第四十二條法律”已經預示著約瑟夫·海勒的黑色幽默小說《第二十二條軍規》(1961)所揭示的“瘋狂世界”的時代特征。在海勒的小說中,第二十二條軍規已成為一個無法擺脫的圈套和羅網。主人公尤索林每每與它對抗,卻每每碰壁,敗下陣來。他終于明白,這條軍規并不存在,但正是因為它不存在,所以它才無所不在。而在弗蘭茨·卡夫卡的《審判》里,對紅桃杰克的荒謬審判得到了來自另一個時代的回響。安分守己的約瑟夫·K為一個他自始至終都沒有弄明白的指控而被莫名其妙地逮捕,盡管多方奔走卻申訴無門。為了面見法官,他在法院黑洞洞的回廊迷途中來回穿行,但徒勞無益,最終成為冤鬼。在《城堡》中,任憑K先生想盡一切辦法就是進不去那既沒有衛兵把守,也沒有設置吊橋的城堡。現實中,似乎神圣不可侵犯的社會存在變成了悲劇性的荒誕世界,處處是“無法穿透的黑墻”。那令人迷惑不解的指控,那詭秘復雜的迷途,那懸疑、排遣和影射的密網,那夢幻般(噩夢般)的異己和異化的強大力量,都是與愛麗絲故事異曲同工的。
女詩人艾米莉·迪金森(1830-1886)說過,“在具有洞察力的目光中,非常的瘋狂乃是最神圣的理智,而太多的理智乃是最赤裸的瘋狂”④。這是對愛麗絲故事的荒誕美學的最真實寫照。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現當代英國童話小說研究”;項目批準號:08BWW003
作者簡介:舒 偉,天津理工大學外語學院教授,文學博士。
① J.R.R. Tolkien, The Tolkien Reader. New York: Ballantine, 1966,p.58.
② Manlove, Colin. From Alice to Harry Potter: Childrens Fantasy in England, Cybereditions Corporation , 2003,p.25.
③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Novel. Ed. John Richetti,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p.579,p.581-p.582.
④ American Literature Survey: Nation and Region.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1962,p.63.
(責任編輯:范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