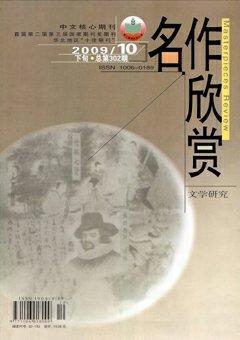境遇·追尋·宿命
關鍵詞:沈從文 《看虹錄》 生命形式 宿命意識
摘 要: 《看虹錄》是沈從文關于生命形式的一次極其隱晦卻又“放縱”的思考與探索。作者從個體境遇出發孜孜追尋生命烏托邦的真諦,發出“神在我們生命里”的熱切吁求。小說在追尋著美好的人性與神性的同時,也呈現出悲劇性宿命色彩,其中的焦慮和困惑恰從另一個側面反襯出作家對生命意義探索的執著。
沈從文的小說《看虹錄》寫于1941年7月,1943年重寫后發表于《新文學》創刊號,后收入小說集《看虹摘星錄》。問世初期它曾被看作影射作家婚外戀的艷情小說而遭到嚴厲批判,后長期淹沒在歷史風塵之中。如今半個多世紀倏然而逝,《看虹錄》又漸漸浮出海面,重新引發了讀者的閱讀興趣與思考。
境遇:“我是個對一切無信仰的人,卻只信仰‘生命”
《看虹錄》分為三部分,以“一個人的二十四點鐘”來結構情節:“晚上十一點鐘。半點鐘前我從另外一個地方歸來,在離家不遠處,經過一個老式牌樓”,天上“月光滑瑩”,我在感動中“忽然嗅到梅花清香,引我向‘空虛凝眸。慢慢地走向那個‘空虛”;經過一番太虛幻境般的精神漫游,與“太虛幻境”的女主人進行了熱烈的情愛交流之后,“我”離開了那個房間,“重新到這個老式牌樓下”;到了“晚上十一點鐘半”,“我已經回到了住處”。作家關于這段關涉男女情感的精神漫游的描寫無疑是大膽而放縱的,其中多次用細膩的筆墨對女性身體及其引發的情感沖動,進行了相當精微的描摹,如“我喜歡看那幅元人素景,小阜平岡間有秀草叢生,作三角形,整齊而細柔,縈迂徐,如云如絲,為我一生所僅見風景幽秀地方。我樂意終此一生,在這個處所隱居。”在戰火隆隆,個人敘事尤其欲望敘事尚缺乏社會認同的年代,沈從文對女性身體尤其是隱私之處的描寫無疑是觸目驚心的。然而如當時的那些批判文章,僅僅將《看虹錄》看作“故意作春宮圖”的艷情小說無疑太過片面。因為我們從上述文字得到的絕非只是感官刺激,而是一種緣于情愛之美、欲望之美的感動。從根本上來說,這篇小說可謂沈從文關于美好生命形式的一次隱晦卻又“放縱”的思考與表達。沈從文說過,“我是個對一切無信仰的人,卻只信仰‘生命”①。其根本創作意圖,就在于“以社會那本大書來好好的學一學人生,看看生命有多少形式,生活有多少形式”,正如《看虹錄》開篇所標明的,小說是在探詢“一個人二十四點鐘內生命的一種形式”。那么,作者是怎樣探索這一生命形式的呢?這到底又是一種怎樣的生命形式呢?
有學者指出,作為人類生活最終的倫理目的,烏托邦亦即生命的意義不是抽象的思維和概念所能呈現的,在他看來,偉大的小說家以自己的敘事對烏托邦的問題提供一種具體展示②,“在敘事的基礎上動用所有理性和非理性的,敘述和沉思的,可以昭示人的存在的手段,使小說成為精神的最高綜合”,這即是為什么“對自由主義的小說來說,敘事技巧變得頭等重要”③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文學精神及其獨特意義,正是在對“烏托邦問題”提供“具體”而非“蒼白抽象”的呈現中凸顯出來。由之在詹姆遜等學者眼中,關于生命的敘事遠比單純研究生命本身更具意義,他亦因此斷言應“更強調境遇”④。換言之,小說的意義乃或文學的意義,就在于描摹具體而微的人生境遇與體驗,透過許多偶然的形式來揭示人生的普遍內涵。
沈從文就是為數不多的從各種時代關鍵詞的樊籠中突圍而出,以種種“境遇”,比如翠翠的境遇,水手的境遇,吊腳樓上妓女的境遇等,表達與展現其對生命形式思考的作家。因此,與同時代許多作家直線性的進化論和啟蒙論觀點相比,沈從文對生命無疑更有著真切感悟與理解。正如《看虹錄》借男主人公之口所說的,“試來追究‘生命意義時,我重新看到一堆名詞,情欲和愛,怨和恨,取和予,上帝和魔鬼,人和人,湊巧和相左。過半點鐘后,一切名詞又都失了它的位置和意義。到天明前五點鐘左右,我已把一切‘過去和‘當前的經驗與抽象,都完全打散,再無從追究分析它的存在意義了。”基于此,沈從文從不主題先行,他“從不用自己對于生命所理解的方式,凝結成為語言與形象,創造一個生命和靈魂新的范本”,而是從個體境遇出發,通過發掘、講述現實個體欲望所由產生,及其在特定社會文化語境追尋滿足或求而不得的種種表現,深刻、感性、具體地展示千姿百態、千奇百怪的生命樣態,孜孜以尋生命烏托邦的真諦。
追尋:“神在我們的生命里”
《看虹錄》創作的年代,正是沈從文創作與思想上的彷徨期,“隨著以湘西生命形式為根基的生命理想的失落,沈從文的生命焦慮與文化焦慮日益加劇,這時期他思考的問題都是圍繞生命而展開的,生命到底是什么?生命的本質何在?如何實現生命重造與文化重造?這些問題成為沈從文這一時期思考的中心問題,在他的創作中表現出來,就成為他創作中的‘生命重造主題”⑤。綜觀其文學創作可見,作家“生命重造”的最終訴求是美好人性,他明確指出,“不管是故事還是人生,一切都應當美一些!丑的東西雖不全是罪惡,總不能使人愉快,也無從令人由痛苦見出生命的莊嚴,產生那個高尚情操。”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沈從文創作意圖正在于激發人們超越充滿“此在”的現實,從“生命”和“生活”的對比中發掘生命的意義。他將這種對比基本上放置在鄉村/都市、中心/邊緣的框架內進行,對現代文明所導致的原始生命與審美能力的萎縮進行了有力的揭示和再現。
《看虹錄》便集中體現了沈從文對生命意識與美的哲學的追尋,表征著“神在我們生命里”的熱切吁求。在他看來,性愛統一和諧的狀態才是美的、充盈著神性的人性。小說為性愛統一的和諧人性狀態設置了重重隱喻,鹿/女性都是這一和諧生命意識和神性的化身。為了更深切細膩地展示“美”的高潔,作者又設計了一個故事中的故事,夢幻中的神話。除上面所引細膩的女性身體描寫之外,小說還用多段文字描摹著作者心目中情愛和諧、人神共在的審美理想,如:“我在那個地方發現一些微妙之漩渦,仿佛詩人說的藏吻的窩巢。它的頰上,臉頰上,都被覆蓋上纖細的毫毛。它的頸那么有樣式,它的腰那么小,都是我從前夢想不到的。尤其夢想不到,是它哺小鹿的那一對奶子,那么柔軟,那么美。”母鹿、瓷瓶、雕刻……對它們的贊美是對女性胴體的贊美,對性愛的贊美,更是對一切未被遮蔽、修飾的內心欲望所發出的神性的贊美!正如作家借小說人物之口所言,“美,令人崇拜,見之低頭。發現美接近美不僅僅使人愉快,并且使人嚴肅,因為儼然與神面對!”
宿命:“美麗總是愁人的”
經歷過動人心魄的“美的歷程”的體驗之后,男性敘事主人公還是回到了現實生活中。時代在前進,凜冽的寒風在窗外刮個不停,轟隆的火炮催促著人們沿著“此在”飛奔。更重要的是,自我內心世界向著美的提升是艱難的,突破道德、倫理、文化等種種社會文明的束縛,裸露自己的靈魂和本真,并非人人都能夠做到。我們看到,作家在追尋生命真諦的同時又陷入了理想/現實、靈/肉、時代/個體的重重矛盾之中,他因此發出了“美麗總是愁人的”慨嘆。沈從文的很多作品都充盈著這樣一種悲劇性的宿命意識,“我們生活中到處是‘偶然,生命中還有比理性更具勢力的‘情感,一個人的一生可說即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來”⑦。晚年的他更做詩慨嘆:“沉浮半世紀,生存亦偶然。”⑧《看虹錄》在以個體境遇顯影作家心中美好人生形式的同時,亦形象而細膩地呈現出抒情主人公內心深處的復雜矛盾,使得這篇小說成為沈從文“美麗總令人憂愁”這一宿命觀的又一例證。
敘事主人公的矛盾首先來自理性與情欲的沖突。“我”和美麗女人之間那行行復行行式的欲言又止、設喻雙關、心理獨白等等都是這一沖突的微妙展示,其中一個非常引人注目的細節是對窗簾上屢次闖入視野的花馬不厭其煩的描寫:“我”剛剛來到充滿溫馨的小屋,便發現“窗簾已下垂,淺棕色的窗簾上繪有粉彩的花馬”;“繼續游目四矚,重新看到窗簾上那個裝飾用的一群小花馬,用各種姿勢馳騁”;“重新看那個小花馬。仿佛這些東西在奔越,因為重新在單獨中”;此后,“馬似乎奔越于廣漠無際一片青蕪中消失了”……這幾乎無處不在的“花馬”意象無疑是“我”對美麗女人欲望的表征,正如女主人對“我”一針見血地調侃:“你那么呆呆的看著我腳,是什么意思?你表面老實,心中放肆。我知道你另外一時,曾經用目光吻過我一身,但是你說的卻是‘馬畫得很有趣味,好像要到各處去。跑去的是你的心!”她甚至對“我”“發于情而止于禮”的言行有些懊惱:“我什么都懂,只不懂你為什么只那么想,不那么做。”由此可見,“我”對性的欲望蠢蠢欲動卻又一再壓抑,不敢直露,唯恐失去所謂的幽雅和禮貌,即使只是用眼睛“漫游”,也“帶著一點惶恐敬懼”,因為“同時還有犯罪不凈感雜在心上占絕大勢力”,敬畏于“房中爐火旁其時就有同樣一片白,單純而素凈,象征道德的極致”。可見超越文明的束縛,還原生命的本真,需要突破多么強大的傳統心理定勢。
其次,敘事主人公因理性/情感的相互砥礪而備感苦悶的同時,亦焦灼于現實與理想的巨大落差,“終不能不使人為眼前這個愚昧與貪得虛偽與卑陋交織所形成的‘人生而痛苦!”⑨沈從文在建構愛與美的“希臘小廟”時,不得不面對迅猛的庸俗化、金錢化的浪潮,淳樸美好的湘西正被外界慢慢同化,作者痛苦地“發現城市中活下來的我,生命儼然只淘剩下一個空殼。譬喻說,正如一個荒涼的原野,一切在社會上具有商業價值的知識種子,或道德意義的觀念的種子,都不能生根發芽……生命已被‘時間和‘人事剝蝕快盡了,生儼然只是煩瑣連續煩瑣,什么都無意義”。現實與理想的背離使他產生了無盡的困惑,更因此而對自己的創作與追尋產生了一種知音難覓的痛苦,“我永遠只想到很少幾個有會于心的讀者,能從我作品上見到我對于生命的偶然,用文字所作的種種構圖與設計。”⑩作家借敘事主人公之口發出這樣的慨嘆,“在一個‘過去的影子里,我發現了一片黃和一點干枯焦黑的東西,它代表的是他人‘生命的另一種形式”,“我靜靜的從這些干枯焦黑的殘余,向虛空處看,便見到另一個人在悅樂瘋狂中的種種行為。也依稀看到自己的影子,如何反映在他人的悅樂瘋狂中,和愛憎取予之際的徘徊游移中。”由之他決定“到明天五點鐘以前,我已經把一切‘過去和‘當前的經驗和抽象,都完全打散,再無從追求分析它的存在意義了”。在小說行將結束之時,作家又一次深入主人公的內心,做出這樣的剖白:“似乎有個人隨同月光輕輕地進到房里中,站在我身后”問:“為什么這樣自苦?究竟算什么?”面對這樣的詰問,“我勉強笑笑,眼睛濕了,并不回過頭去”,說“我在寫青鳳,聊齋上那個青鳳,要她在我筆下復活”。這個非常莊嚴的建構生命意義的文學使命只能是別人眼中的“野狐禪”,難怪“我”的眼里濕了。
小說結尾,“我”最終還是從虛幻回到現實,“詩和火同樣會使生命燃燒起來,燃燒過后,便只剩下一個藍色的影子,一堆灰。”這時候,“窗簾上的花馬完全沉靜了”。作者其后在《看虹摘星錄后記》中說,“我要寫的都已經在紙上完成了,可是到把它重新抄錄一遍時,身心都已經如崩如毀”,“我知道夢和其他都已經成為過去了。我離我自己一小時前那種生命向深處探索的情境,也很遠了。”甚至說“也許再過五十年,一個年輕讀者還希望從我這些仿佛艷而不莊作品中,對于某種女人產生一個崇高優美的印象。但是作者本人卻在完成這個工作時,儼然即已經死去了。”{11}由是“我”不由慨嘆,“上帝,我活下來還應當讀多少書,寫多少書?”更重要的是,讀這些書、寫這些文字的意義終究何在?
沈從文焦慮于這一追問與困惑。這一追問與困惑亦從另一個側面反襯出作家對生命意義孜孜以求的執著。更重要的是,他的書寫個體經驗、境遇,執著追尋生命意義的文字,無疑給徘徊前行的中國新文學開拓了另一條路徑。這一路徑頑強地指向高沖云霄的人性巴別塔;而《看虹錄》無疑是其形上光輝的一個獨特而亮麗的光源。
本文受江蘇省高校人文社科基金項目“1990年代中國小說欲望敘事研究”(項目號08SJD7500010),以及南京信息工程大學人文社科基金預研項目“消費主義文化思潮與90年代以來中國文學的轉型”支持
作者簡介:馬航飛,文學博士,南京信息工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民國文學研究院副院長、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
①⑦⑧ 《沈從文文集》第10卷,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第294頁、第267頁、第359頁。
② [美]詹姆遜:《馬克思主義與形式》,李自修譯,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頁。
③ 劉小楓:《沉重的肉身》,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第140頁。
④ [美]詹姆遜:《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代序》,陳清僑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30頁。
⑤ 吳投文:《論上世紀40年代沈從文的創作》,《廣西社會科學》,2004年第9期。
⑥⑨⑩{11} 《沈從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第48頁、第53頁、第49頁、第53頁。
(責任編輯:呂曉東)